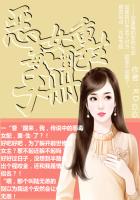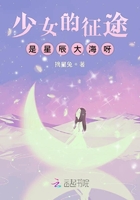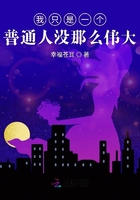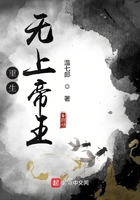一九六一年七月
我们学习创作,都是配合中心任务现编现演出身,但是后来觉悟了,认识到那时写的那些东西,在当时起过作用,今后在必要时,也同样可以利用各种文艺形式从事宣传鼓动工作,这些不可一概抹杀。但这样写出的作品,其中虽然有一些艺术上相当成熟,但是由于忽视艺术规律,严格要求那些作品,大多数都还不是艺术品。明确了文艺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有了这个认识就好了。一个运动来了,不管报刊怎样约稿,我就是不写,不管你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咱有咱的老主意。杂文短诗歌词等等可以,艺术作品不行。可是有些文艺团体,至今文艺思想、创作方法还是过去的老一套,年年月月在赶任务,自然搞不出好作品。这几年谈艺术规律不多。
描写工农兵生活,给工农兵看,他愿意不愿意看,这还是个问题。我这是说题材范围狭窄,作品描写的生活面也太狭窄。有很多片面的观点,都是因为对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忽略。我们写工农兵把他们的生活孤立了,战士就是战场,工人就是车间,农民就是地头,把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生活隔开了,太单调。特别是大部头作品,各个生活面都应该有所展现才好啊。现在,有些阶级、阶层已退出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了,不论是地主还是资产阶级都退出文学和戏剧舞台。工人和资产阶级打交道最多,但在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中却看不到资产阶级,矛盾的一方不出台,怎么写。写打仗就是打仗,写生产就是生产,工农兵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生活的风俗画、风景画,叫人看不见,怎么行。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看不到对于葬仪、婚礼,或对其他群众公共生活中绘影绘声的描写,结婚就是陪个粪筐?中国各族人民生活情趣丰富极了,但文学作品中人民的生活却被简单化了。作品的背景,如:《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赛马、打猎、舞会、婚礼等等,主人公活动的生活场景广阔极了,壮丽极了,美极了,读者如身临其境,流连忘返。我们当代的文学、戏剧、电影、绘画作品,即便是战争题材,也缺少像《伊利亚特》《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那种对战场的广阔壮丽的描绘;而写生产建设题材的作品,对生产现场的博大宏伟的描绘也几乎没有看到。
人,离开风俗习惯或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必要的大描大写,你怎么也很难把他充分表现出来。
作品中只写工农兵,很少写干部,基层干部还有,高一点的干部很少。中国古典作品写他们的“干部”(帝王将相)的很多。学生生活也应进入作品,现在学校里的青年学生也可以写成当代英雄、新英雄的典型,并不一定一写就要改造。对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很少写,一写起来也无非是落后、保守、反对合理化建议等等。要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苦难的历程,但也不尽然,他们也有当代英雄、新英雄典型。总之,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都应在文学艺术上得到反映。不然人家说你们社会生活就那么简单?有些人不写也是顾虑重重……
另外一个问题是,许多作品不是写人,而是写职业。这样作品就难写,写起来就是生产、生产。我们有时问一个同志:“你写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我写技术改革。”技术改革怎么能成为艺术作品的内容?我们要写生产,但不能单纯去写指标,指标如果强调过分,引人注意就麻烦了,指标只能提一下。文学戏剧作品只能写性格冲突。只写他是工人,不写他是某一典型性格的工人,就不是艺术品。典型又是多种多样的,典型也不能简单化,过去一写中农就是两重性。农民问题,作为一个阶级,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多彩。有些作者在写作时主要考虑的是工人、农民,什么阶级出身等等,而且又多半停留在给人物定成分上,对他们真正是什么性格则考虑得很少。有人就不受束缚,如老杜写梁建、老工程师、韦珍、常飞(《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人物),柳青写王二瞎子(《创业史》中的人物),我写《沙滩上》里的思荣老汉等等。我们这些人有老主意,唬不住,年轻人一唬就被唬住了。
文学事业本身应当生动活泼,这方面同刊物编辑部的工作关系很大。编辑工作是门学问,这工作是很难做的,文学杂志也应该各有流派。
以后应该允许编辑部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论你们有何好的看法,我编辑部有我编辑部的意见。
这多年题材限制很窄,把老作家限制了,限制了他们的长处,要他的短处,曹禺写区委书记恐怕不大行。一九五一年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从朝鲜回来后,集中了几十个人在大连写作。田汉写抗美援朝的剧本,三个月动不了笔,终于未见写出来,可他写《关汉卿》就写得那么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以自己所长要求别人之所短。
歌剧创作问题。我们的新歌剧搞了近二十年了,现在应当从艺术形式上好好总结一下,给自己立个规范,立个程式,暂时定下来,在一定的艺术规程要求下,精益求精,以便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然后再突破,再前进。为此,要好好研究一下旧剧,把好的、于新歌剧有用的都提取出来,立起新歌剧的程式。所谓立规范,定规程,也就是从多年的实践中,揭示新歌剧的舞台艺术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看看我们的新歌剧创作在剧本结构方面,人物塑造方面,唱词、道白方面,作曲方面,伴奏方面,表、导演方面,舞蹈方面等等等等,哪些做法是符合舞台艺术规律的,哪些做法是不符合舞台艺术规律的,在一部成功的、艺术上完整的新歌剧中,各个部分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共同规定。没有这样的规程,新歌剧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中国的古典戏曲、绘画、诗歌,一方面都有它的程式,另一方面艺术家又不受其限制,在其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创造自己的风格。
新诗要继续往前发展,达到高峰,恐怕在艺术形式上也得立个不太死板的程式,要有点规范。新诗的章法、结构、语言、节奏,包括平仄韵律等等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国是个诗的古国,有大量的诗篇从几千年前流传到现在,这些诗不仅是印在纸上,它最大的威力是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人们离开书本,能随时朗诵它,我们的新诗起码做到能使广大读者便于朗读、记忆、传诵才好。
一九六一年八月
从艺术上来说,读者对散文有几种要求:
一、思想情感境界高。在感情上给人一种激发、满足,有新的启发,读后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读者新的情操,如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二、扩大见闻。无论是社会的或大自然的,通过精确的描写,扩大读者的见闻,使读者得到满足。
三、扩大知识。历史、科学等等各方面各种知识。如叶圣陶写的《西安见闻》,虽不以抒情为主旨,可是读后给人增加知识。
有些散文作品,虽然也是描写了生活,但也只是形式上的,创作上形成了一个套套,客观生活描述少,主观抒情多,现实主义少了点,主观的东西多了些,对生活钻得不透,艺术上提炼不够,主题不集中,章法、层次不分明,因此不够凝练。散文作为文章,也应该有“眼”,应有新颖独到的立意。
写作时的自信心很重要。学习前人,要在平时学习,而当你坐下来写作时,就不要考虑高不高、朽不朽的问题了,所写的东西,只要自己欣赏,自己觉得有味道,攒劲,不老一套,就一直写下去,不要三心二意,想像力不要被打断,一中断就放了气,就像炼钢,炉缸不能冻结,一结块,要再一次熔到可以流动,就得费很大的劲了。
平时要多思考,写作时的心境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心理上不受今人也不受古人干扰才行。这不是狂妄,而是进行艺术创作时所绝对必要的心境。
观察是否敏锐、独特,全要靠作家的眼光,如《创业史》中塑造的高增福,有这么一个细节:他平常总是不穿上身衣服,家中只有一件干净的白衫,这就是他的“礼服”,只有到了会见什么人或开会时才穿,这表现了他贫困而又节俭的一生。这个事情很平常,但却很典型,柳青敏锐地观察到了,并使其典型化了,用得很巧。我们如果平素观察不精确,用时就不能准确、生动、典型了。
散文古来有之,赋实际上也是散文。另一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文坛上出现的报告文学,如辛克莱的《屠场》、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夏衍的《包身工》等,介乎小说和新闻通讯之间,既强调通讯报导的真实性,同时又强调运用艺术手段的形象性。而我们现在有些特写或报告文学和通讯差不多,没有用真正特写的手法给人强烈的印象;而有些却只是生活现象的表面的泛泛的描写,缺乏扎实的社会生活的文献性的内容。
散文的内在感情深沉不深沉,不仅是感情是否丰富的问题,也还有思想内容问题。散文作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对某一生活事件感动与否,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素养、生活经历也有关。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对生活中的种种事件无动于衷,是不能为诗也不能为小说和散文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对某一生活事件当时感动不深,而在回头再创作时,又被深深地感动起来了,这就更加深沉得多。感情和思想的联系正如《先知》一书中所说,感情是帆,思想是舵。光有感情的帆不行,还要有思想的舵去掌握才好。
有灵感这个东西吗?如果定要说什么“灵感”的话,那么灵感的出现也有个规律,这就是创作欲望的触发、冲动,意志力和想像力的保持,充满旺盛的精力和创作情绪。
创作也并非绝对的不能出题作文,如果十分了解一个作家的情况,出题作文,也未尝不可,如莫扎特,这个大音乐家,多是别人给他出题作文,而作品至今流传。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想象,都很丰富,出题作文也可以,领导者应善于启发、诱导作家,善于点燃作家艺术创作的欲火,诱发他的诗人的灵感。可灵感也不是坐在那里就能祭起来的,作家有时也还得自己强迫自己坐在那里写。李白写《清平调三首》,王勃写《滕王阁序》,曹植的《七步诗》,也都是“遵命”之作。
集中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写作上也应像做“气功”的静坐功似的讲究个“入静”,无其他任何杂念才行。一张白纸摆在水墨画家面前,他脑子里已想好了,画好了,现在只是摹写在纸上。而写小说却不是这样,不一定要把什么都想好才写,开始把人物故事轮廓、情景、转折、结局想好,写起来,想象展开,新的东西就出来了。古人所说:情生文,文生情,就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要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光靠有一点技巧来编是手艺匠,我们不能那样做。
真人真事,我不写,一来嫌麻烦,二来我下去工作一般的不记材料,要广泛接触人,靠记忆。三则是真人真事多半有局限,不能很好地进行典型概括。
真人真事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写?也不一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写得高,用艺术创造的手法去写还是可以的,写那种具有真正强大性格的人,如《李狄山》,抓人物的性格,写出了那种性格,那种人。这一点跟写那种虚构的典型人物是一样的,要明确地表现人物是什么性格,性格刻画要强烈、突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先生抓住了阿Q那句“儿子打老子”在全篇作品中反复出现,这就很是强烈。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也是这样。
作品中的强烈,突兀,在现实生活中虽不一定是司空见惯,但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抒情不一定要用豪言壮语,豪言壮语也可以用,但一定要用得恰到好处,否则就会显得空洞累赘,摒去豪言壮语,即便是平凡语汇,如果有真挚的思想和感情,那便会掷地有声,如像《绞刑架下的报告》一剧中,伏契克最后一句台词:“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这用得多好,多深刻。
一味豪言壮语,一味大喊大叫,把“情感”强加于读者,是艺术表现力不高的一种表现。作者自己首先应该有充分发展的艺术感觉,判断出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感动读者。作品意图不能靠自己说出来告诉读者,只能靠形象和情节表现出来,仿佛在无意之中表现出来,作者要有这个把握,无论是政治思想也无论是自己的感情,都不应强加于人。
浪漫主义也应该以现实生活作基础。浪漫主义和现实生活,是酒与高粱的关系,酒既不是高粱,又是从高粱升华而来的。生活的酒是从客观现实生活中酿出来的。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诗”,浪漫主义就出来了。
要善于讲故事,小说家首先是个讲故事的人,我们确实也还不善于讲故事。小说,向民族传统学习,首先是学习讲故事。故事性强的小说,喜欢读的人多,可惜我们有的作品,讲不成故事。解放前有位在市民中有势力的小说家叫张恨水。他的作品可以认为是小市民的消遣文学,进步青年看不上眼,我过去是瞧也不瞧一眼的。一九五一年因患病滞留北京,有机会涉猎一番,了解了解,我让宾馆招待员在劝业场租了几十本来读,一夜看一本,有时读到天亮,就因为故事编得很抓人,而且是民族形式,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可见把故事情节编得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会讲故事的本领,但不要讲那些没意思的故事,越是动人的故事越要讲个思想性。要主题、人物、故事都能引人入胜才好。不要单单为了编故事而去编故事,要通过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去塑造典型人物,表现深刻的主题思想。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雷特》才是最出色的故事。讲故事,既要讲得娓娓动听,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意味深长,才算是上乘之作。
要在自己的山上唱自己的歌。打雷的声音,春风流水的声音,声高调低不一样。自己的调子是春风流水,不必勉强去学打雷闪电,也不必都去打雷,作家如果都去学打雷,文学产品反而不多样化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强求一律,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善于唱哪个调,你就来哪个,没必要人人唱黑头。硬要唱高调,唱出来空洞嘶哑,很不自然。不惟不同作家有不同风格,就是不同的文学艺术体裁,也各自具有不同的艺术功用。一件文学或艺术作品能给读者以社会主义教育当然好,但若纯然给人以心情舒畅的艺术享受也是好的。
作品写得轻快,同时也可写得深刻,写得丰富。
要想把人物性格突出,就要给人物安排不同的生活场合和种种不同的遭遇,展示主人公在他的各个重要生活领域里的机会、命运,对他的性格及其前程的影响,他的位置等等,像《阿Q正传》那样;或者给人物提供各种场合,利用不同的场合,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如像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华西里?焦尔金》那样;又或者就像契诃夫的《宝贝儿》,环境一变再变,人物性格及其精神境界却不变,以极短的篇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分典型的性格。
要不断追求新东西,写那些应该写而人家却不曾去写的题材、典型,别人不去的地方我去,前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去开垦,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兴旺发达,新颖多样。但这不应是猎奇,比如白痴这一类题材,就没有什么意义,写生理上的白痴,在咱们的社会生活里,写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这在生活中不占多大的位置。我们不能见啥写啥,看见啥样就写成啥样,不能去追求自然主义,要追求生活中主要的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东西。
学习别人的长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发展自己的风格。
写作时,我的心灵中如果是饱和着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美的感受,如果我自己从生活中感受到的诗意的爱和憎全部涌进我的作品,那就必然会自自然然地产生那真正称得上是我自己的作品,铸出我自己的风格。
生活要浑厚些,思想要深沉些,风格笔调要独特些。游击队员们可以唱“风在吼,马在叫”,也可唱“游击小组乐”,认定了是自己的风格,就干下去。
要写自己熟悉的,适合自己写的,写起来拿手的,不要反串。适合演小生的就演小生,长于老旦就演老旦,可以学学各门艺术,但自己适合干啥还是去干啥,主意要自己拿牢。
我们有些作品,从情节上讲,常常后劲不大,缺那么最后一扭。收摊子怎么收法,很重要。转折、结局,是一篇作品的支撑点,要苦心经营,使其出现一定做到是在全局发展的情理之中,而又在读者或观众的意料之外。作品结束时,不要画蛇添足,但如果必要和可能,还要再加一把火,添一点“搭头”,以增强余味,深化主题。
假如生活中有九点缺点,可那一点优点,就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值得高高举起。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漫长的过渡时期里,生活中共产主义新事物的萌芽,共产主义新思想的表现,和几千年来私有制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比起来,占的位置是很小很小的,但它也因此而更加宝贵,我们的作家要抓住生活中闪现着的共产主义的东西,帮助它战胜私有制的传统观念,逐步扩大地盘。革命的作家,是对生活抱有崇高理想的人,他珍视和推崇现实生活中符合他的革命理想的人和事,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作家的理想,当然不是粉饰生活。
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
到生活中去,要能看到那些能代表未来的先进的力量,看到革命理想的闪光。我所十分熟悉的一个村庄,这次整风揭了一个大盖子,是大队的支部书记。此人早先在土改时斗争性很强,很坚决,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入了党,当了书记,这几年变了,很霸道,欺压群众,蛮不讲理,群众同他斗了多时,未曾取胜,这次农村整风,贫下中农联合起来,跟他斗,县上又派了几个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终于把他斗倒了,撤销了他的党内外职务,只保留了党籍。我们就要写贫下中农的斗争,写他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当家做主的态度,或者说,写我们党领导和依靠贫下中农或其他革命群众同坏人坏事进行坚决的斗争。塑造党的形象,塑造贫下中农的形象,塑造这样的英雄典型。据我所知,这些贫下中农中有些人自然也有缺点,甚至是很大的缺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当代英雄,我们更要珍视和发掘他们身上那些宝贵的东西,他们的斗争是那样顽强、机智,他们的生活性格是那样的丰富多样。
戏剧的矛盾冲突问题,剧本的戏剧性问题,是我们的剧本创作,长期以来亟须解决而未很好解决的问题。
费了很大劲,写出来的剧本却流于概念化,无冲突,这是同如何理解矛盾冲突有很大关系的。不错,一部戏剧作品(小说也一样),归根结底,应该揭示一定社会内部的阶级或集团的矛盾,表现一定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巨大冲突,但是,却决不能因此而把戏剧冲突理解为概念的冲突。艺术作品反映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要通过千变万化的个别人和个别人的具体的特殊的冲突,也就是说要用部分暗示全体,用个别暗示一般这个艺术反映现实的规律表现出来。譬如通过喜儿、杨白劳一家和黄世仁一家的冲突,来揭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单这样讲还不够,对小说、戏剧、电影、叙事诗来说,讲冲突更重要的还是要讲性格的冲突,也就是说在阶级的集团的利害冲突这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作品中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形成和事件的曲折发展,以及双方最后的胜负和结局,都明显地含有斗争双方的性格的因素。首先要牢记一条,艺术作品不能搞概念和概念的冲突,按概念来图解生活,或用艺术作品来图解政治概念。现在不少作品中的矛盾冲突还是概念和概念的冲突。有一些作品已经突破概念化这一关,进入了第二层,注意了写矛盾冲突,可是还没有再前进一步进入更高的一层,写性格冲突,或者叫做互相冲突的个性。
《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书,但是,人物上场,谁也从不讲一句反封建的话,作者在表现他们之间各自不同的利害冲突时,十分严格地把握着各个人的性格上的差异和由此而生的一场斗争的曲曲折折的历程和结局。再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书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到他的朋友阿尔卡狄家去度假,和代表守旧派的人物、阿尔卡狄的伯父帕威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发展到进行了一场荒唐的决斗。这两个人物见面伊始,就在性格上合不来,相互蔑视。帕威尔说到巴扎洛夫时,轻蔑地说:“那个头发乱蓬蓬的东西吗?”而巴扎洛夫则对阿尔卡狄说:“你那伯父真是一个怪物……他的指甲,指甲,你应当把它们送到展览会去!”屠格涅夫就是这样察微辨细地从这些细微的性格不合之处入手,一步步写到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敌对而最后发展到火并的。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等无一不是写性格冲突的。《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则是写性格冲突的最出色最伟大的作品,《空城计》《群英会》都是写性格冲突的典范之作。我们写东西时的最大坏毛病是不大顾及性格,不像《阿Q正传》那样,情节和性格拧得很紧,很紧。
文艺要揭示社会矛盾,必须创造出典型。
为了加强作品的戏剧性,一般的作者都是靠卖关子,要想戏剧引人入胜,在情节结构上不卖点关子,不在观众的心理上造成强大的悬念当然不行,但一味靠卖关子,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真正的戏剧性,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戏剧性,莫过于把主人公置于十分严重的“危机”面前,要人物在个人利益和道义之间作出重大抉择,像京剧《搜孤救孤》中程婴舍子,公孙杵臼舍命,《伍子胥》一剧中的渔丈人、浣纱女投江,《献嫂》中的周仁舍妻,《杀庙》中的韩琦自刎等等。主人公在行动以前,要用巨大的道义力量来作出他的选择,表现他将牺牲什么,维护什么,这就把人物举得很高了。比如《杀庙》一折,韩琦只不过是陈世美的一个小小的家臣,他与秦香莲素昧平生,主人差他去杀害秦氏母子三人,他只是出于道义感和对受迫害的弱者的同情,而放走了秦香莲母子,自己则伏剑自杀。我们写戏,就要使人物处于各种“危机”的情况下,着力刻写人物的对于自己行为的决定性选择,以此推动剧情走向高潮,表现出戏剧冲突的力量。
要向传统戏和民间戏学习,像《隔门贤》那样的戏多好啊。
作品中如何处理英雄人物的死很重要,要写死是生的继续,死是人物性格的最后完成。牛虻、刘胡兰、吉鸿昌、黄继光,或如像荆轲刺秦故事中的樊於期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命运,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由神支配的,这也是“命运”的本意。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在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笔下,个人命运就不是人和天神的问题,而是个人和周围环境和社会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了,像《安娜?卡列尼娜》《马尔达》等。现在又不同了,命运和群众连在一起,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和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一般的说来,他们和周围环境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生死攸关的冲突,但他们没有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问题,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具有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会有什么根本冲突,我们如果在看待这问题上出了岔子,就是个严重问题。假如一部作品的故事,是写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终于被他所参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毁灭,那么这部作品的主题无疑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的否定。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在劳动人民中,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之中,由于自己来自旧社会,思想上还有着旧的传统观念的因袭的重担,或者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而在自己的生活斗争中酿成悲剧的结局,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实,而且是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这是从不同侧面对新生活的肯定。《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创业史》中的王二直杠,《前线》中的戈尔洛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拉古尔洛夫等等,就是这样的典型。
塑造无产阶级新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作家的新课题,要我们去创造,在前人那里是学不来的。
社会主义还在初创阶段,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是艰巨的,冲突是激烈的,大有写头。
接受传统,也不应当生搬硬套。现实生活处处有巨大的冲突,当代英雄人物的生活道路,战斗的历程,也有许多是很曲折、很艰难、九死一生,震撼人们的心灵的,要把这样的现实人物的现实生活写得像生活本身那样震撼人心,像古典作家的作品具有的那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要向古典作家学习,过去的艺术遗产要接受,要创造,要发展,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也许我们这一代不行,也许过几十年后,就能在艺术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东西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震撼力的问题,和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有关,可也同无产阶级文艺历史尚短,艺术上尚未积累下更多的经验有关。
(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