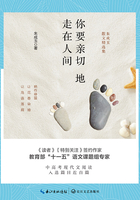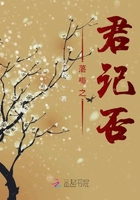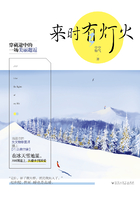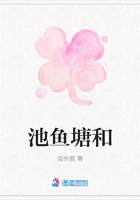一、刘知几的史传文学理论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宋代黄庭坚曾把它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指出:“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史通》所评论的是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而这些著作大都属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也就涉及了史传文学的创作与评论问题,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今天,其中的一些理论仍具有其不朽的价值。笔者将其史传文学理论归纳为以下八个字:“通”、“直”、“深”、“简”、“识”、“文”、“新”、“则”。
一、“通”:传记批评的基本方法
《易传·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变化,“通”是通畅不阻塞,如《系辞上》所说:“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传》第一次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中提出了“通”的思想,并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此后,司马迁的《史记》将“通”用到历史著作上,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描绘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古今社会变化的规律。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易传》关于自然变化的思想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变化,使《史记》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又将“通”用到文学评论上,以“通”观“变”,以“变”观“通”,对先秦汉魏六朝文学进行系统总结。刘知几继承了上述各家思想,将“通”用到史传文学批评上,第一次以“通”的观念,对唐前史传文学进行全面审视。全书几乎每篇的论述,都讨源探流,比较优劣,勾勒发展过程。体例上犹如《文心雕龙》那样:“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如内篇的《六家》、《二体》就是“通”的典型,是一部浓缩了的唐前史传文学发展史。《六家篇》一开始说到:“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犹如老吏断狱,极有分寸。然后高屋建瓴,对六家的渊源发展进行系统疏理,对每家的特点予以分析。如此以来,使读者对远古至唐代的史传发展有一清晰的线索。《二体篇》将唐前繁富的史传作品归纳为编年、纪传二体,指出这是时代发展和文体发展的必然,并对每一种体例的长处、短处加以评述,亦显示出“通”的特点。《外篇》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对远古至唐代史官建置的历史进行了总体勾勒,对《史记》以来的正史著作逐一加以评述,在“通”的历史中看出各部著作的不同特色。这两篇与《内篇》的《六家》、《二体》相得益彰,成为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历史。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的序言评此书曰:“其荟萃搜择,钩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刘知几站在“通”的高度,所以,对每部著作的评论,乃至于对史传的每一种体例、写法,都放在历史著作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以显示其独特之处。如正史中的“本纪”体例,刘知几在《本纪篇》评述道:“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著《史记》也,有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这是对“本纪”体例渊源的探寻。然后对“本纪”体例的写作提出一些要求:“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并对史传中一些不合体例的地方进行指瑕。《论赞篇》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又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论,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将论赞的源头追溯到《左传》的“君子曰”;然后对论赞的特点予以概括,再举史传以证之。不难看出,刘氏《史通》以“通”作为最基本的传记批评方法,因而能使读者对繁富驳杂的唐前史传著作有一清晰的认识。刘知几的传记批评方法,对今人有很大的启示。要评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就必须站在整个文学发展的制高点上,将作家作品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上,放在不断变化的潮流中,察其源头,观其流变,这样才能看得清楚,看得仔细,才能把握住作家作品的真正的特点,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
二、“直”:传记创作的根本原则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传的优良传统,也是史传评论的重要标准。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评司马迁《史记》的创作:“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继承了这一传统,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把真实作为史传的根本原则,要求传记创作做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推崇南、董、司马等“不避强御”、“无所阿荣”的直笔精神:“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但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却赢得了后人的称赞。由于强调直书,所以,他把那些虚假、浮华的历史记载,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在《古今正史》篇中指责王沈《魏书》等“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在批判不实之风中树立起自己“直”的创作原则。这种原则,是中外传记家的共同之处。如卢梭的《忏悔录》,作者在序言中庄严宣布:“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它可以作为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资料。”正因为它的真实性,使这部著作成为传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直”乃是传记的生命。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传记作者是至关重要的,它既强调了传记作者应以真实为生命的传记原则,也揭示了作者与传主人性的多个层面,也要求传记作者摆脱情感的束缚,理智地去对待传主。如此看来,“直”,不只是材料的真实,事实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对于传主应有全面深入的把握,人是一个复杂体,传记作者既要知道传主伟大的一面,也要知其渺小的一面;既要看到真善美的一面,也要看到假恶丑的一面。但并不是各个方面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从这个角度看,唐前史传文学中,《史记》的“真”表现得最为突出。司马迁写李斯,既写其对秦国统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写其苟合求荣使秦国灭亡的不可饶恕的罪过;写吕后,既写其残忍阴毒的个性,又称赞她轻赋敛、重稼穑的政绩;写刘邦,既写其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的帝王风范,又写其阴险狠毒、迫害大臣的小人气度;写项羽,既写其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又写其暴戾残忍、缺乏政治头脑的庸人私心。如此等等。
当然,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并非易事。
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传记作家个人的情感倾向,政治环境的压力,道德观念的束缚等等,写当代人物更是如此。
因此,刘知几对儒家经典《春秋》提出“十二未喻”、“五虚美”的指瑕时,又不得不做出些让步。《曲笔篇》云:“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种为尊者、亲者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直”的原则是一个大冲撞。但从总体上说,刘知几还是以“直”为贵。“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沈约)《宋书》多妄,萧武(梁武帝)知而勿尤;伯起(魏收)《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对《宋书》、《魏书》等不实之词大加指斥。
三、“深”:传记创作的必由之路
真实,这是传记创作的基础,也是传记成功的基础。进一步来看,传记创作还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向深度发展,走“事丰”、“旨远”、“义深”之路。这是史传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所谓“深”,是指史传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事件、人物的表层现象上,而要以人为核心,纵横开拓,全面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写出人物的来龙去脉,写出人物的生命历程和内心世界,写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透过事件、人物,挖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给读者以生命的启迪。同时,作品还要有作者自己明确的思想。像《史记》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应该说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它不仅如《二体篇》所评“《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广阔性、全面性,而且具有思想的深刻性、超前性,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人企及。“深”,还体现在人物选择上。“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也”。社会生活中,人物复杂多样,史传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事件进入传记,都要有明确的思想目的,也就是说,人物的选择要有典型性。进入传记中的人物,要代表一个类型、一个阶层、一种思想,给后人树立榜样,而不能鱼龙混杂,或滥竽充数。在这方面,《后汉书》具有典型性。东汉一代历史,与西汉相比,在许多方面有了不同,因此,范晔慧眼识史,创立《党锢》、《宦者》、《列女》、《逸民》、《文苑》等类传,反映了东汉时代特有的历史现象,使这部著作在深度上超越了当时众多的同类著作。“深”,不只是传记作家,对于传记评论家也是如此。因为“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如果不能“深”,就难以理解传记作品所包含的深意,难以辨别事件的利害、人物的善恶。只有以“深”求“深”,才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数”。因此,“深”,既是衡量史传作品成功的标尺之一,也是衡量评论家的标尺之一。
四、“简”:传记文学的叙事风格
《叙事篇》指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针对魏晋以来“日伤烦富”的文风,刘知几指出四种弊病:侈写符瑞,常朝入纪,虚衔备载,赘录世官。为了避免这些弊病,他强调要以“简”为标准,消除臃肿。关于传记的叙事方法,作者认为有四种:“有直记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用一种方法将事件叙述清楚即可。为实现“简”的目标,他提出“省字省句”、“用晦”等一系列主张。作者认为,像《春秋经·僖公十六年》曰“陨石于宋五”,这是非常简要合理之句,“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这是省字省句的典范。作者还强调:“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钓必收,其所留者惟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要善于抓住关键线索,摈弃不必要的枝节。所谓“晦”,并非晦涩之义,而是指作品要用简练的语言表现深刻的内容,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刘知几举《尚书》、《左传》、《史记》、《汉书》的例子予以说明,如《左传》中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公二年)、“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公十二年);《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项羽本纪》写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等。为了实现“简”的理论主张,刘知几在《点烦篇》专就史传中拈出多例,加以增除,尽管有些不合理之处,但其大胆创新的精神则值得肯定。
当然,不能为简要而伤害内容,要力求达到“文约而事丰”、“持一当百”、“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境界。这是叙事文的最高境界。
刘知几所提倡的“简要”叙事风格,一直是中国散文的传统。但对于传记来说,还应有“详细”的一面,不能只写人物做了什么,还要写出他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乃至于要用一些细小的生活逸事来表现人物的个性。有时过于简,反而影响人物形象的刻画,像《三国志》那样,虽是叙事简练,但在刻画传主形象方面比起《史记》、《汉书》逊色不少。
五、“识”:传记作家和批评家的首要条件
刘知几曾提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一个传记家,必须具有才学,即广博的知识,《核才篇》一开始就感叹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并引《晋令》:“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以说明史才的重要性。但如果“学穷千载”而无识见,不过是“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因此,“识”应在才、学之上。所谓“识”,是指史传作者对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独特的见解,同时,也包括着对人物的全面认识和分析。一句话,指作者的主观条件。上文说过,传记作品要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深”而“识”就是求深的关键。有了“识”,才能“探赜索隐”,“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才能在“征求异说,采撰群言”的基础上“善择”。才、学、识的完美结合,构成了一个史传家的知识结构。这是金字塔型的结构,“才”、“学”是宽厚的塔基,“识”《新唐书·刘知几传》是突出的塔尖。“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这样的史官,既无“识”,又无“才”、“学”,怎么能够写出有内容、有思想的史传作品呢?“识”体现在“博采”方面:“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才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撰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有了“识”,才能博采,而且采来的是真材实料。选材如同“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识”还体现在写作上。那些华而不实、乃至互相矛盾之作,就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所致。“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可见,“识”对于传记作家是十分重要的。
批评家也是如此,如无识见,就会“妄生穿凿,轻究本源”,难以对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乃至于“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刘知几所提倡的才、学、识的统一,对后来的史评家产生重要影响。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以此为基础,又加一“德”字,使史传批评更为完善。德、识、才、学四个字,一直成为衡量史传作家的重要标尺。
六、“文”:传记作品不可缺少的色彩
刘知几反对骈丽、藻饰之文,这种鲜明的态度在书中随处可见。如《叙事篇》指出:自从《史记》、《汉书》以后,“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以蔽之,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杂说下》指出:“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核才篇》指出:“世重文藻,词宗丽淫。”《载文篇》指出:魏晋以来的文弊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但他并非一概反对必要的文采。他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言”,如果传记缺少“文”的色彩,也就失去了感人的力量。他主张在内容真实的前提下,也要追求完美的形式,并引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说“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可见润色也是必要的。他在书中对《左传》、《史记》等著作中一些文学色彩浓厚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富有形象性的语言,予以充分肯定。刘知几对史传中“文”的总结,实际涉及了历史美学问题。历史著作无疑是以真实为根本,但又不能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为了使历史记载生动、感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在内容真实的前提下,也要追求文采,“生死而肉骨”,使外在的美的形式与内在的真的内容融为一体。“真”与“文”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真”是内核,“文”是外壳。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刘知几对《左传》、《史记》等一些文学色彩较为浓厚的著作加以充分肯定,如《杂说上》评《左传》叙事:“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薄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对于《左传》中富有文采的外交词令,刘知几评为“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屈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复。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可见,刘知几主张的是真实与文采的完美结合。
七、“新”:传记文学的个性特征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宗经”、“征圣”等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刘勰的《文心雕龙》、专列《宗经》、《征圣》篇,阐明圣人经典的重要性。刘知几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强调传记创作要学习模仿古人经典。“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与”,“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但可贵的是,他又提倡师古而出新。
在《模拟》篇中把模拟分为两种:“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后者才是“模拟之上”,即从精神实质上向古人学习。学习古人也是为了创新。如果墨宁成规,不思创传记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不仅内容要新,语言也要新。刘知几在《杂说》中强调用当代语言来记言记事,因为一切事物“因地而变,随时而系”,语言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如《言语篇》将古代语言分为三个时期,“上古之世,人为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时代在变,语言风格也在变,不必一味学习古人语言。基于此,他对于王劭、宋孝王大胆采用“方言世语”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新”才能真正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新”即“变”,“变”则“新”。“新”则能“自成一家”。“六家”如果墨守前人,不思新变,就不会自成一家,每一家都是在继承前代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体现出史传作家的创造个性,也体现出时代变化的特征。“二体”亦是如此,由于时代政治的需要,以及史传本身发展的需要,编年体、纪传体成为撰史的主要形式,即使在纪传体中,断代史之所以能独占鳌头,也是由于它适应了时代政治的需要,即将本朝天子放在首位,体现本朝利益。随着体例的新变,史传著作也就有了新的思想、新的手法。《古今正史》篇所勾勒的从上古到唐代的历史著作的变化,也是在“变”的过程中出新,每部著作都有它出新的地方。
八、“则”:传记创作的终极目的
史传创作,要“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有益于褒贬”,“无损于劝诫”,以教化为目的。“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传记的直书、善择、载文、体变等,都要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因为任何传记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现实。传记,总要给人树立“善”或“恶”的榜样,以起警戒作用,这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春秋》一字褒贬,使乱臣贼子畏惧,“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明确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官文化的这种传统,对史传文学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以“直书”而言,只有真实记载历史,才能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只有真实写出人性的善恶,才能给后人以警示。以“善择”而言,选择“善”或“恶”的典范以垂示后人,无非是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人物,这也有思想来源。春秋时代形成的“三不朽”思想(立德、立功、立言),首要的是“立德”,即要达到不朽,就必须在“德”的方面给后人树立榜样,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传记产生的思想基础和追求的目标。因此,刘知几以此要求传记也并不过分。再以史传中收录作品而言,刘知几在《载文篇》中指出:“文之将史,其流一也。”“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也。”这是正面的例子。“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认为史传中收录作家的文章,也应以劝善惩恶为目的。这有片面性,没有看到史传收录作品是“以文传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文学向着自觉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这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强调传记要为现实服务,为后人树立典范,这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对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除以上所述外,刘知几对传记文学中一些不同的体裁也有一定的认识,《杂述》篇将史传以外的杂传划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薄十类,并对每种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概括(其中将地理书、都邑簿列入传记,是不够准确的)。《序传》篇对“自传”这一文学样式也进行了分析,等等。这对于我们认识史传以外的传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刘知几的史传理论,涉及创作论、批评论、文体论等,在传记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前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今天的传记创作很有启发意义。总的来说,要写好传记,除了传主本身具有生命价值外,传记作者一定要把握传主的生命脉搏,做到求真、求深、求美。
真实,这是传记文学的生命。失去了真实,传记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人们推崇司马迁的《史记》、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等,就在于这些传记能真实展现传主生命活动的历程,不虚美,不隐恶。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他的传记作者说:“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他们都不真实。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写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求真并非易事,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情感因素的存在,使作者对传主产生爱憎,褒贬失度;集体意识的影响,使作者有时很难突破世俗偏见;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的传统束缚,使作者难以完整写出传主的优缺点;受虚假材料的影响,传记中往往掺入一些水分;受某些读者好奇心理的影响,传记中难免出现媚俗倾向,等等。尤其是写当代人物传记,政治环境、传主亲属等都会给作者的求真带来影响。因此,要写好传记,作者首先要有勇气和胆量,排除各种干扰,以求传记的真实。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当代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为真实而踏破铁鞋的可贵精神。真实,不仅指事实材料的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掌握传主的真实性格。黑格尔曾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人物性格具有复杂性。处在时代坐标上的人,总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联系,没有抽象的、单纯的、孤立的人。每个人的性格世界都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多种元素,他们的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所以传记作家不仅仅是写出事实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要掌握研究“人”的学问,写出人物性格的完美和谐,写出人物的丰富性格和生命指向,揭示出生命的真谛来。有些传记,把领袖和革命先烈写成先知先觉的革命家,仿佛这些人物一生下来就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有些科学家的传记,科学家一生下来就是神童。这样的传记,忽视了传主的生命个性,缺乏对“人”的综合研究,因而也就失去了真实性。
求深,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挖掘生命的价值,探索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由表及里,由外入内。近年来一些急功近利之作,以赎卖隐私来抬高身价;对于领袖人物,也只靠披露“宫墙”内的材料来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或仅在生活琐事、婚恋逸闻上作点文章,虽有一时轰动效应,但很快失去存在的价值。传记文学的“深”,有多方面的内涵。就传主所处时代的深而言,它是传主生命活动的背景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它的来龙去脉。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生存,这段历史有它的渊源性、继承性,只有搞清了这些基本的面貌,探明了河流的发源,我们才能确定传主在这段历程中的立足点或落脚点。第二个层次,是时代生活的广阔面貌,也就是搞清这段历史的延展性、重要性,探寻这段河流的宽窄、深浅、流量,以便确定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进而对处在这个历程中的传主进行估价。第三个层次,是时代生活的发展趋向。探明发展的趋向主要是为了看这段历程对以后历史的影响,进而确定传主与时代潮流的方向,是顺还是逆,并对这种顺逆方向做出公正评判。就传主的深而言,包括五个层次。第一是承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明显的,也有隐蔽的。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抗争的一面。总之,客观外在条件对每个人的生命活动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二,是传主给予社会的能动作用。人具有丰富的潜能,人的生命力的冲动和活动,就是自己潜能的外显和开发。当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时,也给社会环境一个能动的作用。这个作用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且,有些作用并不一定在当时就能显示出来。进一步来说,有些作用是直接的,有些则是间接的;有些是肉眼所能看到的,有些则是潜移默化的,等等。这就要求传记作者在评判传主的功绩时,必须高瞻远瞩,综合分析,否则就会出现偏颇。第三是传主与其他人的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只有在纵横交错的时代网络中把握传主一生的发展节奏,才能真正把握到他的生命脉搏。第四,为了进一步挖掘传主生命价值,还必须对生活进行升华。这是对传主的一生进行的浓缩与稀释、概括与丰富。为了突出传主的某些特征,可以去压缩不必要的时间交代过程,延长或放大富有生命特征的事件、心理。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把传记写成“生平与时代”的记录本,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传主生命中光辉的一面。第五,以心理学家的身份深入到传主的内心世界,探寻传主“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揭示传主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在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适当进行合理想象,以补充事实链条的不足,但绝不等于瞎编乱造。
传记文学在求真、求深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求美。当代传记作家李辉先生说:“资料,死的,冰冷冷的;故事,活的,热乎乎的;我真想将两者都搂住,跳一个美妙的交谊舞,活脱脱地托出一个真实的人物。”为了给死的资料以活的生命,传记作者还必须借助文学的手段,以美的语言、美的结构、美的形式,使传主的生命价值得以很好地展现出来,“生死而肉骨”,并产生美感效应,能够使传主、作者、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互相沟通。美感效应的大小主要与传主、作者有关。
就传主而言,他必须是一个具有个性、又具有社会共性的典型艺术形象,必须是能够在生命的历程中搏击的健儿,这样,传主的形象就更具有美学意义。就作者而言,只有使自己的审美理想与传主的审美属性相一致,并且用完美的艺术形式使其物态化,才能使传记产生美感效应。这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如果仅仅使自己的审美理想与传主的审美属性相一致,而无完美的艺术形式,传记就显得干巴,不能打动人的心灵;如果仅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作者的审美理想与传主的审美属性不一致,没有“真”与“深”作基础,那么,形式再美,也只是一个外套,没有真正的心灵沟通!中国古代有许多墓志铭,语言、结构等都很美,但无实际内容;有些歌颂那些并无善行的达官贵人,隐恶扬善,甚至曲意颂赞,这些都不能产生美感。就读者而言,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他还要主动地进入角色,身临其境,与作者一起去领略传主的风神。这样,三者紧密结合,彼此协调,就能获得美的享受。
传记作者求真、求深、求美,把传主的生命价值展现在读者面前,无疑会启迪人们的心灵,燃起生命的火焰。茅坤评《史记》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贝多芬传》译者傅雷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这样的传记效果,是任何说教形式难以达到的。
总之,要写好一部传记,作者要以史学家的谨严去求真,以哲学家的睿智和心理学家的细腻去求深,以文学家的笔调去求美,这就是唐前史传文学对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