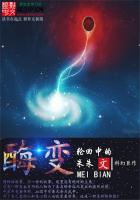林安安沉默了一会,默默地从冰箱掏出一瓶汽水,递给梁楚,自己在这当口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按常规地走安慰程序:“你已经把童颜带得很好了,你姑姑若泉下有知,一定会谢谢你。”
说完这话,林安安做好了心理准备,通常女主说完这样的话,男主就会乘机做痛苦状地抱住女主,口中喊着“姑姑”,顺便揩揩油。像谷米她们说的,被优质男揩油是一种福利,权当自己享受福利了,谁叫自己嘴贱,触痛人家的伤心事。
可惜林安安高估了梁楚的慷慨程度,他并没有想让林安安享受福利的意思。而是话锋一转,转到照片:“刚才那照片,怎么看起来像是要跳楼?”
林安安福利没有享成,又听到他一眼看出自己想跳楼的旧事,顿时觉得一报还一报,双方扯平,互不相欠。心里没了愧疚之情,嗓门都跟着增高:“你才跳楼呢,你全家都跳楼!”
这年头,骂人总是习惯延伸到人家家人,大有古代一人犯罪,连诛九族的味道。比如前几天,林安安在科室里听到长年炒股的小黄抱怨股市低迷,她买的股票全被套了。林安安出于好心,问她道:“你是不是买了中石油了?”林安安不炒股,她对股票的了解,仅限于中石油,中石化,可见这两只股票何等臭名昭著,连股盲都懂。
小黄一听,立即拍案而起:“你才买了中石油呢!你全家都买中石油!”
林安安当即一愣,随后就耐心地跟小黄解释,她家就她和老娘两个人,老娘就一个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对于操作股票这种高情商高智商的东西,她是万万玩不来的。而林安安,自认心脏承受力有限,比不上小黄的万分之一,炒股一事,决不可能越雷池半步。
小黄不等她解释完毕,骂了一句:“神经病!”然后就愤愤不平地给病人换药水去了,吓得林安安担心了一上午,怕她盛怒之下会不会把石油当液体上了。
梁楚无辜地被波及全家,半晌没有说话,只是逼视着林安安,许久,说了句:“你很自卑。”
梁楚的思维跳跃得厉害,林安安一时没能赶得上,被他落在半路,只得仰望着他,等待他解释骂人和自卑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梁楚的话再次证明了他的思维果然是以袋鼠的速度跳跃的,不仅没有给林安安解释,反而给她讲起了故事:“我以前见过一个女孩,恩,跟你有点像,眼睛像,鼻子像,恩,嘴巴也像……”梁楚说着又开始肆无忌惮地打量林安安。
为了听到他的解释,以便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林安安耐住性子听故事,刚听到一个开场白,林安安就不遵守听故事的礼貌打断人家:“你直接说跟我很像就行了。”相象这种事不必交代得这么具体。
“好吧,她跟你很像。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好象有满肚子的心事,一个人穿条米白的裙子跑到天台上吹风,我当时就想吧,这个女孩不愧是师大的,喜欢浪漫也不去别的楼,偏偏跑F楼。有勇气上F楼吹风的女孩不多,当时我刚好在F楼对面的美术室练习素描。只那么一刹那,那艺术细胞腾腾地冒着,瞬间长了几万个出来,我掏出随身带的数码相机,记下了难得的一幕。寻思着,万一这女的不是找浪漫而是想跳楼的,说不定还能抢到第一时间的新闻。
可惜,这女孩果然是吹风的,她吹了一会,就离开了。我报警的电话按了两位数,愣没拨出去,失去了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
林安安听到这里,惊愕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说的那个没事跑到F楼吹风,又临阵逃脱的女孩不是别人。
“然后呢?”林安安压着想找地洞的羞愧,小声地询问事情的进展,她很想知道,他怎么弄来自己的名字,又怎么把那张照片寄给自己的。
“照片洗出来之后,通过放大,我很惊讶地发现两件事,一是我居然可以把一个吹吹风而已的女孩拍得那么像想跳楼的,这就是艺术随着灵感而生的效果,我那么认为,它自己就拍成那样。另一个更重要的,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发现是那女孩有几分姿色。作为纯粹的男人,我已经错过一次救她的机会,就不能错过追她的机会。于是我拿着照片找遍了整个师大。”
林安安忍不住偷笑了,谁知道她不是师大的,而是医学院的呢。惭愧啊惭愧,早知道自己最后没勇气死,早知道有帅哥注意自己,她那时候应该在胸前挂块牌子,写着“我是医学院的”。
梁楚见林安安偷笑,心下早已心知肚明,又继续装死地说道:“没想到,偌大一个师大,居然找不到美女本人。这对我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我岂是那种受点打击就退缩的人?我想到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连我刚分手的女友都问过了,她听到我约她,还以为我想和她破镜重圆,得知我是向她打听别的女孩,她失望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好在她见多识广,打完之后告诉我,美女是隔壁医学院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被我找到了,为了追她,我忍辱负重,爬那堵隔开医学院和师大的墙,有一次,差点被保卫抓到,再后来,她们学校就装上防护电网。”
“你……你……”林安安震撼得暂时语言功能锐减,“你”了半天,硬是没有你出个实际内容。
“我刚才说过,我不是那种随便就放弃的人,一招不成,再换一招,唉说起来,我当年的聪明都用在追女孩身上,要是肯多下点功夫在学习上,也不至于只考到美国的二流大学。想了两天,如果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必须要光明正大地走进医学院。
光明正大进医学院的方法只有一个,再参加高考,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先用不光明正大的办法弄一个校徽,这个难度系数要小很多,医学院的校徽做一个是二十,临床系那哥们很义气地把他的校徽五十块卖给了我,自己再申请一个。就这样,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医学院。天天和美女坐在一起读书。”
林安安仿佛坐了一次云霄飞车,那车运行到一半坏掉,把她吊在空中,半天没法尘埃落地,她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关于梁楚的片段,可是记忆这东西,光靠努力是不行的,事实上,当时她整个心思都埋在书里,压根对旁边的人没有什么知觉。想到自己青春年华,居然忽略了这么一个良苦用心的大好青年,真是遗憾啊遗憾。
“她喜欢去图书馆最里面的倒数第三排第十一个位子,还喜欢去学校东边角落的老槐树下。她从来都是一个人,最习惯的动作是把手抱在胸前,把书抱在手前。没有看书的时候,她会没有目标地望着某个方向发呆。”
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可以知道得这么清楚!不公平的是,他知道自己这么清楚,而林安安却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理论上因为觉得不公平的应该是梁楚才对,可是为什么林安安觉得愤愤不平?
“你注视她这么久,怎么不上前跟她挑明了?真是浪费大好青春!”林安安严肃地批评道,“不仅浪费你的青春,也浪费她的青春,造成剩男剩女的局面,多不利于社会稳定啊。”
“我说了,只是她把我忘了。考察了她许久,了解了她的作息习惯,我还把她发表在校刊上的诗背下来。我自认为万事具备,终于鼓起勇气跟她表白,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笑一个贝?结果你猜她怎么着?”
林安安的记忆突然就被打开了,她依稀记得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确实有个穿着黑色体恤和一条无数个洞的牛仔裤,吊儿郎当的男生走到自己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林安安本能的反应是遇到色狼,于是气运丹田,大叫一声:“色狼啊——”
年轻没有经验的梁楚落荒而逃,总算想起一点残碎的记忆,却是这般不堪,林安安汗颜地继续挣扎道:“你总不能一次出师不利就放弃了吧,还自称不是受点打击就退缩的人。”
“我当然不是一次失败就妥协的人。经过那次失败,我总结出,会让她产生误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没有挑明自己的身份,以至于她觉得我是色狼。第二次,我换了发型,换了衣服,还为了表明自己是个学生,特意戴了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那天,她在槐树下,我叫了她一声:同学。她抬头疑惑地看着我,显然她没认出我就是上次和她搭讪的人,为了避免再次误会,我迅速掏出学生证,认真地跟她说:你看,我是有学生证的人,我是证人君子。”
结果呢,结果林安安想起来了,她很认真地骂了他一句“神经病”,扬长而去。
林安安又好气又好笑,偷笑了半天,总算从回忆中挣扎出来:就算这样,这和她自卑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