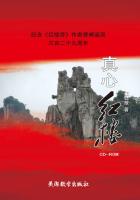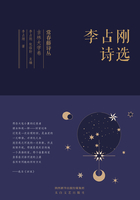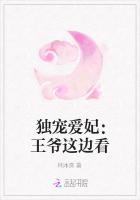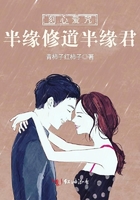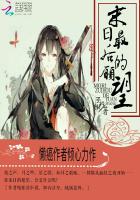引言
有勇气把骸骨留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也是好汉。
这尸骨,是从昆仑山凿下的一块庄严而强悍的硬石,为所有越过它的后来人作碑用。它是一块狂风吹不动的需要铁支架撑着的碑石。
是为序。
1990年6月的一个闪烁着嫩绿的晨星的早上,我在昆仑山深处的一块山间平坝上写下了这个序。此地掩埋着两个不知名的士兵,1954年修建青藏公路时他们死于一场暴风雪中。
岁月的风雨早已把那两个最初的坟堆荡平,但由于后来经常有人培土加固,始终有两个凸现在郊野的土丘展现在山里。没有草,更无树,只有两个点缀着山石的野坟孤寂地躺着。
我特地登上旁边的山峰去俯视这坟时,发现它的高度没有了,变得像是紧贴在地皮上的两张只有线条没有棱角的平面图。与此同时,我又发现它更像两块人造的坚硬的基石,托着整个昆仑山……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
第一节这就是青藏线
我刚从青藏线上深入生活回京,衣服上还落着昆仑山的雪迹。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七年。
我怀念洁白得凝重的雪山;我怀念水冷得美丽的冰河。我怀念寒流冻僵了牧草的帐圈……
这个夜晚,晴空嵌着银月,又鲜又亮,我总觉得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我蘸着月光在北京西郊的书房里写作。
尽管我拿的是一只小碗,但是我面对着大海。
灯下,我刚写下开头,突然有人敲门。一位记者来访。
“真不好意思来打搅你。我们准备发一篇有关青藏线的专访,可是谁也没去过那地方,我算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你这个采访对象。”
他说着递上来一封介绍信,同时另一只手把微型录音机已经很利索地放在了我面前。
我真佩服有些记者,他们像水中的游鱼一样,石头缝里也能钻进去。从来都是我采访别人,现在冷不丁地冒出个记者坐在对面,要我接受采访。尴尬,实在尴尬。
我收起了笔,需要沉淀沉淀。就像我在创作之前必须苦苦构思一样,我要琢磨琢磨怎样使记者的采访得到一个满意的名号。叫别人失望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记者说:最近一个时期,新闻媒介着了迷似地宣传一个对内地人来说十分陌生而又具有诱惑力的单位:“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真了不起,那些战士们在青藏线上默默无闻地干了35年!中国太大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伙兵在那儿折腾。当然,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热热闹闹地活着,但是如果让谁十年几十年地悄不声地孤孤独独地去干活,而且又是在别人不了解、自己不习惯的地方干活,这实在无异于受罪。青藏兵站部的万余名官兵却心甘情愿地耐得住这种寂寞,含辛茹苦地受这种罪,令人佩服!
他把录音机往我跟前挪挪,又说了下去:恕我直言,本人孤陋寡闻,以前真不知道:“青藏线”是何物,吃的还是用的?就我所知,我周围不少人像咀嚼着外国的一个地名一样猜测着青藏线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儿。总之,那块地方太神秘了,人们对它的了解不是缺少而是处于无知。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给我和我的读者谈谈青藏线。
我笑了。凡人变得神奇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从背影去猜度他的面容。青藏线的背影不仅太陌生而且可怕,难怪有人对它望而生畏,谈虎色变。
我告诉记者:很简单,青藏线就是世界屋脊上的三条线。
地面露着一条,天上挂着一条,地下还藏着一条。
地面天空地下有三条线?记者的嘴张成了个“0”,眼睛瞪得像镜头盖。
我必须不厌其烦地对这位甘当小学生的大记者进行启蒙教育——
地上的线就是青藏公路,全长2000公里,零公里的里程碑挺立在西宁市西郊兵站部的门口,终点上的里程碑埋在拉萨河谷,进藏物资的85%由它运输;地下的线是输油管线,起自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终止于拉萨,全长1080公里,承担着100%的进藏油料运输任务;天上的线是通信线,全长1680公里,担负着重要的国防通信任务……
他很认真地听取着,吸收着。要不,他干吗仰着头在沉思什么?我收住话头,抬头望着窗外通往将军院的那条路,月色溶溶,平平坦坦的路面像镀了一层雾气。两个下岗的哨兵正目不斜视地正步走着,我仿佛看见他们胳膊上的肌肉隆起着。
我想到应做几件事:把银月摘下来挂在我书房;把这院落连同这条路挪到昆仑山的某个地方;把昆仑山变成中山公园的一座假山……
都想些什么呀,高原和闹市要移位吗?我砸了自己的脑袋,笑了。
这时,我看到记者在自己的采访本上画了一座山、三条线。嗬,他把我的话图解了。
他继续提问:“我很想知道青藏线的艰苦程度到底是个什么样,比如说,好端端的人怎么到了那里就会死了呢?”
他把最后四个字咬得又重拖得又长,看来绕了半天弯,他的要害问题才托出来了。我听着有点炸耳。
“也许你自己去一趟就会体会得到的。”我有点不悦。
“我肯定会去的。”他说,一点也不在乎我那句失礼的话,“现在我先想听听你的体会,你是老高原,你咽的苦多,爬的山多,而且你又是个作家。”
我和他谈话的兴趣全无。于是我递给他一份材料,那上面有介绍青藏线情况的文字。就算是我对他提问的回答吧!我在不乐意和别人交谈时就用这个办法。我明显地感觉出来了,在这位记者的眼里作家都是狰狞的面目,就会夸张、虚构,就会说谎、骗人。他大概正是冲着这来找我的。
他的眼镜片几乎贴着纸面看着,很吃力。材料上的字收进了他的镜片:
“青藏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地带唐古拉山5200多米。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最冷的时候可达零下40多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水的沸点仅80度左右……”
他把材料往桌子角上一推不看了,又恢复了刚才仰着头思考问题的姿势。然后,他慢慢地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嚼碎,咽下,用眼角夹了一下我,说:
“我想起了一个人,斯诺,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当一个人到高原寻找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12人,回来的可能只有两人。’”
我一愣,斯诺?这位美国人也了解青藏线?可我这方面的材料翻阅了不老少,怎么就不知道斯诺还对青藏线有过评价?显然,这位美国人是夸大其词了,12人死掉10个?没有的事!我转而又一想,夸大自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引用这种夸大了的话的人是比搞夸大的人走得还远。
看来,外国人,还有中国人,对青藏线的印象就两个字:死亡。
我陷入了深深的、也是痛苦的沉思中……
那位记者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仿佛知道,又仿佛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我并没有明了而形象地给他解释清楚青藏线。
我绝对不否认青藏线是“死亡地带”,在我所查找的资料记载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把青藏高原称为“生命禁区”。但是,我认为,对于无所畏惧地把生命献给高原的青藏线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死亡”上,远远不够。死亡的内涵是什么,死者与生者有着怎样的心理历程,死亡与希望的关系如何,等等,需要我们探讨,需要我们揭示。春天来了,栽下一棵树;秋天到了,收一筐果子。难道人生就这样单调而又丰富、平直而又忧郁?
那夜,我失眠了,老是在琢磨着那位使我不感兴趣的记者的采访,还有我不大同意的斯诺的话。是的,青藏线人“死亡”的内涵是什么呢?
我的脑子里装上了许多问题,我爱生的欢乐,我不怕死的寂寞。可是,高原的夜为什么这样令人胆怯?我脑子里乱乱的……
死亡年复一年的不可抗拒的笼罩在各个时代、各种领域。
它是人生全过程的终结,每个人必须像完成生一样去完成自己仅有的一次死。
死亡现象如同生存一样代表着一种价值。
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编一部论述各种死亡的书。”据说英国作家俾雷尔和卢卡斯完成了这一使命。但是,中国人没有看到这本书。大概无人去翻译。
我在沉思……
需要破冰船,在死亡线开拓出生的里程。那些经历了的和听到的青藏线人与死亡搏斗、或战胜了死亡或被死亡所战胜的事情,像一团乱麻一样塞在了我的脑子里。我要把它们整理分清,就像编导在分理、组合镜头一样,使它们各就各位。
我在剪裁。睡意全无……
在这个浮躁而兴奋的京都之夜,我却想起了世界屋脊上的傍晚。那里的夕阳又圆又大,任何地方的夕阳都无法与它相比。牧归的昆仑牧女抽了一个脆响的鞭花,对我说:“高原在流血。”
我真佩服这少女的丰富想象,她从夕阳想到了流血,那么鲜嫩的形象!
沙梁上慢淌的水珠犹如驼铃叮当……
我用心之剪刀在剪裁……
〔镜头1〕俘虏一个也没伤着,他却死了。
这是30年前的事了,它经常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绞着我的心。冥冥之中我还看见他睁着那双可怕的眼睛。
他匆匆忙忙死在青藏线上,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告别一声。
18岁的年华对他该有多少吸引力,他肯定是十分不情愿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我和他是上初中时的同学,同年入伍后分在同一个营的两个汽车连队。第一次出车我们编在同一个车队,记得就是他出车的头一天晚上,高原的月儿格外大,我们保养完车在车场上散步,他对我说:“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写信了,执行任务太紧张,这两天说什么也要把这封信写了。”
说罢他望了望天上,“家乡的月儿有这么大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光笑。他没有来得及兑现自己这一生对老师的最后一个承诺,就去了。
当时是50年代末,我们在西北某地执行平息叛乱的运输任务,我俩都是副驾驶员。那天,车队运载着一批从战场上抓到的叛匪,行驶在高原上。在翻越巴颜喀拉山时,我们遇到了一伙骑着高头大马的叛匪,这些恶人看到车上拉的是他们的伙伴,一下子就急红了眼,像亡命之徒一样向车队涌来,拚命鸣枪。我记得很清楚,涌上来的骑兵队形呈扇状,犹如雷鸣闪电一般急烈……
我们的车队加速了马力飞驰!
在公路绕着山势转去的一个胳膊肘紧弯处,一辆车因速度飞快而翻——正是我那位同志坐的车,四轱辘朝天,油箱里的油飞溅得满地都是。
非常奇怪,一车俘虏全部扣进了大厢内,一个也没死,唯独我的同学丧生。
说来该他死,谁让他跳车呢?
他坐在驾驶室里,见车要翻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慌手慌脚地便跳了出去……
我们击退了叛匪的追击。
连长看着躺在路边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哭凄凄地说:“他是我接来的兵,才18岁啊!我们离开他家那天,他爹再三叮咛我:孩子从没出过十里外的远门,把他交给你了,我放心,我放心……”
连长再也说不下去了。
全连同志垂手站在公路上,我的心里涌着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今天心里为什么这样冷,太阳藏起来了吗?
我是抱着满腔的憧憬上高原的。在中学课堂上我认识了青藏高原这块高地,我在脑海里把它描绘得像天国一样遥远而美丽。天国是什么,我不懂。青藏高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想青藏高原就是天国。现在,我来到“天国”才几个月,它就吞掉了我同学的生命,谁晓得它今后会怎么惩罚我呢?
我明白了,现实生活中的青藏高原与我想象的青藏高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哪里想到它会吃人呢?我的同学死了。
我不相信在死亡中保存的人的价值会更长久。
全连同志都在哭死去的战友,但是,听不到哭声。
山那边,冰块和冰块在撞击,那不是接吻,也不是歌声……
〔镜头2〕一位哲人说:数字是驳不倒的。
非常精彩。
不过,我还要说:数字是痛苦的。
当然,这不是普遍真理了。但是,在青藏线上确实如此。
1987年《解放军报》的内参反映了如下情况:
“长期在青藏线缺氧地区工作的部队干部战士身体素质明显下降。最近,该部对驻守在4200米以上的干部战士查体3334人次,血压异常的占57.8%,心脏阳性体症占59%,心电图异常占64%,高山多血质占72%,心脏异常占37%,五官有一项异常改变者占53%。”
我在兵站部的一份材料上还看到下面的两个情况,可以说是对军报内参反映的这组数字的诠释。
(一)1988年,格尔木大站对日月山至唐古拉山之间几个兵站的官兵进行单项查体,发现100%的人血色素增高,普遍高达25克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8克。据医生讲,达到28克时,人的血液就要凝固。
(二)1988年,拉萨大站对唐古拉山以南到拉萨河谷一线驻在5000米高处的23名官兵进行查体,发现有21人患高山性心脏病,有20人嘴唇发紫干裂,指甲严重凹陷。
这份材料记载着高原军人痛苦的遭遇。
高原上肆虐着拔地而起的风暴,风暴夹杂着6月的冰雹。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母亲为什么总在沉默?儿女为什么比母亲还沉默?
1990年8月21日,青藏兵站部政治部副主任郭东志在总后勤部礼堂对驻京部队作报告,他激动地流着眼泪念了这样一个数字:
“35年来,为了拓线、建线,青藏线的部队有6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在弥留之际,顾不得交代个人后事,都念念不忘青藏线部队建设,留下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深深眷恋。”
礼堂里两千多名听众,屏住呼吸听着。
不知道时是痛苦,知道了也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