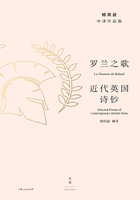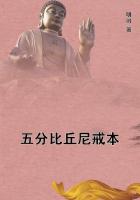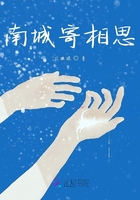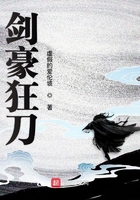但是,他们并未完全否定表现玄学情趣的文学。其批评和不满主要针对一部分作家作品,如许询、孙绰等人。而对另一些作家如阮籍、嵇康的作品态度则不一样。阮、嵇是较早在诗中有意识地表现玄理的作家,他们在一些文学理论家那里普遍受到推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体性》篇说:“嗣宗傲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都非常赞赏。钟嵘《诗品》把阮籍列为上品,以为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把嵇康列为中品,虽然批评他“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但仍然肯定他“托谕清远,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对玄学审美意识中的审美本体论的认识,以及这种本体论和文学理论本体论思想,和老庄道家哲学本体论的关系。
本书第一章,我们讨论玄学与文学联结的特质时,讨论了玄学审美意识。我们看到,玄学家在他们的审美意识中,已经包含了对审美本体问题的认识。王弼以为美在自然,在无声无味;以为无形之象,无声之音,无呈之味,是品物之宗主,事实上也是“苞通天地”的最高的美。既体现于具体物象,又不拘于某一象。
任其自然,就是“大象”、“大音”,以为自然之至美无味无声。
阮籍一方面说以乐移风易俗,这是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说乐之所始,在自然之道。阮籍实际是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无声无味,他以自然平和、精神超脱为至乐的境界,因此他反对“以悲为乐”。嵇康以为声无哀乐,否定声音之道与政通,否定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嵇康认为,乐有其不变的本体,这个不变的本体是自然之和。一切声音都本于自然。这自然之和,体现在音乐,就是音乐的和谐之美;体现于人心,就是“和心”;体现于社会,就在社会的返归自然。乐之本体,在社会风俗本身的和谐,在人心的和谐。社会自然无为无欲,人们的内心,人们的精神,整个社会的气氛,都归于自然和谐,自然淳朴的社会,这是天地无声之“大乐”。无声之乐就是大道,自然之道才是乐之本体。
玄学审美意识中包含的艺术本体论,其基础当然是玄学的哲学本体论。而玄学的本体论,不论是哲学的还是审美的,其基础又都在老庄。“无”和“自然”的概念都直接来自老庄。老子以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以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而道法自然,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冲气为和的状态,就是道的状态。庄子也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庄子·天地》)又说:“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庄子·庚桑楚》)谈到艺术,老子则有著名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
有学者据此提出道家有它的艺术本体论(如《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道家的艺术本体论剖析》)。说道家有它的艺术本体论,这是对的。玄学审美本体论应该是道家艺术本体论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玄学本体论对老庄也有选择,有改造。它们更强调崇本息末,以无全有,而郭象以适性为逍遥。
道家艺术本体论,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本体,可能与观念、精神有关,但未必就直接是指观念精神。老庄的“道”也好,玄学的“无”也好,自然也好,都不直接指观念、精神。老庄及玄学本来就不是把世界截然划分为物质一精神两个对立的方面,如我们现在流行的哲学划分一样。老庄及玄学所讲的万物,并不就指现代哲学含义上的物质,所讲的“道”、“无”、“自然”之类,也并不就是物质之外的东西。它只是在万物之中起作用,而又看不见,能感受得到,却无形无声的一种力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很神妙,因此称之为玄。它并不是宇宙万物生成之前所存在的先验的观念的东西。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只是说,在现有天地之前,万物就是自然的状态,就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并不意味着“道”或者“自然”可以超离万物而存在。“道”不离物,所谓“自然”,就是万物之自然。它不是观念性的东西。
老庄也好,玄学也好,都只是在实有的世界中看到虚的一面,在有限的世界中看到无限的一面,而这虚的东西,可能支配着万物,但这“虚”、“无”并不是万物之外的东西。它只是一种状态。就庄子来说,是把它作为万物无差别、无是非的状态。当你认为万物无差别、无是非,以为万物齐一、物论齐一的时候,你就进人了“道”的境界,“无”的境界。一旦你认为万物有差别,有是非的时候,就不再是这一境界。“道”在万物,但万物本身不是“道”,只有万物齐一的境界才是“道”。“道”在草芥瓦砾,在屎溺,但草芥瓦砾屎溺本身不是“道”,只有草芥瓦砾和金玉珠宝齐一,荣辱生死无差别的时候,才是“道”,才是“无”。而这样一种境界并不等同于与物质相对的观念。这样一种状态(“道”、“无”的状态),当然只有靠心、神才能体悟,而不能靠其他感官直接接触,但心灵所体悟的,并不是观念性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一种状态。在老庄及玄学这里,万物本身不是观念的外化,它只是要呈现为“道”、“无”、“自然”的状态,可以使人进入这种无的境界。
至于说到老庄及玄学的哲学本体论和审美本体论,“道”和“无”,和古代文论中文学本体论的关系,又呈现复杂的情形。哲学之光只是折射、渗透到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认识只是从哲学认识中受到启示,并不会直接原封不动地搬用现成的哲学概念。
它要从哲学形态变为文学艺术形态。古文论不讲无差别无是非,不讲万物齐一。它主要讲自然,它也讲无形无声,但不是相对于有形有声的万物而言,而是相对于具体可感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彩色、语言及其材料而言。这无形无声,主要指多层空灵飘忽的意蕴,指言外之意。古文论中对“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论述,有的带有本体论的性质,但又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本体论,很多时候,它是创作论、鉴赏论,表现为一种审美情趣。它受玄学本体论(包括它的审美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艺术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在文论中,它却主要反映为一种审美情趣,本书因此就把这部分内容放在审美情趣一章讨论。
三
古文论中的本体论,最有代表性的认识,是下面将要分析的刘勰的原道论。刘勰原道论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但也不是老庄玄学本体论的简单套用。它既吸收儒家的东西,也可能有佛家的东西,其中主要的,我以为当然是老庄玄学的东西。但老庄玄学中,它又不讲“无”、不讲无形无声,而是讲“自然”,以自然本然为文学的本体。老庄玄学本体论中的其他思想则没有进人刘勰的原道论。
古文论中带有本体论性质的,还有“诗以情为本”的思想。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它与玄学的关系是又一种情况。
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具体看看,文学本体论中玄学的影响。
古代文学本体论,最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刘勰《文心雕龙》
原道论。《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这是说《文心雕龙》的体制,以“道”为本,也是说《文心雕龙》所论文学问题以“道”为本。原道论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如纪昀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大量引《易传》,原道又转入征圣、宗经,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他所说的“圣”,是儒家圣人;“经”,是儒家经典,这都明白地说明,刘勰原道论有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刘勰原道论,可能也有佛家的某些影响。这里讨论的是,是玄学的影响。
玄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的问题上。刘勰所原之“道”,指自然之道,而这所谓“自然”,又指自然而然,指万物的自然本然。强调万物各有其性,因而各呈其采,这样一种对文的本体本质的认识,有着玄学的深刻影响。
《原道》篇可以看出这一点。《原道》篇的基本思想,是人仿效天地,而不论天文、地文、人文,都是“道”之文,而“道”是自然。天、地、人旁及万品,均因其自然本然而有其文。
他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文”是广义的文,是一切事物的文采。德是得道,文是“道”的体现,是万物自然本然的体现。万物皆有其自然,皆有其道,故皆有其文。万物皆有其文,故日“文之为德也大矣”。
天地皆有其文,有天地即有其自然本然,即有其文,故日“与天地并生”,“何哉”者即在此。“玄黄色杂,方圆体分”云云,即所谓“一阴一阳”,《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一阴一阳的变化本身就是“道”,但刘勰却说,这是“道之文”,就是说,阴阳变化本身还只是文,在它之上,还有一个统摄它、支配它的更高层次的“道”。刘勰强调的不是阴阳事物之间的互相感应,并没有说天文乃至人文,最终都是阴阳运动变化的产物,刘勰强调是的日月如何垂丽天之象,山川如何铺理地之形,它们各自因其本然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表现形式,他的意思,和下面说的“动植皆文”一样,日月山川各有其本然之性,因而各呈其文采,日月之自然本然与山川不同,因而垂丽天之象,反过来也一样,山川之自然本然与日月不同,因而铺理地之形。“道”即寓于日月山川的自然本然。所谓“道之文”,就是日月山川各因其自然本然之性所呈之不同文采。
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这就说得更清楚了。从天文说到人文,而人参效、模仿天地,所谓“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罗宗强先生的解释是对的,“惟人参之”的“参”,就是参拟、仿效。人参拟、仿效天地,而天地五行灵智秀异之气皆钟聚于人,人为天地间最灵异的中心所在,因而言立文明。刘勰的侧重点在讨论人禀受天地灵异之气和人文的关系,他的意思,是把人文看做人禀受天地灵异之气的自然体现。人参拟、仿效天地,禀受天地灵气,自然有其文。他是以“道”指自然,而自然指寓于事物的自然本然。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这是继续明确说明“道”即自然,不过刘勰的意思,并不是以自然与人工雕饰相对。刘勰在这里确是以为自然高于画工之妙,锦匠之奇,但画工之妙、锦匠之奇之所以不及自然之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既因其是人为,更因其“外饰”。而动植之文则出于自然,并非外饰。所谓外饰,就是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以外力强为饰之。对于自然事物来说,任何人为都是外饰,都违逆事物的自然本然,因而都须反对。反对人为,归根到底是反对外饰。刘勰的意思是,龙凤虎豹、云霞草木都有文采,而文采均不同。之所以各呈不同的文采,是各因其自然本然,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龙凤之藻绘呈瑞,虎豹之炳蔚凝姿,都是文丽采奇,刘勰之所以以为它高于画工之妙、锦匠之奇,就因为前者是“道之文”,是事物自然本然的文采,而后者不是。
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镗,故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
万物各有其形,因而万物各有其文采。和形立声发并生的,只能是它们的自然本然。任何一事物,当它产生形成之时,就有了与另一事物不同的自然本然的东西,而因其自然本然,文亦与之俱生,因而“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林籁结响既成,则有如竽瑟相应之调。泉石激韵既发,则有如钟磬相和之声。有其形而有其声文,而声文之不同,乃各因其自然本然之不同。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按照汉儒的解释,“太极”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郑玄注《乾凿度》“孑L子日‘易始于太极”’就说:“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所始也”。后来唐孔颖达为《易》“易有太极”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实取汉儒成说)。刘勰所谓“太极”如果是取汉儒之意,并且是从时间上追溯人文之元,那么,天地既未分,何以有人?又何以有人文?何况他明明说过,文“与天地并生”。或者,刘勰是说理先事后,与天地并生,是言已形之事,而肇自太极,是言尚未明著之理,是说未有天地,已早孕人文之理。但刘勰也可能仍是以此说明“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说明人文之元,乃参拟、仿效天地。他无意追溯宇宙产生构成如何从元气混一到天地始分云云,所以他推演《易·系辞》“易有太极”,却不说“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云云,而直截说:“幽赞神明,《易》象为先。”《易》象最早深刻阐明天地神妙之理。“《易》象为先”也就是人文之元,元也就是先。人文之元为《易》象,而《易》象肇自太极,之所以肇自太极,是因为它幽赞神明。神明即天地之神明,太极之神明,因此“太极”即天地。幽赞神明即参拟仿效天地神明之理。因参拟仿效天地之理,故有《易》象。王弼把太极直接解释作天地(见《晋书》卷六十八顾荣之言:“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未当”)。刘勰之“太极”,可能即取王弼之解释,因此下文又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言》托文王之言,故称《文言》。但刘勰取其另一义,以为《文言》之文即人文之言,以说明它和天地的关系。前面说过,人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既然如此,人文自亦为天地之心。前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此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是知太极即天地,肇自太极,天地之心,都有参拟、仿效天地之意。因参拟、仿效天地,故得为天地之心,为天地神灵秀异之气所钟聚,故始有人文,《易》象惟先。《晋书》卷六十八顾荣曾批评王弼说:“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这恰恰说出了王弼“太极”说的本意。刘勰取的可能正是此意。就是说,他认为天地乃自生。天地自生,则天地之文亦因其自然而生。仿效天地而生人文,就是一个因其自然本然的过程。刘勰是把人文之元最结到自然本然上来。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刘勰相信《河图》、 《洛书》之类传说,相信圣人法《河图》、《洛书》以成文。他把这归之为神理。谶纬神学是把《河图》、《洛书》看做神秘的神灵启示,刘勰所谓“神理”,可能多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刘勰主要似在强调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下文“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神理与道心相对,是神理即道心。而“道”是自然之道,如旁及万品、动植皆文一样,《河图》、《洛书》玉版金镂、丹文绿牒之类,也是自然而然,不过动植皆文视而可见,而《河图》、《洛书》更为神妙,是神秘的本然罢了。
在追述了自《三坟》到孔子的人文历史之后,刘勰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又赞日:“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取象《河》、《洛》,观天文以极变,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云云,是说圣人与天地相参,象天地,参物序,但天文乃道之文,而人文是道沿圣所垂之文,自《三坟》到孔子,都“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他是把人文、天文归结为“道”的表现,而“道”即寓于万物之自然本然。因其自然本然,因此历代有历代之文。他用自然本然之道,来解释天文旁及万品之文,也用它来解释人文的发展历史。本于自然之道,自然为万物之本然,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基本思想。
三
文本于自然之道,所谓“自然”,即每一事物之自然本然,这种本体论的认识,影响到《文心雕龙》对其他很多问题的看法,或者说,在《原道》篇之外的很多内容上体现出来。
比如,《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篇。“征圣”、“宗经”,是确立圣人经典不可移易的权威地位。圣人经典之所以权威,是因为它体现了自然之道,它是“道”的体现。既然“征圣”、“宗经”,其准则是不变的。它也提出了一些不变的准则,如宗经六义,如情信辞巧、衔华佩实等等。但事实上,刘勰讲“征圣”、“宗经”,也讲因宜适变。
《征圣》篇云:“或简文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邻《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央,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春秋》、《诗》、《书》、《易》,文体各不相同,故繁略隐显各不相同。这实际是说,文体不同,故文风亦当不同。文风要随任不同文体而变化。文本于自然,恰恰是讲变化的,万物各自因其自然本然因而呈其文采。刘勰说:圣人经典“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可以看做是文本于自然思想的具体体现。
《宗经》篇云:“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
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
主言志,诂训同《书》,搞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鹚’,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说圣人殊致,表里异体,事实也是讲变化,因文体不同而文风有变化,因为圣人殊致异体。因此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
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
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这是说,后代所有文体都可以从经典那里找到它们的渊源,但同时也是说,不同文体当宗法不同的经典,并不是任一种经典,都可为任一种文体所效法,而要根据不同文体自身的特点。一种文体,宗法什么经典,要因任这种文体的自然本然的特点。这和《征圣》篇讲的变通适会是一致的,和文本于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体性》篇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斡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傲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前说“莫非情性”,后说“岂非自然之恒资”,他是把情性看作人的自然本然的东西,而文章风格,就本于作家的自然情性,是作家情性的外在表现。“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表里必符”。正如从本体论来说,天地万物之文是天地万物之自然本然的外在表现一样。从原道论来说,龙凤则必然以藻绘呈瑞,虎豹必然以炳蔚凝姿,日月则必然垂丽天之象,山川则必然铺理地之形。从体性来说,则贾生俊发,必然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必然理侈而辞溢,等等。从原道论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从体性论来说,则“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体性论强调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把文本于自然的本体论的思想具体化了。它所体现的,正是文本于自然的思想,而所谓“自然”,正是自然本然,万物的自然本然,作家情性的自然本然。万物因其自然本然而各呈其文采,文章则因作家之自然的情性而风格各异。
《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是指人的情性的自然。“感物吟志”,就是吟咏人的自然本然的情志。诗本于情性,就是本于自然。
作为一种风格走向的客观态势,一种蕴藏着的力的流动,引而未发的发展潜力的动势,这种动势影响着的文章风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情,是体。《定势》篇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文章的体制体貌,是因情而立,而以情致为中心,包括体裁、文辞、结构、义脉等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格局体制,形成的体貌,就形成一种“势”。这种“势”使文章风格有一定的走向。他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东西。
他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因此,“模经为式者,自人典雅之懿;效《骚》
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之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他又把这称为“本采”,本采,就是本来本然的色彩。文章写作,风格趋势的确定,就要本于这本然的色彩,因其自然。比如,“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霰要;
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不是人为的脱离文章自然本然的.
体制而规定其风格趋势。这里体现的,仍是文章本于自然的思想,而所谓“自然”,就是事物的自然本然。就原道论来说,是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就定势论来说,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是循体而成势。原道论是自然之道,定势论是自然之势。
四
一种看法,以为文本于自然,所谓“自然”,指外界大自然无意识的自然变化,或称自然规律。另一种看法,把刘勰所谓“自然”解释为与人为造作相对的自然。这两种看法似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文心雕龙》。就《原道》篇来说,刘勰主张人仿效天地,但天地之所以值得仿效,是因为它是“道之文”,天地自然变化本身只是“道之文”,在它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而这“道”,就是万物之自然本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刘勰是认为自然高于画工之妙、锦匠之奇,但刘勰反对的实际上是画工锦匠的“外饰”,即违背事物之自然本然而以外力强为饰之。就整个《文心雕龙》而言,刘勰所谓“自然”,很多并不是论外在自然的变化规律。《明诗》篇论感物吟志,《诔碑》篇论蔡邕的碑文创作,《定势》篇论文势,《体性》篇论风格与才性的关系,都用自然之道的理论去说明,却都没有涉及外在自然的变化规律。
很多时候,刘勰所谓“自然”与人为造作也并不对立。一切人类文化包括文学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刘勰却认为它们都本原于自然之道。一部《文心雕龙》,一方面以文之本原为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连篇累牍地讨论声律、章句、对偶、比兴、夸张、用典、练字这些显系人为创造的写作技巧,可见他至少认为“自然”和这些写作技巧不矛盾。《体性》篇所论十二位作家的风格,基本上都不以去雕饰、淡退人工痕迹为特色,刘勰却说这些风格合于“自然之恒姿”。《定势》篇论文势,说只要“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就是“自然”,而这样的文中,当有不少雕削取巧、润色取美者。《定势》篇为说明自然之势而举例的归于艳逸之华的《离骚》,文体风格如典雅、清丽、明断、弘深、巧艳等等,都不是以去人工雕饰为特色。《诔碑》篇一面称蔡“察其为才,自然而至”,一面称他的文章善缀文采、能出巧义,这都有人工雕饰的因素在。《明诗》篇以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紧接着就论述自葛天氏至宋初历代诗歌。他的意思,显然是说历代诗歌均为感物吟志之作,均本原于自然。而事实上,历代诗歌并非普遍以尚自然去雕饰为特色。《征圣》篇、《宗经》篇也不好解释。圣人、经典都是明道的,这两篇反映的是刘勰对圣人经典所明之“道”具体内涵的认识,但是,这两篇没有一句话说到反对人工雕饰,虽然《宗经》篇有涉及天地的一句话,但就全篇而言,都不是论述天地的变化规律。
因此,刘勰所谓“自然”,仍应解释为自然本然。每一事物一旦形成,就有其自然本然的东西,因而有每一事物之“文”。
所谓“文”,就是这一事物自然本然的外在具体表现。这种自然本然,就是一切事物表现为“文”的本原,而这也就是“道”的精神。就文章来说,则具体体现在作者和作品两个方面。就作者来说,他自然本然的东西,就是他的情性。就作品来说,指它本然的写作情理。文章写作既要本于作者的自然情性,又要本于文章自身的写作情理,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心雕龙》,这正具体体现了文本原于自然之道的精神。
这样理解,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文心雕龙》讨论了很多问题,涉及到很多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如《体性》、《定势》篇中所论及的),虽然大多并不以去雕饰为特色,《文心雕龙》也讨论了诸多人为创造的写作技巧,但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作家情性和文章写作情理的本然之义。假如这位作家禀性傲诞,那么,文章浮侈溢美、夸饰其辞,就合于他的自然情性。假如这种文体本来就是效《骚》命篇,那么,归于艳逸之华就合于它的写作情理。假如从文章写作情理或作家情性出发,需要声律、对偶、用典、比兴、夸饰、章句等,那么,这些人为的写作技巧就合于自然。关于这一问题,《情采》篇有一段论述可作很好的说明。刘勰在《情采》篇中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这一观点,向来被认为刘勰是反对人为造作。其实,这样看至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为文而造情”是人为造作,“为情而造文”又何尝不是人为造作!不同的是,一个是“造情”,一个是“造文”。刘勰之所以反对“为文而造情”,乃因为它是“造情”,即违逆作者情性之本然;之所以又赞成“造文”即人为造作之文,乃因为它是“为情”,即顺任作者情性之本然耳。以自然本然释“自然”,自然和人为在这些地方就统一起来了。
刘勰何以一边讲“文本于自然”,一边又竭力推崇儒家名教,也就好理解了。儒家仁孝忠恕、政治教化一类东西,当然是人为造作的产物,从这点看,它不合于与人为相对的自然。但是,这些东西又可以看做事物自然本然的禀性,从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合于自然的。以事物的自然本然解释“自然”,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至此,我们可以把刘勰关于“文本于自然”的思想特点归纳为两点:
一、它把名教和自然、有为和无为、人工雕饰和天然之美统一起来了。这些东西本来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但从刘勰的原道论看,这些矛盾的东西都是事物的自然本然,都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文心雕龙》之所以既强调自然,又推崇儒道,既提倡天然之美,又用那么多篇幅讨论有着明显人工雕饰痕迹的写作技巧问题,就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事物自然本然的表现,都合于自然。
二、所谓自然之“道”,就其认为事物都顺其自然本然这一点来说,是统一的,是主张万物归本于一。但是,它的侧重点却是强调万物各有其性,因而各呈其采。按刘勰的观点,“道”即在万事万物各自本然的禀性之中。这实际上又否认“道”是一个固有不变的统一实体。他之所以在《定势》、《体性》等篇中提出风格多样化的理论,之所以强调每一文体须遵循每一文体的写作规范,而不是遵从某一统一的法则,都与他的原道论的这种特点有关。
这样一种原道论,就玄学与它的关系而言,可能会有王弼哲学的某些影响,但主要的,似是郭象哲学的影响。前面我们讨论过,郭象和王弼虽然都是玄学,都崇尚自然,但它们的思想特点并不一样。首先, “自然”是什么?王弼认为, “自然”就是“无”,是世界万物共有统一的本体。王弼注《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郭象则强调,所谓“自然”,不过是万物任其自性的自然,世界万物都各有其自性、真性,它们不过是各任其性而“自生”、“独化”,并不存在共有的统一的本体。其次,有为、名教与自然是什么关系,两家认识也不一样。王弼虽然并未否定有为、名教,但认为有为、名教和自然毕竟是两回事,自然是本,名教、有为是末,只有崇本息末,才能“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否则,“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王弼注《老子》三十八章)。在他那里,还是有名教与自然、有为与无为之分。但是郭象认为,只要率性而动,就没有什么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之分。有为亦无为,他认为:
“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则古今上下无为,谁有为也”(郭象注《庄子·天道》篇)。牛马穿鼻本是人为,“荀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亦本在乎天也”(郭象注《庄子·秋水》篇)。只要任其自然,有为亦是自然。同样的道理,名教亦即自然,郭象注《庄子·齐物论》说:“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
刘勰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其实和王弼有很大区别。刘勰认为仁孝忠恕、儒家典章文化一类东西,本来就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征圣、宗经就是原道。王弼则认为名教有虚伪矫饰的一面,只有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名教才可以肯定。王弼对名教有批评,刘勰基本上没有批评。刘勰所谓“道”产生“文”,和王弼所说的无中生有也有很大区别。王弼以为无中生有,是以为宇宙万物皆归于一,共同的本原只有一个,就是“无”。刘勰所谓“自然之道”并不认为万物存在的根据是一个共有的不变的实体,他只是认为事物存在的根据,“文”产生的根据,在于每一事物的自然本然之中。刘勰所谓“道”、“自然”,和王弼的“无”在内涵规定、思想走向上有很大差异。
刘勰和郭象思想有不少区别,刘勰没有郭象哲学那么多消极的东西,没有郭象那种冥然自合的蒙昧主义,也没有郭象浓厚的宿命论,刘勰也没有政治上的愚民说教。但是,刘勰以自然论道,在本体论问题上,更为接近郭象的思路。他们都把自然视为事物的自然本然(郭象称为“自性”、“真性”,刘勰称之为“自然之恒资”、“本采”等等),都认为万物各有其自然本然的东西,“道”即存在于事物各自本然的禀性之中,不承认有一个高临于万物之上的固有不变的统一的本体,都把名教、有为看做自然的本有之义。刘勰的有些用语也与郭象《庄子注》相似。“性分”、“适性”之类说法在郭象《庄子注》中触目皆是,刘勰也常用。
比如,《文心雕龙·明诗》篇论诗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便同时指出,诗歌写作须“随性适分”,因而“鲜能圆通”。郭象强调任万物之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也明确提出,要“因性以练才”。《庄子》说“随其成心而师之”,郭象《庄子注》接过这个说法,也以“成心”称物之自性。《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刘勰在论述因作者情性不同而风格各异时,就说,这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顺便说一下刘勰关于“文本于自然”的原道论的意义。我以为有三:一、它为作家表现个人情性,为文章风格多样化找到了哲学本体论的根据。二、为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对文学自身特点、表现技巧、手法、声律、对偶、辞采等,找到了哲学本体论的根据。三、为他之前形成的各种并不相容,甚至对立(如重功利和重抒情、重实用和重审美)的文学思想找到了能使它们相容的统一的哲学本体论的根据,从而使《文心雕龙》能完成在文学理论上将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汇流成海的严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