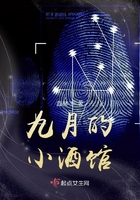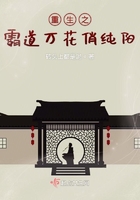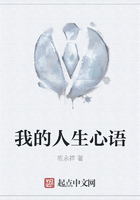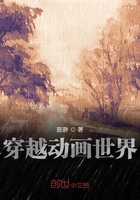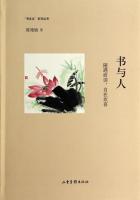列传第四。
<乙支文德><居柒夫><居道><异斯夫><金仁问><金阳><黑齿常之><张保囗>(+<郑年>)<斯多含>。
四四卷列传四乙支文德零一
<乙支文德>,未详其世系。资沈囗有智数,兼解属文。<隋><开皇{大业}>中,<炀帝>下诏征<高句丽>。于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与九军至<鸭囗水>。<文德>受王命,诣其营诈降,实欲观其虚实。<述>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来,则执之,<仲文>等,将留之,尙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遂听<文德>归,深悔之,遣人囗<文德>曰:“更欲有议{言},可复来。”<文德>不顾,遂济<鸭囗>而归。<述>与<仲文>,旣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谓{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兵,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述>等不得已而从之,度<鸭囗水>追之。<文德>见<隋>军士有饥色,欲疲之,每战辄北{走},<述>等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旣恃骤胜,又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
四四卷列传四乙支文德零二
<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旣高,知足愿云止。”
<仲文>答书谕之。<文德>又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王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难以猝拔,遂因其诈而还,为方阵而行。<文德>出军,四面囗击之,<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至<萨水>,军半济,<文德>进军,击其后军,杀右屯卫将军<辛世雄>。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九军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囗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凡}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
四四卷列传四乙支文德零三
论曰:<炀帝><辽东>之役,出师之盛,前古未之有也,<高句丽>一偏方小国,而能拒之,不唯自保而已,灭其军几尽者,<文德>一人之力也。『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信哉。
四四卷列传四居柒夫零一
<居柒夫>[或云<荒宗>。]姓<金>氏,<奈勿王>五世孙,祖<仍宿>角干,父<勿力>伊囗,<居柒夫>少囗弛有远志。祝发为僧,游观四方,便欲囗<高句丽>,入其境,闻法师<惠亮>开堂说经,遂诣听讲经。一日,<惠亮>问曰:“沙{汝}弥从何来?”对曰:“某<新罗>人也。”其夕,法师招来相见,握手密言曰:“吾阅人多矣,见汝容貌,定非常流,其殆有异心乎?”答曰:“某生于偏方,未闻道理,闻师之德誉,来伏{趋}下风,
愿师不拒,以卒发蒙。”师曰:“老僧不敏,亦能识子,此国虽小,不可谓无知人者,恐子见执,故密告之,宜疾其归。”<居柒夫>欲还,师又语曰:“相汝囗鹰视,将来必为将师{将帅}。若以兵行,无贻我害。”<居柒夫>曰:“若如师言,所不与师同{相}好者,有如囗日。”遂还国返本从仕,职至大阿囗。
四四卷列传四居柒夫零二
<眞兴大王>六年乙丑,承朝旨,集诸文士,修撰国史,加官波珍囗。十二年辛未,王命<居柒夫>及<仇珍>大角囗<比台>角囗<耽知>囗<非西>囗<奴夫>波珍囗<西力夫>波珍囗<比次夫>大阿囗<未珍夫>阿囗等八将军,与<百济>侵<高句丽>。<百济>人先攻破<平壤>,<居柒夫>等,乘胜取<竹岭>以外,<高岘>以内十郡。至是,<惠亮>法师,领其徒,出路上,<居柒夫>下马,以军礼揖拜,进曰:“昔,游学之日,蒙法师之恩,得保性命,今,邂逅相遇,不知何以为报。”对曰:“今,我国政乱,灭亡无日,愿致之贵域。”于是,<居柒夫>同载以归,见之于王,王以为僧统,始置百座讲会及八关之法。<眞智王>元年丙申,<居柒夫>为上大等,以军国事务自任,至老终于家,享年七十八。
四四卷列传四居道零一
<居道>,失其族姓,不知何所人也,仕<脱解>尼师今,为干。时,<于尸山国><居柒山国>,介居邻境,颇为国患。<居道>为边官,潜怀幷呑之志,每年一度,集群马于<张吐>之野,使兵士骑之,驰走以为戱乐,时人称为马叔{技}。两国人,习见之,以为<新罗>常事,不以为怪。于是,起兵马,击其不意,以灭二国。
四四卷列传四异斯夫零一
<异斯夫>[或云<苔宗>。]姓<金>氏,<奈勿王>四世孙。<智度路王>时,为沿边官,袭<居道>权谋,以马戱,误<加耶[或云<加罗>。]国>取之。至十三年壬辰,为<阿瑟罗州{何瑟罗州}>军主,谋幷<于山国>。谓其国人愚悍,难以威降,可以计服,乃多造木偶师子{狮子},分载战舡,抵其国海岸,诈告曰:“汝若不服,则{卽}放此猛兽,踏杀之。”其人恐惧则{乃}降。<眞兴王>在位十一年,<太宝>元年,<百济>拔<高句丽><道萨城>,<高句丽>陷<百济><金岘城>。主{王}乘两国兵疲,命<异斯夫>,出兵击之,取二城增筑,留申{甲}士(+一千)戍之。时,<高句丽>遣兵来攻<金岘城>,不克而还。<异斯夫>追击之大胜。
四四卷列传四金仁问零一
<金仁问>,字<仁寿>,<太宗大王>第二子也。幼而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庄><老>浮屠之说。又善隶书射御乡乐,行艺纯熟,识量宏弘,时人推许。<永徽>二年,<仁问>年二十三岁,受主{王}命,囗{入}大<唐>宿卫,<高宗>谓涉海来朝,忠诚可尙,特授左领军卫将军。四年,诏许归国觐省,<太宗大王>授以<押督州>援管{摠管}。于是,筑<獐山城>,以设险,<太宗>录其功,授食邑三百户。<新罗>屡为<百济>所侵,愿得<唐>兵为援助,以雪着{羞}耻,拟谕宿卫<仁问>乞师。会,<高宗>,以<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摠管,率师讨<百济>。帝征<仁问>,问道路险易,去就便宜。<仁问>应对尤详,帝悦制授<神丘>道副大摠管,囗赴军中。遂与<定方>济海,到<德物岛>。主{王}命太子,与将军<庾信><眞珠><天存>等,以巨舰一百囗,载兵迎延之。至<熊津>口,贼濒江屯兵,战破之,乘胜入其都城灭之。<定方>囗王<义慈>及太子<孝>王子<泰>等,回<唐>。
四四卷列传四金仁问零二
大王嘉尙<仁问>功业,授波珍囗,又加角千{角干}。寻,入<唐>宿卫如前。<龙朔>元年,<高宗>召谓曰:“朕旣灭<百济>,除尔国患,今,<高句丽>负固,与<秽貊>同恶,违事大之礼,弃善邻之义,朕欲遣兵致讨,尔归告国王,出师同伐,以歼垂亡之虏。”<仁问>便归国,以致帝命,国王使<仁问>与<庾信>等,练兵以待。皇帝命邢国公<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摠管,以六军,长驱万里,囗<丽>人于<须江{浿江}>,击破之,遂围<平壤>,<丽>人固守,故不能克。士马多死伤,粮道不继。<仁问>与留鎭<刘仁愿>,率兵兼输米四千石租二万余斛,赴之,<唐>人得食,以大雪,解围还。
四四卷列传四金仁问零三
<罗>人将归,<高句丽>谋要击于半涂,<仁问>与<庾信>,诡谋夜遁。<丽>人翌日觉而追之,<仁问>等,回击大败之,斩首一万余级,获人五千余口而归。<仁问>又入<唐>,以<干封>元年,扈驾登封<泰山>,加授右骁卫大将军,食邑四百户。<摠章>元年戊辰,<高宗皇帝>遣英国公<李绩>,帅师伐<高句丽>,又遣<仁问>征兵于我。<文武大王>与<仁问>,出兵二十万,行至<北汉山城>,王住此,先遣<仁问>等,领兵会<唐>兵,击<平壤>月余,执王<臧>,<仁问>使主{王}囗于英公前,数其罪,王再拜,英公礼答之,卽以王及<男产><男律{男建}><男生>等还。<文武大王>,以<仁问>英略勇功,特异常伦,赐故大琢角干<朴纽>食邑五百户。<高宗>亦闻<仁问>屡有战功,制曰:“爪牙良将,文武英材,制爵疏封,尤宜嘉命。”仍加爵秩,食邑二千户。自后,侍卫宫禁,多历年所。
四四卷列传四金仁问零四
<上元>元年,<文武王>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唐>皇帝大怒,以<刘仁轨>为<囗林>道大摠管,发兵来讨,诏削王官爵。时,<仁问>为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在京师,立以为王,令归国,以代其兄,仍策为<囗林州>大都督开府仪同三司,<仁问>恳辞不得命,遂上道。会,王遣使,入贡且谢罪,皇帝赦之,复王官爵,<仁问>中路而还,亦复前衔。<调露>元年,转鎭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大将军,<载初>元年,授辅国大将军上柱国<临海郡>开国公左羽林军将军。<延载>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寝疾薨于帝都,享年六十六。讣闻,上震悼,赠囗加等,命朝散大夫行司礼寺大医署令<陆元景>判官朝散郞直司礼寺某等,押送灵柩{枢}。<孝昭大王{孝照大王}>追赠太大角干,命有司,以<延载>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囗于京<西原>。<仁问>七入大<唐>,在朝宿卫,计月日,凡二十二年。时,亦有<良图>海囗,六入<唐>,死千{于}<西京>,失其行事始末。
四四卷列传四金阳零一
<金阳>字<魏昕>,<太宗大王>九世孙也。曾祖<周元>伊囗,祖<宗基>苏判,考<贞茹>波珍囗,皆以世家为将相。<阳>生而英杰。<大和{太和}>二年,<兴德王>三年,为<固城郡>大武{太守},寻拜<中原>大尹,俄转<武州>都督,所临有政誉。<开成>元年丙辰,<兴德王>薨,无嫡嗣,王之堂弟<均贞>,堂弟之子<悌隆>,争嗣位。<阳>与<均贞>之子阿囗<佑征><均贞>妹壻<礼征>,奉<均贞>为王,入<积板宫>,以族兵宿卫。<悌隆>之党<金明><利弘>等来围,<阳>陈兵宫门,以拒之曰:“新君在此,尔等何敢凶逆如此。”遂引弓射杀十数人。<悌隆>下<裴萱伯>,射<阳>中股。<均贞>曰:“彼众我寡,势不可囗,公其佯退,以为后图。”
<阳>,于是,突围而出,至<韩囗[一作<潢祇>。]市>,<均眞{均贞}>没于乱兵,<阳>号泣旻天,誓心白日,潜藏山野,以俟时来。
四四卷列传四金阳零二
至<开成>二年八月,前侍中<佑征>,收残兵,入<淸海鎭>,结大使<弓福>,谋报不同天之雠。<阳>闻之,募集谋士兵卒,以三年二月,入海,见<枯征{佑征}>,与谋举事。三月,以劲卒五千人,袭<武州>,至城下,州人悉降,进次<南原>,囗<新罗>兵,与战克之。<佑征>以士卒久劳,且归<海鎭>,养兵囗马。冬,彗囗见西方,芒角指东,众贺曰:“此除旧布新,报寃雪耻之祥也。”<阳>号为乎东将军{平东将军},十二月再出,<金亮询>以<鹉洲>军来,<佑征>又遣骁勇<阎长><张弁><郑年><骆金><张律荣{张建荣}><李顺行>六将统兵,军容甚盛,鼓行至<武州><铁冶县>北州{川}。<新罗>大监<金敏周>,以兵逆之,将军<骆金><李顺行>,以马兵三千,突入彼军,杀伤殆尽。
四四卷列传四金阳零三
四年正月十九日,军至<太丘{大丘}>,王以兵迎拒,逆击之,王军败北,生擒斩获,莫之能计。时,王顚沛逃人{入}离宫,兵士寻害之。<阳>于是命左右将军领骑土{士},徇曰:“本为报雠,今,渠魁就戮,衣冠士女百姓,宜各安居,勿妄动。”遂牧{收}复王城,人民案堵。<阳>召<萱伯>曰:“犬各吠非其主,尔以其主射我,义士也,我勿校,尔安无恐。”众闻之曰:“<萱伯>如此,其它何忧。”无不感悦。四月淸宫,奉迎侍中<佑征>卽位,是为<神武王>。至七月二十三日,大王薨,太子嗣位,是为<文圣王>。迫{追}录功,授苏判兼仓部令,转侍中兼兵部令,<唐>聘问,兼授公检校卫尉卿。
四四卷列传四金阳零四
<大中>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薨于私第,享年五十。讣闻,大王哀恸,追赠舒发翰,其赠赙殓葬,一依<金庾信>旧例。以其年十二月八日,陪葬于<太宗大王>之陵。从父兄<昕>,字<泰>,父<璋如>,仕至侍中波珍囗。<昕>幼而聪悟,好学问。<长庆>二年,<宪德王>将遣人入<唐>,难其人,或荐<昕><太宗>之裔,精神朗秀,器宇深沈,可以当选。遂令入朝宿卫。岁余请还,皇帝诏授金紫光禄大夫试大常卿{太常卿}。及归,国王以不辱命,{擢}授<南原>大守{太守},累迁至<康州>大都督,寻加伊囗兼相国。
四四卷列传四金阳零五
<开成>已未{己未}闰正月,为大将军,领军十万,御<淸海>兵于<大丘>,败绩。自以败军,又不能死绥,不复仕宦。入<小白山>,葛衣蔬食,与浮图游。至<大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感疾终于山齐{斋},享年四十七岁,以其年九月十日,葬于<奈灵郡>之南原。无嗣子,夫人主丧事,后为比丘尼。
四四卷列传四黑齿常之零一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毅有谋略,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犹<唐>刺史云。<苏定方>平<百济>,<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纵兵大掠。<常之>惧,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遯去,啸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归者三万。<定方>勒兵攻之,不克。遂复二百余城。<龙朔>中,<高宗>遣使招谕,乃诣<刘仁轨>降,入<唐>为左领军员外将军<囗州{洋州}>刺史。累从征伐积功,授爵赏殊等。久之,为<燕然道>大摠管,与<李多祚>等,击<突厥>破之。左监门卫中郞将<宝璧>,欲穷追邀功,诏与<常之>共讨,<宝璧>独进,为虏所覆,举军没。
<宝璧>下吏诛,<常之>坐无功。会,<周兴>等诬其与鹰扬将军<赵怀节>叛,捕系诏狱,投囗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马为士所囗,或请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马,鞭官兵乎?”前后赏赐分麾下,无留囗。及死,人皆哀其枉。
四四卷列传四张保囗零一
<张保囗>[『罗纪』作<弓福>。]<郑年>[<年>或作<连>。],皆<新罗>人,但不知乡邑父祖。皆善鬪战,<年>复能没海底,行五十里不囗,角其勇壮,<保囗>差不及也,<年>以兄呼<保囗>。<保囗>以齿,<年>以艺,常龃龉不相下。二人如<唐>,为武宁军小将,骑而用枪,无能敌者。后,<保囗>还国,谒大王曰:“遍<中国>,以吾人为奴婢,愿得鎭<淸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淸海>,<新罗>海路之要,今谓之<莞岛>。大王与<保囗>万人,此后,海上无囗乡人者。<保囗>旣贵,<年>去职饥寒,在<泗>之<涟氷县{涟水县}>。一日,言于戍将<冯元规>曰:“我欲东归,乞食于<张保囗>。”<元规>曰:“若与<保囗>所负如何,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耶。”遂去谒<保囗>,飮之极欢。飮未卒,闻王弑国乱无主,<保囗>分兵五千人与<年>,持<年>手泣曰:“非子不能平祸难。”<年>入国,诛叛者立王,王召<保囗>为相,以<年>代守<淸海>。[此与<新罗>传记颇异,以<杜牧>立传,故两存之。]
四四卷列传四张保囗零二
论曰:<杜牧>言:“<天宝><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虽同盘飮食,常囗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临淮>,分<汾阳>半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囗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巨盗,实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后,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积愤,知其心,难也。忿必见短,知其材,益难也。此<保囗>与<汾阳>之贤等耳。<年>投<保囗>,必曰:‘彼贵我贱,我降下之,不宜以旧忿杀我。’<保囗>果不杀,人之常情也;<临淮>请死于<汾阳>,亦人之常情也。<保囗>任<年>事,出于己。<年>且饥寒,易为感动。<汾阳><临淮>平生抗立,<临淮>之命,出于天子,囗于<保囗>,<汾阳>为优,此乃圣贤迟疑成败之际也。彼无他也,仁义之心,与杂情囗植,杂情胜则仁义灭,仁义胜则杂情消。彼二人,仁义之心旣胜,复资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称<周><召>为百代之师,<周公>拥孺子,而<召公>疑之。
以<周公>之圣<召公>之贤,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义之心,不资以明,虽<召公>尙尔,况其下哉。语曰:‘国有一人,其国不亡。’夫亡国,非无人也,丁其亡时,贤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宋祈{宋祁}>曰:“嗟乎,不以怨毒相甚{囗},而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汾阳>,<保囗>,孰谓<夷>无人哉。”
四四卷列传四斯多含零一
<斯多含>,系出眞骨,<奈密王>七世孙也,父<仇梨知>级囗。本高门华胄,风标淸秀,志气方正,时人请奉为花郞,不得已为之。其徒无虑一千人,尽得其欢心。<眞兴王>命伊囗<异斯夫>,袭<加罗[一作<加耶>。]国>。时,<斯多含>年十五六,请从军,王以幼少不许,其请勤而志囗{确},遂命为贵幢裨将,其徒从之者亦众。及抵其国界,请于元帅,领麾下兵,先入<囗檀梁>[<囗檀梁>,城门名。<加罗>语谓门为梁云。]。其国人,不意兵猝至,惊动不能御,大兵乘之,遂灭其国。囗师还,****功,赐<加罗>人口三百,受已皆放,无一留者。又赐田,固辞,王强之,请赐<阏川>不毛之地而已。<含>始与<武官郞>,约为死友。及<武官>病卒,哭之恸甚,七日亦卒,时年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