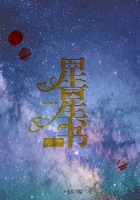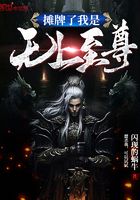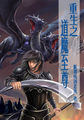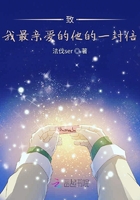魏若华
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议论:“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对于职业也罢,婚姻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名人名言,于是产生了“围城效应”!
但对明代官场这“效应”就不灵了,你想,他费了老大劲才“冲”进官场,尝到了当官的甜头,享受了既得利益,已经是美哉优哉了;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停滞不前,而是利用“剥皮”的手段,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当然是官越大越好,钱越多越好了;他又何必弃官不做,“逃”出官场呢?即使是官场失意,油水不大,他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退下来去当平民,“退”就意味着“丢了面子”;至于官做砸了,赃事犯了,或“诏狱严刑”,或“命丧黄泉”,他也会“生而无诲,死而无憾”的,也许还会来上两句:“再过二十年,老子拼命也要当个大官!”
据《官僚与官僚制》一书列举的研究资料显示:
——数千年来,古代就是“官吏与农民”构成的。官、民两级,以官为主,官贵民贱,民只是官吏的奴仆、权力的客体。
——官位是衡量士族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价值有无的唯一标尺,而民众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仅有的义务就是兵役、徭役、赋税。
——士族为达官欲、权欲、钱欲、****,往往像瘟疫感染一样,很快便会蚀透整个身心,除少数“海瑞”幸免其害,绝大多数在劫难逃。
——“官无常贵”这一规律导致的兴衰起落,使得做官为吏者们私欲膨胀,总是得其一,思其二,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直至死而后已。
——踏上仕途的人,大都官性旺盛而人性泯灭,一旦退出(多系犯案清除),官性才会逐步收敛,人性才会日益复苏。
——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于寻常的贪得欲,为了权与钱,可以父子相残、兄弟相戮、夫妻相离、亲朋相分,什么人间悲剧都会发生,古代的政治绝不仅仅发生在古代。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奇就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鲁迅先生在《致郑振铎》信中也曾谈道:“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
作为共产党人,老祖宗马克思有句名言:“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话又说回来,自己毕竟是一介平民,又何必“杞人忧天”?嘴说不过心啊!我依旧在苦苦地沉思与反思。
我想到了官吏的起源:
在我国的典籍中,不乏关于“官”的古老的传说,“三皇五帝”大概是最早最大的官了,这在《尚书·尧典》《左传》《史记·五帝本纪》中皆可得到印证。但还可以往前追溯,就是说在尧、舜、禹之前(不知是多少万年),人们往往以“云”、“火”、“水”、“龙”、“鸟”等自然现象或某种生物作为官的名号,以确保部落首领的权威,处理公共事务,维护氏族团结,这便是令人难以理喻的“图腾崇拜”。
我这样讲并非胡编乱造,不信可翻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2页、154—160页,以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尽管恩格斯与卢梭都是洋人,但就“官”之起源而言,中外世界大抵同而不悖。
那个时代,是一个十分单纯、质朴、美妙的时代,至少“没有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就是说,官只是协调生产关系的“人中之人”,并非指挥生产的“人上之人”
扯远了,怎么拉到原始共产主义上去了?还是就题来谈《明史中的“剥皮史”》吧!
明初,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他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可以“总百官”、“治万事”、“佐天子”。然而,天子毕竟是天子,天子就是天之子;“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乃皇上,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
皇权至上,相权几何?
朱元璋对相权从登基那天便心怀忌讳。他再三告诫臣僚,要效忠,“勿欺、勿蔽”,但官僚们为了争权夺利,竟搞什么淮西和浙东两大集团,互相攻击,各不相让。胡惟庸竟露骨地说:“杨宾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后杨宾被杀,左宰相果然轮到了胡惟庸。但这胡宰相却偏不识相,他倚仗韩国公做靠山,“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竟置皇权于不顾。朱元璋是何等样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以“擅权植党”罪诛杀了他。接着“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将其职分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历经千余年的宰相制废除了。接着又捕杀了居功自傲、横行不法的大将军蓝玉,被牵连者有一公、二伯、十三侯,并公布了审讯后所辑的《逆臣录》。
这两案,前后绵延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史称“胡蓝之狱”。由此,明代之“元勋宿将”(最大的官),几乎消失殆尽。
不难看出,再大的官也是皇帝封赐的,不管你资格多老、能耐多大,一旦超越皇权,或抵制、或分割、或诤谏,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伴君如伴虎”正是这一经验的总结!
然而,再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总理一切,朱元璋就曾叹息:“朕日总万机,岂能一一周遍?”于是在罢相两年后设大学士,“使侍左右,以备顾问”。到他儿子明成祖朱棣手上,干脆来了个折中办法,既不逾越“不置宰相”的禁令,也不沿用“以备顾问”的旧法,而称之为“内阁”。于是乎,“内阁辅政”便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
“政事因人而异,官职由人而设。”从宰相到顾问,从顾问而后内阁,机构越来越庞大,“官多缺少”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
究其因大约有三个:初期的“多途并举、三途并用”(除进士、举贡外,另推举“杂流进仕”,即不拘资历而破格录用);中期的“捐纳与荫生”(除“正途”考试外,另开“异途”二种,即捐班之官和世袭之官朝廷承认);末期的“开邸卖官晋爵”(除吏部任命外,另由位高权重者“职外加官”、“一官多人”,皇帝默许而不过问)。
上述流弊沿至明末,则更甚、更滥、更加不可收拾,已衍化到借钱买官、集资捐官,以致“有资即可官,才品俱无论”的地步。有人在京都长安门上贴首无题歌谣: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另有一首民谣,概括了捐资贿官者的群体形象,他们竟是一批不懂诗书、专刮民膏的“肉头千岁”:
唐诗无全诗,宋词有微词。权术窃王者,皆是瓷中次。
这里的“王者”,当也不仅专指“王公贵族”。因之,清末大学者顾炎武曾愤言:“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代官场之舞弊,不仅我们今天不理解,即使当时的皇帝也只能默而许之,从未细察之、深而究之,请看有关史料:
太监李广以左道见宠,及死,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书,搜其家,得纳贿薄籍一帙。中云: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通计数百万石。上询左右:“广所食几何,乃受许多米?”对曰:“黄米即金,白米即银。”(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
在那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年代,皇帝身边一个小太监收受之黄金白银竟数百万计,面对国库空虚、军饷无着、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不知皇帝本人又作何感想?
后人就此作了若干解释,皇帝所搜的并非“纳贿簿”,而是“奇方秘书”,至于黄米、白米之匿称,皇帝不明白也不足为怪。因皇帝并不直接参与卖官事宜,只是“私令左右”去操办。即皇帝将大头收入后宫大内,“聚财以为私有”;左右将小头归为己有,“以肥私室”;零头缴国库,当然所剩无几。于是,“卖官市场”上便出现了转手倒卖的“二道贩子”,也就是“左右的左右”了。就朝廷而言,卖官也是一项国库收入:国库空虚,可靠此渡过难关;国库盈实,可借此增强国力。卖官当然是一本万利,既能给皇帝带来财源,又能为皇帝缺钱分忧,皇帝何乐而不为之?至于老百姓呢,当官的多了,头上的虱子跟着多了,太多了也就不痒了!
明思宗崇祯倒真不是这样的皇帝。他曾多次以“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之类的话训告满朝文武,务必自律戒贪。但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枯竭的局面,也实在是无法应对、无力挽救的。
在夏维中的《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有这样几段文字(大意):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曾直言:
“皇上啊,文官也知不应爱钱,但时下局面,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文官也是不得已才爱钱!道理很简单,多数官就是以钱而晋,就任后自然得把本钱‘捞’过来。”
接着,韩一良讲了些官场内幕:
“据臣所知,谋一督抚,最少得银子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两三千两不可。至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丞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打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以自身为例道出了官场的现状:
“臣乃是从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时下,每提‘蠹民搜刮’,则全归属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何以能廉?他们的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又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两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容他一口气奏完,沉思良久,不知该作何解答。
但他知道,韩一良所述乃是真情实况矣。国家危难,这样讲真话的人堪称难能可贵啊!不久,便下一旨,破格提拔韩一良为右佥都御史了。
到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崇祯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自然想到了韩一良的进言,再次厉言重申: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无非是盘剥小民。这怎能选到好官?选拔之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期待的“吏治清明”至死也未曾实现!
反之,奢靡之风、裙带之风、帮派之风、舞弊之风、请托之风、贪墨之风,禁而不止,愈演愈烈;政以贿行之弊、冗官赘员之弊、任人唯亲之弊、恩荫得官之弊、以资晋官之弊、捐班买官之弊,积重难返,日盛一日。
日理万机的崇祯,至到煤山上吊之时,受朝廷俸禄的两三千文武官员又在哪里呢?
他依稀记得,曾传旨告曰:“百官俱赴东宫候旨。”而今,除身边的老太监王承恩,竟无一官,亦无一员,难道都殉职了,死光了?
他终于明白了“爱吾百姓”才是“保吾江山”的道理,然而晚了,完了……
但他还是在衣袖上写下了“杀尽百官,勿杀百姓”八个大字的遗言。
——这绝命遗言留给谁呢?
——打进北京的李自成!
1999年5月22日再校
(选自《明史笔记》,获宁夏第六届文艺评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