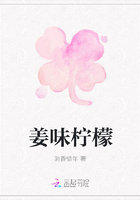理论批评模式是指运用某一理论观照文学文本,在分析文学文本的同时,进一步说明理论本身。其思维的走向是理论——文学文本——理论。其价值在于凸显批评者的理论意识、眼光和水平,同时可对文本意义做出与所用理论相关的新颖而独到的阐释。这种批评模式在小说研究中始于侠人的《小说丛话》,成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此后不少研究者也有丰富的表现,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一个文学研究的方法流派: 理论批评派。
一、 侠人《小说丛话》
人们通常认为,最早对《红楼梦》进行理论解读的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或认为用评论方法研究《红楼梦》者,王国维是第一人。究竟王国维是不是第一人,即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前,是否有人用西方理论解读过《红楼梦》?在对这一问题考察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 什么是理论评论?理论评论有哪些表现形态?
评论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广义为: 泛指一切评点论说文字,诸如古代的随笔、尺牍、杂记、序跋、评点等,也包括用某一理论分析、评论作品的评论文字。而其狭义则指后者,又称理论评论。前者带有古代的灵性,后者具有近代的科学性。本文所言理论评论指后者而非前者。
理论评论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 明确的理论、论证过程、结论。明确的理论有两种形态: 或对其使用的理论做详尽的说明;或舍去对理论阐释的环节,只将其带入论证的过程,且表现于结论内,读者一看就明白你所使用的是什么理论。《红楼梦》研究中最早出现的前一种形态的评论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早出现的后一种形态的评论是侠人于1903—1904年发表于《新小说》上的《小说丛话》。由于《小说丛话》发表的时间在《红楼梦评论》之前,所以可以说,用理论评论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是侠人而非王国维。
侠人在《小说丛话》中发表的文字是一篇《红楼梦》专论,其结论是: 《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此结论显示了作者视角的多元以及所用理论的多样,尽管侠人并未一一阐释其所运用的理论内涵,但有此知识者,一读就明白,作者所运用的是近代西方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的理论观念。其论述的过程(尽管是粗疏的)也贯穿着这些理论观念。譬如论及《红楼梦》是哲学小说,他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因为说人性或善或恶皆不科学,科学的方法应是直指人性,研究人的本质问题,从“人性与社会世界之抵触”来分析人性。这一认知显然是接受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观点。又如说《红楼梦》是一部社会小说: 《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足,至于再三。则何也?曰: 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隐痛者也。凡一社会,不进则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昭然,故一社会中,种种恶业无不毕具。而为男子者日与社会相接触,同化其恶风自易。女子则幸以数千年来权力之衰落,闭置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熏染,虽别造一卑鄙龌龊绝无高尚纯洁的思想之女子与社会,而犹有良心,以视男子之胥戕、胥贼,日演杀机,天理亡而欲肆者,其相去犹千万也。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以寓其种种隐痛之第一伤心泣血语也。而读者不知,乃群然也淫书目之。呜呼!岂真嗜腐鼠之不可以翔青云邪?何沉溺之深,加之以当头棒喝而不悟也。然,我辈虽解此义,试设身处地置我于《红楼梦》未著此语未出现之前,欲送一简单直捷之语,以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欲如是语而赅,真穷我脑筋,不知所倡矣。且中国之社会无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间,日受其惨,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读《红楼梦》十二曲中,凡写一人必具一人之苦处,梦寐者以为褒某人、贬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观之,直无一人而不可怜,无一事而不可叹,悲天悯人而已。何褒贬之有焉。此其关于社会上者也。侠人认为宝玉之女儿论是作者的牢骚,牢骚源于社会不仁,意在揭社会之恶态。揭社会之恶态,是企求社会之仁爱,此乃大慈大悲,“悲天悯人”。论述不能说不严密,识见不能说不深刻,只是理论色彩不那么浓烈而已。他似乎介于旧评点派与新理论评论派之间,处于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状态。
当然,侠人此文中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处。由不同视角观《红楼梦》自可得出不同结论,这可说明《红楼梦》一书内涵的博大精深,然而,政治、社会、伦理、道德诸说之间的关系如何?则并未说明白,故散而有余,集中深刻不足,也是它远不及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来得透彻之处。单就其中的某一观点而言,也有偏颇的地方。譬如宝玉的“女儿论”,包含着纵横两方面的意义: 男儿不如女儿,老的不如小的。并非说女子都比男子好,女子结婚后就变坏了,待成了老婆子就成了“鱼眼睛”了,也浊臭起来。侠人只考虑前者却忘掉了后者。
侠人的这篇《小说丛话》,在当时的小说评论中,因首次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价值,开启了小说研究的新方法而独具意义,至于其观点本身的价值倒在其次了。
二、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与侠人从多视角发现《红楼梦》的多重文化意义不同的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重在阐释叔本华的意志论,在意志论的阐释中评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理论在一篇文章中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独一无二地位,从而使得全文充溢着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和论证严密的逻辑性。
说《红楼梦评论》重在阐释叔本华的意志论,在意志论的阐述中评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可从全文结构中看得出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杂志》。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意在说明叔本华意志论哲学和悲剧美学之要旨。这一章是全文立论的基石。基本观点为: 永无止境的生活欲求是人的生活本质,人的生活皆源于此,故“生活之本质”也是人的欲求而已。因欲求不能满足,不能满足的精神状态是痛苦。即使满足了,便生厌倦,厌倦也是一种痛苦,所以“生活的性质又不外乎痛苦。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那么知识与科学能否解脱人的痛苦呢?回答是不能。因为知识与科学皆生于人的欲求,知识愈广,人的欲求愈多,“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所以知识与科学不能解除人的痛苦。若使人摆脱痛苦,必须超然于利害之外,“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能担当此任者,唯有美术。因为美术可以“使人忘物我之关系”。美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所观之物与我无关,心态宁静为优美;所观之物不利于我,使我悲伤,使人悲伤,但在美术之中,人却乐于观之,则为壮美。还有一种与美相对立的东西,令人观后“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那些淫秽之笔墨,“《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之类。王称之为“眩惑”。眩惑不能使人解脱痛苦,只徒增人之欲求与痛苦。总之,这一章从“哲学”推衍到“美学”,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只有美术可以解脱人的痛苦。并以此为尺度,衡量我国的美术,莫过于一部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人生是痛苦,唯美术可以解脱人生之痛苦为理论前提,探索《红楼梦》是如何描写人生之痛苦与解脱之道的。《红楼梦》开卷述贾宝玉之来历,说那无才不得补天的顽石“自怨自艾”,于是被带入尘世,是“但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书近尾声,和尚跟宝玉讨玉,宝玉遂将那块玉还他,又随那和尚去了,绝世解脱,“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顽石自己而已”。所以“《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自杀是希求于来世欲求的满足,不晓得来世仍是痛苦,所以不是真正的解脱。而解脱自分为两种: 一是自己虽未经历苦痛,只观别人苦痛便能猛醒,自求解脱。此“唯非常之人为能”。二是自己经历过一次次的苦痛,栽过若干跟头后,方“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此通常人之解脱之道。《红楼梦》若写非常人之解脱,则不会使普通人觉醒,其意义也自然要小得多。而此书好就好在写出了普通人解脱的过程,可使人人警醒,其意义也就更普遍、伟大。“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红楼梦》正因写出了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之道,所以更具美术上的价值。
接下去的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单从美学着眼、立论,考察《红楼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王国维认为,我国文学所表现的人的精神都是乐天的,无悲剧,也无写厌世解脱的佳作。若细求之,唯《桃花扇》与《红楼梦》。《桃花扇》之解脱是他律的,非真解脱;独《红楼梦》之解脱是自律的,是真解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叔本华论悲剧有三种: 其一是小人作祟、挑弄而造成;其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而生悲剧;其三则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此,人人思之此悲剧随时可能临于自己头上,无不恐惧”。对悲剧中人物无不同情悲悯之。这第三种是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属于第三种,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第三种悲剧因“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使人之精神得以洗涤”,所以此美学之目的正“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于是《红楼梦》美学上的价值与伦理学上的价值连在一起。
第四章接下去谈“《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所谓伦理学上的价值,实指能唤起人类使处于忧患苦痛中的人有希求解脱的勇气,并最终获得解脱。然而,在论述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王国维对人类能否真正获得解脱发生疑问:“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叔本华在他的《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一文中曾对此问题用力遮护之。王国维仍说:“然叔氏之说,徒引经据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抑徒沾沾自喜之说,而不能见诸实事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最终王国维将解脱归为理想的东西。解脱是伦理学上最高理想的东西,《红楼梦》以解脱为理想,故而其伦理学上的价值自在。然而王国维尚有余言未尽之感,遂有第五章《余论》。
《余论》主要讲研究《红楼梦》的方法。王国维首先区分历史学与美学性质的不同,从而研究美学与研究历史在方法上也有其自身差异,进而对从《红楼梦》故事中考索作者的索隐派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是文不对题。正因为《红楼梦》表现的是人类全体之性质,所以主人公是谁并不重要。“谓之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继而,王国维将以往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归结为两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前者认为贾宝玉就是纳兰性德。其所依据不过是纳兰性德中的几首词,词中曾多次出现“红楼”、“葬花”等字样,从而认定纳兰性德就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此王国维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后者认为“《红楼梦》一书是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王国维从两方面给予批驳: 其一,“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其二,美感并非单是后天实实在在的东西,也有先天的东西在。王国维从叔本华的意志论出发,认为意志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与之后的一切自然界中,先于人类而存在,故美术也存在于美术家经验之外的天才之中。既然美术有作者先天的因素,那么作品表现的内容不能与作者的经验一一画等号。既然不能画等号,那么从作品故事中寻找作者,或者说《红楼梦》是某人“自道其生平”,同样是荒谬的。他援引叔本华的话说:“故美之知识,断非自经验得之,即非后天的,而常为先天的,即不然,亦必其一部分常为先天的也。若不然,雕刻家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能决矣。”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在红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叶嘉莹先生曾谈及三点:
第一,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的理论基础,仅就此一着眼点而言,姑不论其所依据者为哪一家的哲学或美学,在七十多年(此文发表于1981年,由此向前推——笔者)前的晚清时代,具有如此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了。因为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不仅被人目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之价值,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一向没有人曾经以如此严肃而正确的眼光从任何哲学或美学的观点,来探讨过任何一篇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睿智过人的眼光,乃是《红楼梦评论》一文的第一点长处。
第二,如我们在前面所言,中国文学批评一向所最为缺乏的便是理论体系,静安先生此文……是一篇极有层次组织的论著,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所以批评体系之建立乃是本文的第二点长处。
第三,在《余论》一章中,静安先生所提出的“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日猜谜式的附会,为以后的考证指出一条明确的途径,这是本文的第三点长处叶嘉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见周策纵主编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此外,我们认为尚可补充两点:
其一,20世纪对索隐派红学的批评始自王国维而非胡适。王国维对索隐派的批评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批谬,认为美术所表现的是“人类全体之性质”,而不像历史书所叙乃具体特定的人或事,所以将小说的主人公坐实为某一个具体的人的方法是错误的。二是对其考证的具体方法批谬,即索隐派仅凭《红楼梦》的用语与某人作品中的用语的巧合,或小说中的故事与历史上某人的生活经历相似便加以附会,在两者间画等号,是不可靠的。此后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未超出王国维所批评的范围之外。
其二,王国维是批评“《红楼梦》是作者自写其生平”的观点(即后来的“自叙传说”)的第一人。王氏的批评着眼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首先认为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因为美术上之事包括作者经验之事与非亲身经历之事(他人经历自己熟悉的,想象的,理想的,先天的“非常之巧力”的),它远大于自身的经历,即作者亲闻亲见的事远远小于写入小说中的故事,所以在它们之间画等号是讲不通的。其次这种方法也不可取,因为以此法而得出的结论是可笑的。“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此说,则唐旦之《天国戏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闻亲见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若必躬为剧中人物,则《西游记》的作者必当为孙猴子了。
由此看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不但以自身先进理论和严密的论证为本世纪《红楼梦》评论树立了典范,而且从多方面纠正了以往以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的错误,为此后《红楼梦》的考证指出了正确的途径。一句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奠定了20世纪研究《红楼梦》应采用的正确方法与学术路径,其价值岂可仅视为评论一模式哉!
三、 季新(汪精卫)《红楼梦新评》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十二年后,又有季新的《红楼梦新评》问世,在论述之专、篇幅之长、挖掘之深、观点之新等方面颇为近之。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发表于1916年《小说月报》第七卷第1—6期。它是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后,又一篇以某一理论从某一特定视角评论《红楼梦》的长篇专论。不过王国维所用为叔本华的哲学,理论思辨性更强;季新所用为政治社会学,是从中国社会组织的特征——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着眼,探讨形成中国社会家庭之弊病的根源及其解决之方法,事实分析多于理论思辨,较之《红楼梦评论》更切近实际。不过二文的用意似皆不在《红楼梦》本身,是借《红楼梦》来说明他们的主张,从他们的主张里,看到《红楼梦》的价值。
在红学史上,季新第一次指出《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此说很有见地,因就研究对象而言,《红楼梦》所写的正是中国的家庭,是以贾家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中的多类家庭。小说叙事之变化,人物形象之演进,无不与家庭这一描写对象的改变相关,而小说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家庭描写来显现的。
《红楼梦》在写中国家庭方面有哪些贡献呢?季新认为它揭露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家庭专制制度的弊端,以及建立于这一制度基础上的道德礼仪的虚伪性。因“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也全是专制的,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想曹雪芹于此,有无数痛哭流涕,故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又嗟叹之”。于是,他写此文的目的也十分明了,“欲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症结一一指出,庶不负曹雪芹作此书之苦心”。又说:“此书凡写字男女,人人爱阅。如今批了出来,准科学的学理,以指中国家庭之种种症结,使人阅之,惊心怵目,知道这种家庭组织是不能不改的,这是区区的一段心事。”
其实,季新批书的目的不单此一种,因为他于《红楼梦》对家庭问题的看法也大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惜雪芹虽知此制度之流毒,却未知改良之方法,以为天下之家庭终是如此,遂起了厌世之心,故全书以逃禅为归宿。此亦无怪其然”。正因有此不满意,他要为改变此制度寻找“改良之方”。这些改良之方,主要是就男女爱情与婚姻而言的。由此而知季新此文之目的便成为两个: 揭弊与寻方。
季新是用人权、自由、平等的西方进步文明观念来揭示中国专制国家与专制家庭之弊的。这种弊端首先表现在男女爱情上。男女真情相爱,却不能成为婚姻,专制的婚姻制度是爱情的障碍,宝玉与黛玉有真正的爱情却未能成其婚姻,宝玉与宝钗未有真正的爱情却能成夫妇,却是不长久的夫妇。这两对爱情与婚姻的悲剧皆是专制造成的悲剧。那么什么是爱情呢?季新认为,须具备一个条件:“缘于自由,归于平等”,即我既重我之爱情,又重人之爱情。不在于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因为婚姻制度都不能使人在爱情上自由。“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视女子如饮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围碟,样样不同,各有适口充肠之美,下箸既频,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后,便已弃其余,直不视为人类。又何爱情之有?多妻之男子不知爱情,非苛论也。……多妻之制以女子为饮食物,因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为珍宝,亦是私心。……中国之俗,结婚不得自由,西国之俗,结婚得自由矣,而离婚不得自由。……诚以婚姻者以爱情为结合,爱情既渝,其婚姻自然当离也。于是社会学者倡为废去婚姻制度之说”。以此观念观之,宝玉的爱情也不是纯洁的爱情,是不合自由平等之爱情。“宝玉一生钟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滥及情于旁人,此不足为训。虽则一夫多妻制中,不能以此责之,然究非情之至者”。因为他重己之爱情,而不重人之爱情。然而季新的话也是有问题的。问题之一,真正的爱情是纯自私的,重己之爱情,便不可能同时重人之爱情,若重己之爱情同时也重人之爱情,便非真正的爱情。因为如果一个人炽烈地爱着一个女子,当得知别人也爱这个女子时,想到别人的爱情而主动让位,而后他再去找一个人爱,试问真正的爱情能舍去吗?他对另找的那位女子,是真相爱吗?如对后一个是真相爱,那么他对前一个,就定非真相爱。问题之二,若以此标准评说黛玉,黛玉对宝玉的爱情便不是真的爱情。因为当她知道“金玉良缘”之说后,即知他人也在爱宝玉后,为了重人之爱就应放弃他,不再去爱宝玉。她依然爱着宝玉,说明她并未真正爱宝玉,因为她的行为不符合季新的爱的理论。
季新由此观念论爱情,不但得出了上述宝玉之爱情非真爱情、非情之至者的结论,而且以此论黛玉与宝钗,又得出了宝、黛对立论。所谓对立即一个真爱情,一个伪爱情也。
季新继而认为,礼是专制的产物,是虚伪的,家庭之间合乎礼的行为及关系也是虚伪的。《红楼梦》的成绩也在于揭露了家庭关系中礼的虚伪性。这一点同样在此之前的理论评论中从未有人指出过。季新说:“彼专制者之以力服人,知人之非中心悦而诚服也,虑力有时而穷,乃不得不以礼为之辅。力之为用,能使人之肢体失其自由;礼之为用,能使人之良心失其自由。举其喜怒哀乐,不惟良心之是从,而惟礼之是从。礼所谓喜,则从而喜之;礼所谓哀,则从而哀之;驯至礼所谓可,则从而可之;礼所谓否,则从而否之。是不啻去人之良心,而代之以礼也。宗教之能使人迷信,专制之能使人盲从。其妙用皆在乎于此。”于是季新提出改良家庭的方法,然其方法也仅仅提出树立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并以此观念而于家庭成员间感化之。这种感化论软弱无力,无实施之效。
不过从家庭角度论《红楼梦》,用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探讨爱情、婚姻、礼仪与家庭、社会制度间关系,进而深入地研究《红楼梦》所描写的家庭问题,非但此前所无,此后也少有在深度上超过他的。
四、 成之《小说丛话》
成之的《小说丛话》刊载于1914年《中国小说界》第一年第2—8期。虽名之曰“小说丛话”,但因仅以《红楼梦》为例,说明自己的小说观,故而可视为一篇《红楼梦》专论。而且是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季新《红楼梦新评》之后的又一篇理论性较强的《红楼梦》专论。此篇专论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一相同点,即意在说明理论,在理论的说明中评论《红楼梦》。然也有不同处: 王国维所使用的理论是某人现成的东西,人人都晓得那是叔本华的意志论、人生悲剧说;成之所用的理论却是自己的某种理论观点,尽管其观点是化用他人理论,却有自己的体验与创建。
成之将《红楼梦》视为一部通过人物事件表达人生哲理之书,意在探讨《红楼梦》所写人物与所表现之思想。这篇《小说丛话》的基本观点不外两个: 一是小说描写社会的基本特点与方法是以小见大,以浅见深;二是其所假借的人物与事件都是某思想、观念的代表。他于文章的开端是如此阐释自己观点的: 小说所描写之社会,较之实际之社会,其差有二: 一曰小,一曰深。……小说所描写之事实在小,非小也,欲人之即小以见大也。小说之描写之事实贵深,非故甚其词也,以深则易入,欲人之观念先明确于一事,而因以例其余也。然则小说所假设之事实,所描写之人物,可谓之代表主义而已,其本意固不徒在此也。成之认为《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金陵十二钗——代表十二种人物、十二种苦痛、十二种思想。 “《红楼梦》中之人物为十二钗。所谓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亦即吾人生于世界上所受之种种苦痛也”。然而,说十二钗具有十二种个性,可;十二种个性代表十二种类型的人,可;若说十二种个性的人代表人所受十二种苦处则未必可;说十二钗代表十二种思想则犹未必可。因为一种个性并不等于一种苦处,一种苦处也并不代表一种思想。处于同一苦境的不同人可有不同个性。不同人同经历人生的一种苦处,也可生出不同的思想。所以说有十二种个性的十二钗代表十二种思想,则难免牵强、撮合之病。譬如那“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的第三支曲。成之评道:“阆苑仙葩,即绛珠草,喻人;美玉,即神瑛侍者,喻地,亦以喻一切无情之环境也。人生世上,四围无情之物,若天地,若日月,若风云雨露,若土地草木,与我相遇,不为无缘,其如终不能尽如吾意何!所谓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也,故曰:‘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也。”将黛玉喻为有情之物人,而将宝玉喻为无情之物地,那么,宝黛不能结合,岂不全因宝玉对黛玉无情吗?这显然与《红楼梦》本意不合,也与作者的原意不合。
成之分析的结论与王国维分析的结论看起来相近,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成之也认为:“《红楼梦》一书,以历举人世种种苦痛,研究其原因,而求其解免之方法为宗旨。”然实际上却有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在于二人所使用的理论不同。王国维所凭借的理论武器是叔本华的意志论,其核心在于肯定欲求是人的本质、意志,人的欲求总是受到社会的限制而不能满足,或满足之后又有新的欲求,总不能如愿。故而欲求是一种痛苦,满足也是一种痛苦,人生便是一种痛苦,而解脱之道在于美术。成之思想骨子里的东西是佛教与道教。佛教认为人来到世上总是痛苦,这种痛苦源于人的欲望,欲望是痛苦之源,而欲望生于心,只要在心中灭此欲,自然无痛苦了,所以解脱之法在于消灭欲的自修。道家则主张“齐物”,泯灭是非,即否定人的欲求。此乃二人的本质区别。
不过成之所言:“《红楼梦》之写一林黛玉一贾宝玉,所以代表人和世间无论何事不能满意也”,总体把握依然是正确的。此后从哲学上研究《红楼梦》的论著的核心观点都是这一观点的发挥。如: 人的欲望永不能满足说、表现人的失落感与心理的绝望说、爱情悲剧说、人生悲剧说等等。
五、 吴宓《红楼梦新谈》
1920年3月至4月间,《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上,连载了吴宓的《红楼梦新谈》。这篇文章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其一,就全文思维结构而言,显然是受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影响,即以西方某一理论为范式,比附被研究对象——《红楼梦》,阐述《红楼梦》对这一理论内涵的表现,并进而说明被研究对象的价值。吴宓此文是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英文教员Dr.G.H.Magnadier关于称之为杰构的小说必须具备的六个条件(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来衡定《红楼梦》的。并就这六个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简要而深刻的分析、论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其对《红楼梦》地位的评价,似又不在王国维之下。然而,王国维的分析是从哲理上把握,论证严密,但对文本的分析较为粗疏,原因在于他以理论为主,文本为次。吴宓的文章,理论上不及王国维严密,文本的分析则较细密,他是以文本为主,理论为次的。这一点对后来的俞平伯影响较大。
其二,吴宓与王国维所不同处在于,他不是从哲学角度阐释《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从文学角度分析论证《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他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所以他的论证,处处存了一个文学的眼光。这可以说是此后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如俞平伯《红楼梦辨》)的滥觞。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即吴宓在说明并证实自己的观点时,总不忘与西方小说与西方思想加以比较,可视为最早、最自觉地采用比较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人。由于他学贯中西,对西方理论与小说甚是熟悉,故运用起来自然娴熟,对发掘《红楼梦》一书的艺术与精神真谛甚有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其四,有几种对后来深有影响的观点。一是“贾宝玉是作者自况说”。吴宓说:“贾宝玉者,书中之主人,而亦作者之自况也。”又说:“甄贾二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此观点发布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版之前,胡适或受其影响。二是以黛、宝情缘展示贾府盛衰说。吴宓云:“凡小说巨制,每以其中主人之祸福成败,与国家─团体─朝代之兴亡盛衰相连结,相倚伏。《石头记》写黛宝之情缘,则亦写贾府之历史。”这直接启示了以后的写宝、黛爱情与贾府兴衰的两条线索说。三是指出《石头记》表现的是一种“归真返朴之思想”,并对这一思想做了哲学上的说明。四是指出该书“虽写贾府,而实足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全副情景”,开启此后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五是指出了《红楼梦》一书结构上的特点与价值: 有主干有枝叶;如河流入海有起始演变,中无断裂;有因有果,合乎情理,前有伏线,后有余波,不可无端造作;首尾前后照应,无矛盾处。六是指出作者写人的特点:“合乎人情;其性行体貌等,各各不同,而贤愚贵贱,自合其本人之身份。且一人前后言行相符,无矛盾之处;人数既众,于是有反映,两两相形,以见别异。”又特别指出:“又至善之人,不免有短处;至恶之人,亦尚有长处。各种才具性质,有可兼备一身矣。”此说远在俞平伯、鲁迅之前,故价值自在。
六、 陈独秀《〈红楼梦〉新叙》
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是《红楼梦》评论史上的一篇具有转折意义的论文。从王国维到成之的评《红楼梦》,都是用政治、道德、社会学、哲学等非文学的观点来透视《红楼梦》,所言《红楼梦》之价值,皆非文学的价值。陈独秀的这篇叙言,却换了个角度,他更走近《红楼梦》本身,步入《红楼梦》的文学世界。他的基本观点有三: 一是为《红楼梦》写叙的理论依据。西洋小说起于神话,起初善写故事,到了近代,受实证科学方法的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则交于历史家了。而中国古代小说起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后来仍然是善述故事,那是因为小说家与历史家没有分工的缘故。结果既减少了小说的趣味性,又减少了历史的正确性,两败俱伤。小说家兼历史家的习惯是小说与历史发展的两大障碍。二是用这一理论评论《红楼梦》。《红楼梦》既善述故事,又善写人情。但善述故事的地方读来令人可厌。领略《石头记》应领略其善写人情的地方,写小说也应作善写人情的小说。三是指出了批评《红楼梦》的方法,而这一点最有价值,对此后的《红楼梦》评论具有导示意义。他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见陈独秀《红楼梦新叙》,载于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的确,《红楼梦》的评论应该成为真正文学的评论,真正评论其善写人情的地方,关注其具有文学趣味的东西。吴宓虽也用文学眼光研究《红楼梦》,但并未有如此的理论自觉意识,明确将思想的评论与故事的考证从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清除出去,从而提倡纯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后俞平伯的用文学眼光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文本分析方法,可视为陈独秀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用文学的眼光分析文本的研究方法与思想始自陈独秀的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