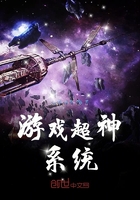二次革命
孙文迅速回国,准备武力讨袁。
黄兴以下全部反对,认为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当诉诸法律。
孙文怒道:“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陈其美附议。
国民党此时的地盘只有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湖南都督谭延恺虽加入国民党,但奉行自治)。结果,当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时,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均不买账,气得孙大炮逢人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绝非袁世凯的敌手。
不过不打紧,国会已经开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帮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
首战便是“善后大借款”。
所谓善后,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烂摊子——各种外债加赔款共计一千二百万英镑。
政府不但没钱,还等米下锅,只好再举新债,结果唐内阁时的首轮融资即在同盟会一片“丧权辱国”的唾骂声中偃旗息鼓。
可民国百废待兴,总不能宣告政府破产吧?于是,暗地里的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同五国银行团(美国主动退出)达成了总计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由于列强坚持认为中国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信用等级偏低,故定了个奇高无比的利息,算下来到手的钱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传出,舆论鼎沸,国民党更是一副国亡无日的表情,对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签订借款合同这一悍然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捶胸顿足。
孙文给五国银行写信拆台,众议院则命内阁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龙潭虎穴,谁敢去闯?最后还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马。
国民党籍的议员一见到段,登时血气上涌,有跳到凳子上大骂赵秉钧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凯的,甚至还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党的议员则默不作声,静观场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岿然不动,等国民党闹够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即覆水难收,已成定局,请你们批准是给你们面子。
议员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起来,段祺瑞始终只有这一句回答。
参议院的情况也一样,稍好些的是袁世凯亲自给议长张继(国民党籍)写了封信,语重心长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议员商议,认为合同既已签字,袁世凯势必蛮干到底,国会的否决完全无济于事,还有损《临时约法》的权威。
既然秀才解决不了,就交给兵吧。
孙文同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恺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袁世凯怒了。
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数国的外交承认,孙文又来败坏政府的国际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对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为反击,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联电指责孙、黄“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为了逼南方首先发难,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果然激起反弹。
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之名发表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安徽、广东、湖南和上海等地陆续呼应,声势浩大,颇有重现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势,史称“二次革命”。
其实,由于兼并了其他几个党,比起同盟会来国民党的纯洁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许多老同志,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黄兴虽不在此列,但对贸然举事也很动摇。因为他认同《纽约时报》的说法,清楚所谓的“天下云集响应”只是表象:
当前的所谓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内战不可能持续太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稳固。
黄兴举棋不定,气得陈其美诬赖他收了袁世凯的钱。
两人一理论,陈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说程德全出兵来自证清白。
性情刚烈的黄兴当即赶赴江苏都督府,“扑通”一声给程德全跪下,求他发兵。
程督不紧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
黄兴给陈其美打电话,答称:“明天有两车钞票运到。”结果第二天一查验,全是已经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诸君立场一致,但拿废票采购军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决不做!”
看似浩然正气,实则明哲保身。
南方议论未定,北军兵已南下,相继攻克安徽和江西,气得柏文蔚痛骂黄兴“一将无能,千军受累”。
不久,张勋带着还乡团杀回南京,虚张声势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孙、黄再次流亡日本。
长江以南被袁世凯全盘接收,各省都督均换上了自己人(湖南汤芗铭、安徽倪嗣冲、江苏冯国璋、广东龙济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极点。
列强相继表态:只要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即给予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选票长啥样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宪在先,其次才由国会根据宪法来选总统。
制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袁世凯想赶在本年的双十节(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联合十九省都督发表通电,建议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虽说二次革命的惨败让国民党一蹶不振,但毕竟还占据着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袁世凯一面命梁启超以共和党为基础,兼并数党后扩大为进步党,一面对国民党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诱之下,士气低迷的国民党议员有的改投进步党,有的坐等袁世凯来买他们的选票。一时间,报纸上满载国民党人的退党声明,进步党趁势拿下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之席。
袁世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孙黄乱党”发出通缉令,罪名除煽动叛乱外还有贪赃枉法,说查账后发现孙文一里铁路都没修,却挥霍挪用了大笔公款。
刚在日本落脚的孙文听说后,痛定思痛,认为所有的噩梦都是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开始的。混进来的四个党目无尊长,良莠不齐,污染了组织,破坏了纪律,必须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诫全党同志:“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对唯一的领袖绝对服从。”
紧接着,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级,新人入党时必须按手印发誓。
黄兴、汪精卫、李烈钧、柏文蔚、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元老纷纷大摇其头,敬而远之,只剩陈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几个不离不弃。
计划中的“三次革命”从此遥遥无期。
北京。
辞去了总理之职的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
对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荣誉和信任,但以总理之尊改迁于此,只能是失势的标志。
毁宋一事,自作主张的赵秉钧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现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担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时任顺天府尹)去参加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的宋教仁追悼大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气壮道:“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对象可能是陈其美,因为当时对陈的质疑一度甚嚣尘上,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凯,至少国民党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治馨的话极具杀伤力,且捕风捉影的事,袁世凯又不好站出来辩解,非常恼火。
不久,王治馨贪污案发,袁世凯公报私仇,重判其死刑。
赵秉钧自知闯祸,赶紧递了辞呈,袁世凯和国会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一职。
相位不宜久悬,七零八碎的内阁也到了重组的关头。
国民党大势已去,进步党锐不可当。以熊希龄为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的“一流人才内阁”华丽亮相。
这帮学者型官员全是社会名流,无可指摘,但袁世凯更看重的是他们进步党党员的身份。
很快,国会拟定了宪法中的一章——《总统选举法》,以便先选总统。
三天后,参众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走入会场,举行总统大选。
最高领导人的任命,在这片土地上终于实现了竞选而不是竞猜。
根据游戏设定,无记名投票共分三轮。
想第一轮就搞定对手,得票必须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则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的胜利条件同第一轮一样。若仍决不出胜负,则得票最多的两人进入终极PK;
在扣人心弦无比刺激广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该环节,谁的得票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即为赢家。
袁世凯一合计,发现问题很严峻。
投票人里有三百五十多位国民党议员,只要其中超过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两轮就无法胜出。而等挨到第三轮,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危险系数还很大。
没办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当天,会场外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团。三千多名团员自称热心市民,专程前来维护竞选秩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批社会闲杂(部分是军警便衣)的监督下,会场的确井然有序,因为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偶有议员想出去买根油条打个豆浆啥的,刚跨过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会。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点心,被公民团拦下,经反复解释,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用的,方准进入。
国民党本部送来的午餐则始终不予放行,气得国民党议员冲外面破口大骂,公民团则恶狠狠地回敬道:“饿死你们也是活该!”
为了早点慰劳自己的肚子,议员们抓紧时间投了两轮,袁世凯位居第一,黎元洪紧随其后,孙文和伍廷芳垫底,都没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三。
时已薄暮,二选一的巅峰对决拉开帷幕。
国民党议员交头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嘱声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
然而,更多的人选择向现实低头,因为袁总统明码标价:一张选票,大洋八千。当有人质问某出卖选票的国民党议员时,对方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都要当选,拿这笔钱作亡命费也好。”
终于,汤化龙宣布袁世凯得票过半,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
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盖因国民党不愿鼓掌,进步党精疲力尽也懒得鼓。
公民团领了赏钱,一哄而散。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毫无争议,高票当选。
专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当天,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
典礼既不在国会也不在总统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数千来宾齐聚太和殿广场,静候袁世凯莅临。
上午10点,三百多名头戴金线军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卫兵列队进入广场,在来宾席前分东西两侧立定。
随后,四顶四人抬的肩舆出现,载着此次大典的仪从梁士诒、唐在礼、荫昌和夏寿田(总统府秘书)。
终于,身着海蓝色大元帅服的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广场。
下轿后,由梁士诒等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仪式在礼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轮到总统宣读誓词时,离主席台很近的国民党议员韩玉辰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态度极不严肃,一句“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八个字念得铿锵嘹亮,余者则声如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
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
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
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