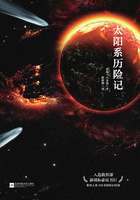千层菊开花之前,风中有一股酒味儿。去海滩哎,去哎,小村里的年轻人又喊又叫。没有办法,疯张的日子又来了,?鲅又该摇头摆尾啦。海滩的酸枣棵上挂满了枣子,年轻人急不可耐地下手了。他们每年都打下一堆堆酸枣,搓去枣皮枣肉,把枣核儿卖掉。没人敢鄙视荒滩上的这个季节。赶鹦领上她那一伙在丛林中出没,又黑又长的辫子任人抚摸,两条罕见的长腿像小马驹一样踢踢踏踏。大家都带了干粮,中午就待在野地里,点上一堆堆火。太阳晒着灰烬,晒着赶鹦的脑壳。她的近旁就是憨人,他像老羊一样打着瞌睡。赶鹦常常去捏他结疤的鼻子。烈日下大伙全躲进树阴里了,赶鹦叫喊起来,有人哧哧笑,并不回应。憨人拔来一棵酸菜,把老叶剥下来吃了,将剩下的嫩叶芽送到赶鹦嘴上。一条绿花蛇弯弯扭扭爬来,憨人救火似的扑上去,捧起大把沙土扬撒……
“你知道千层菊花蕊儿是什么味儿吗?”柳树阴下高颧骨的喜年问姑娘金敏。金敏长了一副平肩膀,显得方方正正。她一条腿跪着,一条腿伸出——喜年的头就枕在这条腿上。他的脸土黄,脸形像枣核。金敏不答。他的两手插进黄色的乱发中,笑了。太阳花花点点印在他们身上,蚂蚁也爬上来了。金敏看到喜年的淡色胡子,就伏下身去亲了一下。喜年梦呓般咕哝:“我听见河水声了,噜噜噜噜,像大风刮布单哩。”金敏哧哧笑了:“你长了只驴耳朵呀?”喜年说真的,小时候蹲在河岸上能听见水草间有大鱼咕咕叫……他的耳朵蜕化了,如今只能听见人的声音——谁都能听到的一些声音。金敏撇撇嘴。喜年一直闭着眼,却说:“你撇嘴了。”金敏用手挡在他的眼睛上方,他马上说:“把手拿开。”金敏说:“天唻,古怪的人!”她捧着喜年的头,认认真真地看。他不算好看,可他是做活的好手,她亲眼见他用手推车推过两三个人才推得动的黑土。那时他的裤子用力一扭就破了,露出了脏乎乎的皮肉。他的鼻头像小猪一样,永远湿漉漉的。她用衣襟给他擦了一下鼻子……有一年秋天,喜年和憨人爸在场院看粮,她去看他们,结果出了事。憨人爸叫弯口——他夏天图凉快,在大碾盘上蜷着睡了一觉,醒来后腰永远也挺不直了,那弯儿就像碾盘的弧度一样。弯口彻夜不眠,喜年胡乱串游。金敏见他钻到了场角的大草垛子里,以为赶鹦那一帮也在,就随他进去了。谁知里面塞紧了麦草,往日的通洞不知被谁堵死了,她想倒退回来,结果洞口也没了。她只得硬着头皮乱扒。有一只大手从草间伸出来将她揪紧了,她刚喊了第一声嘴巴就填进了一团草。那个人像刺猬一样拱过来,一声不吭……第二天金敏到田里做活时老要偷偷抹泪,喜年走过去说:“不用生气了,昨夜是我哩。”金敏还是哭。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终于明白这辈子是喜年的人了。她不敢想她会嫁给外村人,她天生就是?鲅老婆,要为这些远道迁来的人传宗接代哩!从那时起她就知道心疼他。如果搞到一块巴掌大的玉米饼,她就用一层层土纸包了,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暖着,寻个机会给他吃。这个男人哪,这个准定会做丈夫的家伙啊,你的头好沉,压得我的腿都麻了!我的好人哪,俺想夜夜搂抱的人哪,你让俺好好看一会儿,俺兴许今年冬天给你做个小棉袄呢!金敏看着这张风干了似的、毫无油性的脸,突然发现了三两道皱纹。她叫起来——不足二十的人啊!喜年一睁眼,金敏发现他长了一双马眼,只不过太小,向上吊着。她倒吸口凉气,心想喜年是大马托生的啊,注定了一辈子拉车挨鞭抽打的命——他不会有更好的命了!金敏不顾一切地亲着、亲着。喜年嘿嘿笑了。这是老实人的笑声啊——他是老实人吗?他压住了俺,他把两个土人的命贴到一块儿了。金敏眼窝热起来,她要一生一世学做他的好女人。比如这顿午饭吧,前一天她不顾家里人的盯视,调制了地瓜面,又铺了一层玉米面,掺了浸好的干槐花,卷起来拍成一张饼。他们两人分吃了这张饼,周身甘甜。他俩的头发揉在了一起,分也分不开。风把远处的绿草吹得火焰一样燎动,散在其间的野花如同星星般闪亮。喜年看着前方,快活得连连呼叫:
“赶鹦啊!长腿野马啊!满滩上跑啊!”
金敏站起来。喜年突然不吱声了。他们都定在了原地——一片白毛毛草间,肥一个人踟蹰,两腿越来越沉,差不多伏在了地上。你怎么了肥?可怜的肥,大海滩上哪里不是成双成对啊!金敏和喜年彼此使个眼色,一齐掩上了嘴巴……
肥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在街巷上游荡,一个人走在大海滩上。她离开赶鹦他们,一边打酸枣一边往前走。她挥起杈棍一下一下打在枣棵上,让枣子溅在篮子里、溅在汗淋淋的脸上。中午热辣辣的太阳啊,把一地白毛毛草快燃着了,她一迈进这片草地就烤得难以支撑。她又感到了那对目光,就像在茫茫夜色中、在小村的街巷中一样。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执拗地直射过来。她猛地止步回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毛毛草地。肥的一双手不由得按在胸前,按住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她仍能感觉那双目光——这会儿正由于长久的注视变得信心百倍。她低下头,转过身子走开。四周没有一丝声息,连喘气的声音也没有。她知道那个人不会追赶,但他会尾随着她,走过一千一万个白天和夜晚。她想绕开什么。那双目光把她灼痛了,她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跑啊跑啊,跨过荆棘,钻进灌木丛,连头也不敢回……
金敏和喜年仍注视着这片白毛毛草,他们终于从中发现了一个伏卧的人——如雪的白发、倔犟的脖颈、锥子似的目光,那是老刘家的后代龙眼哪!喜年害冷似的吸气。龙眼独自伏卧,他好孤单。肥刚刚跑开,你筋骨铁硬的手指抓不住她吗?肥真的要像传说那样飞出小村吗?那你该驾起祖宗留下的破车去追,扛起老辈儿传下的锈枪去打。肥也是?鲅,她注定了要在这片草窝里生籽儿,繁衍出一群身上有灰斑的小鱼来哩……喜年看着龙眼,张大了嘴巴。他看见龙眼旁边是半篮子酸枣,一根打枣棍像拐杖一般握在手中。他多像一个白发老人——啊不,他的眼里还有刚刚烧起来的火,脸上还没有打皱哩。他从娘胎里生出来就顶着一头白发,那是从老辈的血脉里传下来的。虽然他的爷爷、父亲,还有母亲家里都没有这样的少白头,可那愁根儿一代一代积下了,最后让龙眼生着一头白发出世。中午的太阳照耀着,白发银亮,与一片白毛毛草浑然一体,远远望去极难分辨。
赶鹦在远处打起了又长又亮的口哨。年轻人从树阴下走出,打着哈欠,提着篮子和杈棍。他们蹦蹦跳跳,一抬腿,裤子上没有缝牢的补丁就一起舞动。肥、金敏、喜年、年九、小欢业、赖牙的独生儿子争年,都拥出来了。年九露着肚脐,不断地提一下裤子。有个叫香碗的眼皮上长小疤的姑娘走到赶鹦跟前,说:“我睡了,年九伸手捏我。”赶鹦吓唬年九说:“送你去找方起。”年九迎着赶鹦腆起肚子,直挺挺地倒下去。赶鹦再没有理年九,扬着手说:“干活了!干活了!”大家欢叫着找枣棵下手。“千层菊花蕊是什么味儿呀?”喜年像女人一样小步奔跑,呼叫着。赶鹦说:“不要散开,他们说来就来!”——外村的年轻人也来荒滩,如果人多,就上来抢枣子,如果人少,就站在沙岗上,叉了腰一齐呼道:“?鲅!?鲅!”这边追上去,他们就撒丫子蹿了。那时大伙儿的一天就给毁了。这片荒滩啊,漫漫苍苍,蛇鸟兔子,什么都自由自在哩,凭什么让小村人忍受屈辱……大家互相叮嘱,后来才发现少了一人——龙眼呢?
“龙眼龙眼少白头龙眼哩……”
龙眼躺在没膝深的白毛毛草间,风把白绒毛擦到他的脸上,滑滑的柔柔的。他一声不吭。白毛毛多像他的头发啊。村里老人说:“少白头龙眼,生个孩儿也会是白头发。”多少人议论猜测他这头白发,连他自己也疑惑起这白发的来历了。白头发根儿到底扎在哪里?一个愁字缠住了龙眼。雨天他跟在一群大人身后抢捡地瓜干,那些人唉声叹气说,龙眼是在娘肚子里闷坏了。龙眼像中了箭镞一样,一下蜷在了雨地里……一个生命刚刚开始那一刻小得像尘粒,它游动游动,不巧落在了一片苦海里。“他爸,他爷,他老爷爷……”他似懂非懂地听。他更早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他从黑暗中挣扎出来,睁开眼的那一刻看见了什么?那时候的头发真的像白毛绒绒一样颜色吗?他在娘胎里怎么知道愁?也许他投胎后反悔了,开始愁苦,直熬过了十月怀胎的漫长日子?也许是一辈一辈分泌的愁汁把他泡白了?母亲像海一样的愁苦之汁啊……龙眼发狠地揪下一绺绺白毛毛花,直吞下肚子。天哪,他好饿!吃吧,这些白毛毛,让我把你嚼个精光。这是几辈人吞咽过的食物了,像棉絮,像白雪。老爷爷挑着担子奔走在雪地上,拉扯着一个女人一个娃娃。白雪的反光快要刺瞎了老头子的眼睛,他全靠那个大头娃娃牵引。向北向北,听说北边开满了千层菊花,娃娃妈你忍住一口气。向北向北,听说北边有喷喷香的玉米饼,让咱一家三口咬住一块金黄玉米饼好了。雪地上的脚印一会儿变成了一溜儿不断线的银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跟上来,抢着,追着……那群人直追了两天两夜,捂住破衣烂衫,低头一看,银币全都化成了水。他们懊恼得呼天抢地,可这会儿已经回不去了,只有跟上这溜脚印儿,向北向北。
龙眼躺在了白毛毛花儿间。“奶奶,老奶奶……”“愁死人啊,娃他爹,娃儿活不成了!”女人揪紧老头子的衣襟,只一扯就扯下一大块。这块破棉絮立刻缠到了大头娃娃身上。大头娃娃脸是紫的,嘴唇发青。“饿……哦。”她弯腰掏一把雪填进娃娃嘴里。“愁死人啊,他爹!”老头子顿足,伸出巴掌打了女人一下。走啊走啊,走过了冬天。白毛毛花儿开放了。采棉花似的白毛毛花吧,赖牙喊。全村人都出动了,红小兵带着脏黏的酒壶上了荒滩。“采下做棉被哩,做棉裤棉衣哩!”大脚肥肩飞快地采摘。都穿上了厚厚的白毛毛花棉装,盖上了厚被子。夜里它深长的香气撩拨得人在被子下扭动不停,汗水湿了席子。老爷爷想不到会有老天爷送给的白毛毛花,女人也只会捂住娃娃喊:“愁死人啊……”大头娃娃死在了雪路上。龙眼一辈子见不到伯父了。大朵雪花覆盖了一溜脚印,一个死人。剩下的人走过冬天吧,走到白毛毛花里,去踩这片没有汁水的雪。赖牙采着白毛毛花,骂着那个老人,说他第一个来搭下窝棚。该死的,他先有了窝儿,又生了孩子。先有窝儿的人就该当地主。一个黏黏的小孩儿像条虫,在棉被上滚动,沾满了白毛毛花绒。谁见过小草窝里刚孵出不久、闭着眼睛的麻雀幼崽?它在草窝里颤动,嫩皮包住了一层血肉,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白毛毛花儿下面有一个圆圆的小窝儿,那是用金黄如丝的小草编织成的,光滑柔软像个小篮子,里面盛了三个红嘟嘟的幼鸟——龙眼伸出手去。“呀呀呀!”它们嫩黄的小嘴一起张大了。小嘴在龙眼坚硬的食指肚上啃着,小脖子拧了一道麻花褶。“说什么化成水的银币,呸,传说的瞎话。”父亲把老羊皮袄抖一抖披上,吸起了辣烟。“龙眼妈,你这条不死的母狗。”他吆喝一声,龙眼妈赶紧从里间出来。她手里捧着一个火罐。“赖牙怎样,我也要怎样。”父亲露出一个膀子。母亲伸出食指从水碗里蘸了点水抹上去,接着点火、扣上罐子。皮肤吱吱地收紧了。“哎呀!我的妈妈呀!”他像挨了刀一样嚎叫,身子绞拧,头往墙上撞,又一下蹿了起来。“你杀了我吧!我睡你祖宗!”他放声大骂。白花绒绒沾在黏糊糊的男婴身上。“他痒哩,痒哩……”女人眼泪汪汪。“你留那东西做啥?给他吃哩!”她挤了又挤黑乳房,一滴奶都没有。“天哩,愁死人啦!第二个娃也不保哩……”父亲一次次讲他活过来有多么不易,说那会儿就像一条虫。他活过来,并且娶妻生子。母亲在他三岁时饿死了,父亲在他十岁时也倒下了,是被地瓜噎死的。“要紧是有个传香火的人。”父亲盯着儿子雪白的头颅说。他磕着烟锅,烟灰飘到了白发上。他说:“赖牙是报应。大脚肥肩活该不成,断根了。”他们的争年是要来的,说不定是外村人生在高粱丛里的一个野物。那不是?鲅,不是小村种儿。“我看赖牙这村头儿做不成。”父亲咬着牙:“我要起事不成,还有孩子哩。”他盯着星夜……天哪,没有边缘的黑夜,永远游不到尽头的黑夜!它的中央漂着一颗白色的头颅。一个粗哑的嗓子在堤岸上呼叫,那是母亲的声音哪。他游啊游啊,迎着母亲的呼唤。有几次他要沉下去了,但终于还是挺过来。堤岸在哪?哪里才是边缘?巨大的惊恐使他浑身战栗。游啊游啊,渐渐听到水浪拍岸的声音了。那时他哇哇大哭。母亲终于抱住了他,第一句就问我儿为什么白了头发?哦哦,那是急的、愁的,是绝望之火烤成的。母亲把乳头对在他嘴上。他用力吸吮。天哪,它是干的……饿呀,饿呀,龙眼在白毛毛花里滚动,揪了白绒绒毛往嘴里填。泪水涌出来,差一点就噎死了。透过泪花他望到了什么?他望得到茫茫夜色的背面、他的遥远的来路?他记得三岁那年父亲开始拔火罐。火罐扣在肩肉上,肌肤急急收缩到一起,母亲给男人膀头上盖了一块脏手巾。“遮遮盖盖,变出个妖怪。”一句歌儿飘过脑际。又停了三五分钟,母亲动手取火罐了。多么坚牢的东西,她憋得脸通红,火罐还是没有取下。父亲大骂。母亲的汗珠一滴滴落在儿子的白头发梢上。突然哇一声,火罐取下来了。火罐腔里黑洞洞的……“人死如灯灭。”父亲的先人,那个高个子黑老人手持拐杖走近了说。他在说自己过世的女人,好像没有一丝牵念。黑老人浓浊的异地口音唤着龙眼妈——她小步跑过去,从地上捡起一根湿乎乎的杨树枝条,从老人后衣领那儿插下去。她一下连一下捅着,老人舒服地哼哼。“真解痒,真解痒。”后来妈妈不停地呕吐,头发枯得像苘麻。“我的儿啊,儿啊。”她一边叫一边抓紧儿子的手。父亲去找红小兵,后来戴着镜框的赤脚医生出现了。那人摆摆手,父亲拉上龙眼就走。他一步三回头,惦着母亲。身后咚的一声,门关了。他闭了眼也能看见赤脚医生取出一把刀,按按这儿,戳戳那儿,血水涌了出来。“妈妈!”他大叫一声,父亲狠狠一扯。刀子在妈妈身上剜着什么。妈妈的皮肤如干燥的雪层一片片切开,露出一大块变色的干结。赤脚医生气喘吁吁,取出小村人都不陌生的粗劣玻璃针管,给她注射。“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父亲握紧他的手腕。他听着妈妈的呼叫苦熬,熬白了最后一根头发……白毛毛花如醉如痴地歌唱,摇曳不停。白绒绒被西南风吹得纷纷扬扬,一朵朵飞向低空。云絮起起落落,覆盖了少白头龙眼。雪白的头发与其融为一体,再好的眼神也难以分辨。
对这伙年轻人来说,月亮升起之后是一段最美妙的时光。从天黑到月亮升起之前,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不停地咀嚼酸枣,躺在温暖的沙土上歇息。他们等待月亮,盼望在凉爽的月色里奔跑。那时令人讨厌的外村人都回家去了,他们可以在开阔草地上大声呼号、跳跃,追逐赶鹦徐徐扬起的长辫。夜色里,年九在一个角落骂着香碗。憨人拍打节奏,想趁月亮升起前引逗赶鹦说一段数来宝。一个刺猬走过来,憨人起身去捉。刺球儿滚动不停,滚到赶鹦跟前舒展开身子,伸长鼻子嗅着。憨人咕哝:“说段数来宝吧。”山狸子在远处连声喊叫,月亮如果禁不住它的呼号就会提前溜出来。长尾巴喜鹊、狐狸、鹌鹑、野獾,它们都等着在月色下梳洗打扮,搽上花粉去喝老兔子王酿的老酒。据说老兔子王已经在荒滩上活了一百七十二年,如今只剩下一颗牙了。只有红小兵见过他,他们之间偷偷交流着酿酒秘方。他们的胡须都白了,一颗心却越变越善良。月亮快出来吧,快让俺借个光吧。不知是谁念叨起龙眼来了,大家都转脸去看肥,肥沉默不语。更远些的橡树丛里,喜年和金敏趴在地上等月亮。喜年说:“我不会有孩子啦。”他脸色阴沉下来。“为什么哩?”喜年叹口气。“到底咋啦?”喜年咬咬牙关:“前些年我爬树逮鸟,让树杈子把身子硌了。”金敏想笑:“那有什么!”喜年摇头:“不止一次了。真的。”金敏不吱声。一会儿,她抽噎起来。不知停了多长时间,当他们一齐抬头时,发现又圆又大的月亮在东边点亮了!老野鸡一声连一声喊叫:“渴——渴死!渴呀……”
赶鹦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所有人都抖掉沙土跳了一下。“上沙岗去呀!跑哩!”大家喊着,伸着懒腰,有人还就地翻了个斤斗。年九的腰在月色下看去像狗一样细,赶鹦忍不住用手掐了掐。年九第一次红了脸嚷:“大姐大姐。”这时又有人喊:“看!”
龙眼提着篮子,手拄杈棍出现了。
“龙眼龙眼龙眼少白头龙眼哩!”
龙眼一直往前走。他雪白的头发在月色下闪亮,直刺人眼。近了,大家都看见他衣服上、头上,到处都是白毛毛绒。再看篮里的酸枣,只有小半篮儿。“龙眼躺在白毛毛花地里睡了一觉哩。”眼上长小疤的美女香碗说了一句。“咱走啊,咱到月亮底下去。”赶鹦第一个奔跑起来,长腿跳腾。一匹热汗腾腾的棕红色小马,皮毛像油亮的缎子,光溜溜的长脖儿小血管咚咚跳。亲一下你乌亮亮的大眼啊,骑手不忍心使用鞭子哩。抓住马尾、马缰、马鬃,好骑手先伸手一纵,别怕摔跤。月色下真像追赶宝驹一般,连憨人那沉重矮小的身体也在沙地上弹动如簧。他们冲出树林的阴影,盯着被月色挂上一层银粉的矮灌木梢头往前跑。橡树的宽叶儿上有露水串儿,树隙的茅草尖上有金豆子在跳荡。火苗儿隐隐约约燃起来,渐渐听得见噜噜声了。一只兔子箭一般射去,飞蹄在火焰之上不敢久留,一点一荡掠过旷野。赶鹦终于说起了数来宝,喉咙又清又脆,四周鸦雀无声。只是在她煞住话尾的那一瞬间,人们才听见了另一片嘈杂。没有人怀疑:那是狐狸和草獾它们——一支急于享用老酒的队伍出动了。
千层菊花没有开,可是年轻人已经闻见它的气味了。就在一道自然形成的大沙岗的漫坡上,在夏季的最后一天,火一样的千层菊会同时开放。这是一只神奇的大手播下的种子啊。千奇百怪的动物在花地里狂欢,嘶叫、奔跑、互不伤害地咬架。它们的鸣唱使云彩变得通红,使天空的太阳微微颤抖。从早到晚,皓月当空,动物们在花地上狂欢。这样直至第二天凌晨,它们才敛声息气,隐到树丛后面。这会儿疯长的茅草把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月光如水,浇泼着这漫坡草地,让你听得见咝咝的渗水声。
他们伫立在沙岗上遥望。荒滩上的一切都在这会儿获得了生命,活得生意盎然。有什么在前方嘀嘀叫唤,赶鹦将拇指食指含到嘴里与它应答。满天的星星在口哨声里溅出了火花。赶鹦的腰身在月光的洗涤下显得越发娟秀,周身上下都散发出再清楚不过的千层菊花味儿。她的打了补丁的碎花裤子、那件褪了颜色的条绒布衣服,都变得一片芬芳。她提议将篮子放在沙岗上,大家跑到坡地上去——说着第一个冲下了沙岗。大家欢呼着,像骑兵高举马刀那样擎起杈棍跑去……宝驹的鬃毛在月色里奓开了,微微泛红。追赶宝驹啊,油黑闪亮、毛色像缎子一样的宝驹啊。就连憨人也一蹦老高,就连肥也气喘吁吁。无边无际的荒滩原来有一匹花斑骒马,老辈儿人比比划划讲过骒马的故事——可是这十几年里它没有了。为什么?就因为花斑骒马转生了赶鹦。谁由什么转生得慢慢琢磨……赶鹦直跑得满脸涨红,胸脯一耸一耸像有什么要钻出来时才止步。她又躺在了草上。大家也躺下来。有人把腿搭在别人腿上,那个人就再搭另一个人——所有人都腿脚相连,像编草垫那样。年九的腿压到了香碗肚子上,香碗就骂。有人讲起了荒滩上的鬼怪故事,说蚂蚱变成的鬼像拇指那么大,兔子变成的鬼喜欢抽烟——看到夜间那些闪亮的火头儿了吧?那是它们在过烟瘾。正说到这儿有人喊了起来,大家一转脸,发现沙岗上有火头儿一闪一闪。谁都不吱一声地呆坐起来。一点、两点……十个火头儿!正看着,突然那边嬉笑起来。“那是外村人哩!咱的篮子放在那儿。”大家有些慌。赶鹦说:“不怕他们。我们去拿篮子。”
一群外村青年站在岗顶,有男有女,也是打酸枣的。这会儿他们居高临下看着过来的人,都挤着眼。“?鲅。”一个男青年吐了烟蒂说。赶鹦他们在岗下停住了。“不要篮子了吗?”有人涎着脸说一句,其余人大笑。赶鹦说:“走开!别碰俺的东西……”“俺的俺的。”岗上人学着她的腔调。一个斜眼小伙子抓起脚下篮里的酸枣嚼了嚼说:“好甜!”金敏咕哝:“不要脸。”那些人又笑。斜眼小伙子踢了一下,篮子顺着漫坡滚,酸枣全洒了。金敏哭叫着:“我的枣儿啊……”大伙儿都举起了杈棍。岗顶的人叫着“不好不好”,一齐踢翻了脚下的篮子,转身往回跑去,发出夸张的呼号。小村里的青年追赶上去,没有人去拾篮子。憨人的喘息伴着大家杂乱的脚步,龙眼、喜年和赶鹦一直跑在前边。不知跑了多远,突然外村人定住了。那个斜眼隔着一丛槐树问:“还真想比试吗?”喜年沙着嗓子嚷:“赔俺的枣!”“那你过来!”斜眼说着用木棍钩住了刺槐的枝干,喜年真的高举杈棍走上去。眼看就要走到刺槐跟前了,赶鹦和龙眼猛然意识到什么,一齐叫着喜年——可是晚了。斜眼的钩子一松,刺槐树的枝枝杈杈、数不清的尖刺一下子反弹过来!天哪,有一根粗枝条抽在喜年脸上,他立刻捂脸倒地……赶鹦他们扑上去,扒拉喜年的手,喜年死也不肯松手。“妈妈呀,哎呀我的妈妈呀。”喜年的脸在月光下煞白,有什么黏黏的从指缝间流出来,是血!喜年把手移开,大家都看到他左眼当中插了一根槐刺……金敏跪在地上。赶鹦慌了。都想为喜年拔出槐刺,可又不敢动手。还是喜年自己摸索着,嘴里发出嗯的一声,把槐刺除掉了。血不断地涌出。大家把他的头捧起,用包干粮的布围上他的眼。正做着,有人发出“啊啊”大叫——原来是龙眼举起了杈棍。“龙眼!龙眼!”大家一齐喊。那些外村人见一个头发雪白的人追过来,转身就逃。龙眼疯了!他追上一个打倒一个,所向无敌。不知多少人呀呀哀求,倒在树丛间……“龙眼要杀人啦!”憨人大喊。
黎明时分,赶鹦他们收拾起洒在沙岗上的酸枣,抬着绝望的喜年向村里走去。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金敏偶尔发出一声哽咽。龙眼离开人群一个人走着。他不知道今夜伤了多少外村人。他只清清楚楚地记住了:从现在开始,小村里添了一个独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