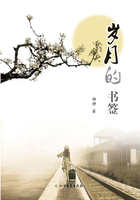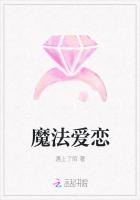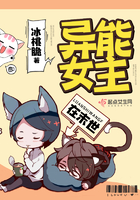《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70]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71]。
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72]。
《边城》原有《题记》,但多数时候不被重视;一些作品选本在选《边城》的时候也只有正文,不选《题记》。《新题记》收入全集前没发表过,却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73]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74]
《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75]。
《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76]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77]。《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
翠翠的故事很简单: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爱二老傩送,不爱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也驾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翠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刚开始,你不会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终发展到这么哀伤的地步。
作者一落笔写翠翠,就是美而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78]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文学里并不能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动人,却有些不同。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你就是把她称为“自然人”也无妨——作者甚至把她写成自然里的小动物。“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说,她从里到外,都得自于这青山绿水的自然,与之和谐一致。“教育”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说的是人从自然现象和人事经验中的学习所得,区别于我们通常说的从书本、学校、知识系统里接受文化的行为。他说“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染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从“文明社会”的“文化”观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她说成无知无识,心智未开:如若她见了人有“机心”,不是就要举步逃入深山么?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了。如果我们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在努力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却也未必就学得好吗?
我们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79]
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时,前面要加个限制,“单就情节来说”。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单薄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点事情”[80]。“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流经“边城”的河叫酉水,“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81]。
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做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这样的叙述特征,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都能见到。在这里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82]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亲的故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叙述者直接对着读者讲的,不经过小说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现在老船夫的意识和思想里,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现,这是老船夫以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时候,“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告诉翠翠大老托人来做媒,“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还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老人话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见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83]第四次、第五次是紧接着出现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84]。说到“共通的命运”这地步,对老船夫来说,不祥和悲哀的感觉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说起她母亲的事,但接下来只写了翠翠对祖父流泪的惊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对母亲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移开[85]。
叙述到这个地方,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了。一开始,它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接下来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而且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种种,凡是以前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做“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轻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其他声音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第十三章,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了,“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这时候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很觉得悲伤”,此时,“杜鹃又叫了”[86]。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贴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本章开始的部分,引述过沈从文关于《边城》的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老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
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87]。
“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88]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如果反过来,用小说的叙述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89]。“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她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90]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在命运的转折处写下了一些回顾人生经验的自白性文字,生前都没有发表。其中《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91]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生活中所受的屈辱,无从抵抗和报复,“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影响到以后。年纪稍长,在部队中只看到一片杀戮,“说现实,我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
《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却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当我们一开始讨论是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的时候,就没有把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闭在某一段时期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92]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题记》最后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93]
【附录】
《边城》题记[94]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我知道的。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至于文艺爱好者呢,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理论家有各国出版物中的文学理论可以参证,不愁无话可说;批评家有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边城》新题记[95]
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从文 卅七年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