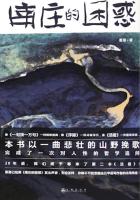“强子、强子,娃考上了,快来看呀!两个娃都考上了大学。”在村里担任调解主任多年的宁致和,一边跌跌撞撞地向还没出五服的本家侄儿宁文强家飞奔而来,一边大呼小叫地吆喝着。
花儿疙瘩村坐落在中条山余脉的脚下,土地贫瘠,是个只有八百口人的小村。以前,这里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如今,宁文强的一双儿女同时考上了大学,这在花儿疙瘩村,不亚于一场地震。
宁文强虽是个瘸子,但他的举动却矫捷得像只猫。他的皮肤微黑,脸上有一条手指头粗的疤痕,使那张本来还不算太丑的脸显得十分可怕。每当他一开口说话,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他的面部就要起一阵神经性的痉挛。假如没有这些缺陷,他人长得还算标致。他的儿子宁玉胜继承了他所有的优点,缺点却一点儿也没有,是宁家巷数一数二的帅小伙。
宁文强的妻子张桂花天生一美人胚子。她中等身材,柳眉修长,一双顾盼撩人的大眼睛一扑扇,微微上翘的长睫毛便跟着上下跳动,端庄秀气的鼻子下面,棱角分明的小嘴仿佛正在唱歌。她的女儿宁玉莲简直是她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宁玉莲的脸蛋像鸡蛋剥了两层皮又光滑又细腻,不涂胭脂自然红,比起母亲那苍白色的脸更多了妩媚。
宁致和走进宁文强家门时,他们一家四口正围着饭桌吃早饭。张桂花手捧宁致和递过来的那两张入学通知书,泪不由得往下流。她的梦想终于在一双儿女身上得以实现,她的心情要多激动有多激动,便不由自主地把那两张入学通知书贴在自己心口窝,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考上了、考上了,我娃终于考上了……”宁致和不解地望着她,一时不知所措。张桂花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赶忙止住哭,顺手拉了一个小板凳,递给宁致和:“小叔叔,你快坐。你看我,心里太高兴了,所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你见笑了。”
宁致和连忙鸡啄米似地点头:“我理解,我理解,咱花儿疙瘩村自古以来就没出过大学生,你家两个娃儿都考上了,他们为咱宁家,为咱整个宁家巷,为咱们村争了脸,是应该高兴的。”说着,重新拿起那两张入学通知书说:“考的不赖,玉胜考的是北京农业科技大学。玉莲虽说录的是一个专科,可娃上学迟一年,一边帮你们在地里干活又一边读书,能考个专科也实在不易。好着哩,实在好着哩。呃……”宁致和正想问一问两个娃都考上了大学,上学前该做些什么准备,一扭脸不见了宁文强。
此刻,宁文强正坐在自家的口粮田,那块叫东洼地的地头发愣。花儿疙瘩地处中条山的余脉脚下,那个叫涑水大峡谷的出口处,这里一年一场风,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日晚。该村属丘陵地带,全村两千多亩的土地全部分散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上。只有东洼这块地处大峡谷的背风处,一年能种点小麦、玉米。东洼地只有三百来亩,自古以来便是村里八百多口人赖以生存的粮仓。土地承包到户那一年,宁家弟兄三人总共分了四亩地。后来,分家另过,老大老三各一亩,父母把自己名下的一亩土地分给了宁文强,为此,大哥宁文华和他老婆胡玉环闹翻了天。谁能多得一点东洼地,就预示着谁家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宁文强瘸着一条腿,媳妇身子骨弱,做老人的自然凡事都想着他。大哥两口子吵归吵,在宁家还是父亲说了算,最终,东洼这两亩粮仓地还是归了宁文强耕种。宁文强宁肯人亏着也不让地亏着,他虽瘸着一条腿,但人十分勤快,每天天不亮便起床,掏茅粪、挖猪圈。自己家的掏完了、挖尽了,便去学校掏,去村委院子里掏。东洼这两亩地,硬叫宁文强伺弄得一亩地顶别人家两亩地的收成。他家不仅正月初一的饺子管饱,还能蒸一笼白面馒头,平时隔三岔五地还能吃顿干面。
山坡地没法丈量就按块分,宁家分了三十块,外加一条南沟。南沟,是涑水大峡谷的一个支谷,这沟更深,坡更陡,一年四季没人进去,纯粹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大哥因为分东洼地依然耿耿于怀,充满情绪地对父亲嚷:“你不是偏向老二吗,那就把坡上还有这条宝贝南沟给了他,我和老三只要坡下那两块地。”坡下的地距村近,地块相对大一些。宁文强不愿与大哥、三弟闹僵,赶快接过话头:“那就把坡下地给大哥和老三吧,坡上地我种。”父亲明白坡上地从没人耕种,一溜一溜的地块过不去一个耙,只好长叹一口气,转身离去。从此,坡上那块地洒下了宁文强无数的汗水。不过,这块地也没亏待了他,一年也可挖回几平车的红薯和土豆。宁文强用这些红薯和土豆,还有东洼地产的粮食,不仅把一家几口人的肚皮填饱,还能给一双儿女买回本和铅笔,供他们上学。如今,儿女双双考上了大学,花儿疙瘩村终于飞出了金凤凰。可宁文强望着那两张录取通知书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单两人的学杂费一年就得四五千块,这是坡上地和东洼地,三年收入的总和,即使一家人不吃不喝也拿不出这些钱供儿女上大学啊!宁文强不愿扫了妻儿的兴,独自一人坐在他视为生命的东洼地头发愣。他正想着,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原来是张桂花和宁致和。还没等宁文强开口说话,张桂花已经急切地说:“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怎么办?娃的通知书拿到了,咱得想法子让他们上学才行啊。”
宁文强低垂着脑袋,说话像蚊子在哼:“我有什么办法,咱家砸锅卖铁,也凑不出他们这些学费呀!”
宁致和接口道:“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咱得想辙呀!”
“想辙?该想的我都想了,我确实没辙。”宁文强脑袋插在两腿间,绝望地说着。
“我倒有个辙,不知你愿不愿干?”
宁文强忽地站起来,由于起得猛,他那条瘸腿有点站立不稳,身子左右摇晃了几下,抓住宁致和的手道:“小叔叔,有辙你快说!除非傻瓜和白痴才不愿干。”
“镇上扶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咱宁家巷我给你家报上了。”
“扶持?怎么个扶持法?他能不能给两个娃拿点学费?”
“学费的话我倒没和人家说。即使说了,人家给拿,能拿多少?要摆脱困境还得靠咱自个儿。”
“靠?怎么靠?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把地里的土变不成钱。”
“咱得想办法让它变啊。镇上决定,让咱花儿疙瘩村在东洼有地的户,明年都种薄膜棉瓜间作,镇上提供农膜种子、肥料,弄好了一亩地一年就收入好几千。”
宁文强重又垂下脑袋,瓮声瓮气地说:“那玩意儿咱没搞过,也不知行不行。”
宁致和口气强硬地说:“一辈子不嫁是闺女!金鸡岭村今年已有好几户种了。薄膜瓜确实上市早,瓜秧拔了还能长好棉花。今年一斤西瓜三毛钱,他们一亩地卖一千多,加上棉花,就是小两千块。两个娃学费有多少?你那二亩东洼地种好了,一年好几千,还愁娃学费没着落?”
宁文强依然高兴不起来:“唉……远水不解近渴。棉瓜间作即使能成,那也是明年的事儿。眼下,娃九月份要上学,这道坎儿就过不去。”
“咱长远和眼前结合啊。我让咱宁家巷子的人给你凑点,你再去县城找宁三,他是咱宁家巷子的能人,让他帮你想想辙。”
一听宁三,宁文强的眼前忽地一亮。宁三确实是个能人,这几年,土地承包到了户下,农民没了命的在土地上抓挠。红薯、土豆产量比在农业社时翻了好几倍。农民留足自己口粮,把这些东西交给宁三。宁三如同变戏法似的,总有办法让它变成钱,这是花儿疙瘩村民一笔不菲的收入。宁文强一拍大腿:“好,真是太好了,我明天就进县城找宁三。”
花儿疙瘩村距县城四十多里,宁文强走过那七拐八弯,坑洼不平的只能过一辆平车的土路,才来到了通往县城的水泥路上。宁文强活了四十多年,这还是第三次走这条通往县城的路。上两次,是因为父母生病住院,村里人用门板抬着奄奄一息的双亲。如今,他是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上两次,他是跟在门板后面,悲痛欲绝地往前走。如今,他虽然仍被缺钱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心底里还是乐呵呵的:谁家的娃儿有他家娃儿有出息,两个一下子都考上了大学。大学那是什么地方?是出秀才、举人的地方,用如今的话说叫出干部的地方。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家终于可以走出当干部的了!宁文强一边走一边哧哧哧地笑出了声。
宁文强从没来过县城人们居住的地方。一幢幢、一排排的房子都是青砖兰瓦,几乎一个模样。这样的住宅,宁文强只是在金鸡岭那个叫木根的财主家见过。他一边走一边问,终于来到了一个叫东关的地方。宁致和告诉他,宁三住在东关西巷三号。他边走,边盯着院门口的牌子看下去,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宁三的住处了。他使劲用手拍着铁门上的门环,嘴里叫着:“喂,宁三、宁三,开门!开门啊!”工夫不大,只听院内有人接上了腔:“谁呀?”
“是我,你文强二叔。”
院门拉开了,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小媳妇,她张口问:“你是谁?宁三走没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
“他去省城发展了,把房子租给了我。”
“发展了?发展什么了?”
“发展就是赚大钱去了。”
“哦……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既是发展去了,又把房子租给了我,我想他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的。”
“那……”宁文强十分失望地转过身。来的路上,他还在一遍一遍地琢磨,今年的红薯、土豆长得不错,除过留足口粮,应该还有五平车的余头。如果把这五平车的红薯、土豆换成粉条,粉条再去周围几个村换成粮食,粮食卖了就可以拿到小千数块,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学杂费。可如今,宁三走了,红薯、土豆换粉条的路也没了。怎么办?怎么办?单纯卖红薯、土豆可卖不了几个钱。宁文强低下脑袋,一边琢磨一边往前走。正走着,抬头一看,已来到了县医院门口,听到一伙人正围在一块儿说卖血的事。原来,一位患者大出血,急需输血却找不到血源,家属急得在医院门口大声喊叫:愿意献血者,他将付双倍的费用。宁文强看见已经有好几个人报名输血,在那里等着验血型。他见有了来钱的门路,自然不肯放过。于是,也报了名,等着抽血验血型。宁文强拿眼扫了一下,他断定这伙报名的人都是农民,可能他们和他一样,想筹足钱给儿女交钱上大学或是成家,或是给老人换几个医疗费。
宁文强很幸运,血型对应,被抽了血,并很快接过了两张崭新的钞票。他算了一下,这么不痛不痒,只在胳膊上抽了那么一管血,就顶自己撅起屁股劳作几个月的收入。他一边用一个指头按着胳膊上那片白色的小胶布,防止针眼出血,一边问:“嗨,以后还要不要血?”护士不敢抬头看宁文强那奇丑无比的嘴脸,一边收拾装针管的小盒子,一边回答:“要,这里差不多天天都有手术,血源缺得很呢。”
回家的路上,宁文强兴奋无比,他终于找到了一条为儿女筹集学费的路子。他在心里默默计算着,卖十次血,就可以筹一个娃一年的学杂费了。他陡然想起了那个白脸皮中年汉子在县医院门口一脸焦急,向众人乞求似的叫喊声:“诸位父老乡亲,请伸出友爱之手,愿为我爸献血者,我将付相当于医院血价双倍的钱。父老乡亲行行好!救我爸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宁文强深深为那个白脸皮中年汉子的行为感动。若不是两个娃儿上学要花钱,他才不要那双倍的血钱,甚至医院血价的钱也不要。不就是一点血嘛,这就像河里的水,你从这里舀一桶,那里的水就会立刻把这个空空补上。只抽那么一管血,回家喝碗盐水,再来两碗酸菜调齐子(齐子为地方方言,指面条),血管里的血照样满满的。
回到家,宁文强照吃照喝,没把他卖血的事告诉张桂花和两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除过爸妈,张桂花和两个娃儿就是他最亲的亲人。张桂花花朵般的一个美人儿,嫁给了他这个丑八怪,图的什么?为的什么?是男人就得担当起对妻儿的责任,更何况他这个奇丑无比的丈夫,他不能让妻儿对他有一星半点的担忧。第二天,他早早起了床,照例到厨房做好了饭,对还在被子窝儿里钻着的三人喊了一声:“嗨,饭在锅里哪,起来热热吃。记着,得热得热热的再吃,温咕咚饭吃了对胃不好。”张桂花惯例地应了一声,宁文强这才走出门去。
宁文强又来到县医院。这天的运气不好,虽然仍有人做手术,但需血量少,医院血库里又有了血。几个等着输血的农民东张西望,不见医院护士出来找人输血。他们等啊等,眼看医院快到了中午下班时间,仍没人出来找人输血。几个人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先后一个个离去,最后,剩下了宁文强一个人。他又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出来,便失望地叹口气,正准备离去,陡然看见从住院部出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正是那天抽他血的护士。宁文强立刻凑上前去,口气柔柔地叫:“护士同志。”
护士一回头,尽管不是第一次见他,但还是被他的容貌吓得退后几步,怯怯地问:“你要干什么?”
宁文强知道自己的样子吓着了她,连忙歉意地说:“你别怕,我虽丑,但不是坏人。昨天我在这里卖过一次血,今天还想卖,我整整等了一上午,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叫人输血?今天没手术?”
护士面无表情,不冷不热地问了句:“怎么,你输血还输上了瘾?”
宁文强苦笑了一下:“这又不是吸烟喝酒,怎么会上瘾呢?实话告诉你,我的两个娃儿今年都考上了大学,我想卖点血给他们凑学费钱。”
听后,护士重又抬起头来打量了他一番,并立刻从情绪储备库里调来了笑容,甜甜地说,:“大叔,您教育得真好,两个娃居然都考上了大学。您为他们凑学费的爱心可以理解。但是,您又不是专业卖血人员,可要保老本啊,血抽多了,对您身体不好。”
护士甜美唱歌般的声音鼓舞了宁文强,他拍了拍胸脯,说道:“没事,我身子壮得像头牛,抽上个三管两管的,不碍事的。娃很快就要上学呀,交不起学杂费可怎么整?”
护士似乎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说道:“我们医院最近手术很多,而血库里的血只能用三天,一般都是在当地买。你是O型血,用得比较多,如果真愿意输的话,明天后天都有两个大手术,需血量多一点。况且,病人家属一般还是愿意买不是专业卖血人员的血。”宁文强正想问专业卖血和不专业卖血有什么分别,护士已扭转身走了。
第二天,宁文强早早便来到了县医院那天抽过血的门口等候,不多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宁文强卖血那天见过这个人,本来觉得他不该来,或者不该早来。如果他不来,或者是迟来一会儿,那护士就能多抽自己一管血,孩子的学费就能多凑一点。他来了,病人对血的需求量就得二一添作五的分。转眼一想,也许那人和自己一样,也是在为孩子凑学费。想到这里,与他相视一笑,那人居然也笑了笑,没有了第一次那种恐惧甚至厌恶躲闪的表情。
宁文强又抽了和第一天一样多的血,但钱却比那天少。宁文强问那个抽血的护士,护士说:“这是正常价格,那天是病人家属愿意多出。”宁文强不作声了,拿着钱认真数了数,自嘲地说:“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按正常价格算也比种地强多了。”他正嘟嘟囔囔朝外走,一同卖血的那个人也从医院走了出来。宁文强朝他笑了笑,搭讪道:“老哥来干这个也是为娃凑学费。”
那人回答说:“不,老娘得了胃癌,在医院做手术。你是为孩子凑学费?”
宁文强点了点头,又随口问了句:“明天还有个大手术,你还来不?”
那人也朝宁文强友善地笑笑:“来,不来怎么办呢?老娘在病床上躺着,你还来不?”
宁文强一边连声回答:“来来来。”一边一瘸一拐地和他走出医院大门,各奔东西。
宁文强又抽了一次血,这天,他从县医院出来,陡然觉得头有点晕,腿有些发飘,有点像腾云驾雾的感觉,肚里也觉得空落落的。他在心里说,今天早晨明明吃了两个大馒头,还有一大海碗拌汤,怎么肚里有了掏吃虫,这会儿又饿了呢?路过一家羊汤馆,羊汤的香味儿使他不住地吸溜鼻子,摸了摸口袋里刚刚拿到手的钱:不行、不行,一个娃的学费都没凑够呢,想喝什么羊汤,那种地儿是你能去的吗?他坚定地摇了摇头,一回头,看见村子里唯一的一辆四轮车过来了,便招了招手,搭四轮车回家。
回到家,宁文强觉得好累好乏,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想动,他问儿子:“玉胜,你妈和你姐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
“干吗去了?”
“不知道。”
宁文强想站起来进厨房做饭,可试着站了几次,都觉得头晕力乏站不起来,便理亏似地说:“玉胜,你过来扶一下爸,我得进厨房做饭了。”
宁玉胜走过来,伸手去扶宁文强的胳膊,看了眼他的头,惊叫道:“爸,我那天回来,你头发还黑黑的,怎么这才不到一个月,你头上就这么多白头发?”
宁文强听说书先生说过,谁谁谁遇到了难事,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这段时间他心里确实为两个娃儿的学费急得心焦火燎,“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发”,他只是觉得那是说书先生夸张的说法。如今自己真得急白了头发吗?他想验证一下,便故作轻淡地说:“爸老了,有白头发在所难免。玉胜,你拽一根爸看看。”宁玉胜从他头上拽下了一根白头发,递到他面前。这才发现他面容憔悴,眼睛深陷,嘴唇青紫,不由惊呼:“爸,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宁文强不愿让儿子知道自己卖血的事,便连忙敷衍道:“没事,爸今天走路太多,有点累,歇歇就好。胜,我口渴,你给爸倒一碗盐开水来。”
宁文强喝下去一大碗盐开水,确实感觉好多了。吃过饭,姐弟俩又出去了,宁文强便掀开褥子,从底下取出一大把钱来,一张一张数起来,数来数去,把家里所有的钱加起来,还不足一千元,距两个娃的学杂费还差了一大截,这么多的钱从哪里弄去?
第二天,宁文强又跑到医院,想再卖点血。还是那天抽他血的护士,断然拒绝:“大叔,你真的为给孩子筹学费连命都不要了?”
“我这还不是没办法的办法么!”
“没办法也不能用命拼,我跟你说,你的身体已不能再抽血,你回去再别来了。”
“一次,就这一次了。护士同志,我求求你了。”
“一次也不行,我担不起这责任。”说完,护士收拾器具出去了,宁文强不得已也只好跟着出来。
回家的路上,宁文强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来钱的门路,陡然,他想到了猪圈的猪。这两口猪是他家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喂大的。平时,他们去地里干活,回家总不忘给猪捎一捆草。这几年雨水好,地里的灰条、人汗个个长得肥肥胖胖。灰条、人汗是一种野生菜,用开水一煮,捣点蒜,放点熟油辣子,再撒上一点芝麻盐儿,一人一顿能吃一碗。这么好的东西人都喜欢吃,猪自然更爱吃了。自从土地承包到户,老百姓粮食不缺了,但也舍不得用精粮去喂猪,猪吃的只能是些野菜、泔水、磨面剩的麸皮等东西。这猪好吃手,不管你扔什么东西,它都低着脑袋,“呱嗒呱嗒”一个劲儿地把肚皮吃得鼓鼓的,吃饱了,就躺在圈内向阳处晒太阳。那只浑身毛雪白,脸短嘴翘,宁文强叫它“老白”,另一只杂毛,脸长嘴秃,眼圈有两道黑,宁文强叫它“花脸”。这会儿,宁文强把一荆条筐红薯倒进了猪圈,老白和花脸就抢着吃,老白一嘴叼两三个,脸一仰吞进了肚里。宁文强拍了拍老白屁股:“嗨,老白,慢慢吃。”老白似通人性地摇了摇尾巴。宁文强一边用手抚摸它,一边用指头丈量老白的身长和身高,计算着它的体重,随即用手拍着它脑袋说:“老白啊,一年了,也没叫你吃上什么好吃食。今天你该出槽为小主人做点贡献了,红薯就尽着你吃。”一荆条筐红薯很快吃完了,宁文强又把另一筐倒上。两筐红薯不大一会儿工夫,被老白和花脸吃了个精光,肚子也撑得滚圆。
这时,宁玉胜叫的几个帮忙的年轻人也来了。小江、小河手利索,跳进猪圈,一人拽一条腿,把老白从猪圈墙上提溜了出来。“老白”哪受过这种待遇,就扯着嗓门嘶叫、挣扎,脚蹬腿刨。不管老白怎样反抗,它和“花脸”还是被几个壮汉五花大绑硬硬按上了平车。
宁玉胜拉着平车,撒开脚丫子跑,宁文强撵不上,只好远远跟着。花儿疙瘩村到向阳镇食品站十里路,宁玉胜一口气就到了。进了向阳镇,他按父亲的吩咐,准备到合作社买盒烟,送给验猪等级的检验员。宁玉胜放下平车,正准备进合作社的门,无意间回头一看,吓得他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原来,平车上的“老白”和“花脸”口吐鲜血已经死亡。怎么回事?刚才还在猪圈活蹦乱跳的猪,这才多大一会儿,怎么就能死了呢?宁玉胜脑子一片空白,浑身仿佛被人抽了筋,“老白”和“花脸”是他家的半份家当,是他和姐姐上大学的希望,如今说没就没了。宁玉胜泪似泉涌,他有种天塌下来,世界末日的感觉。
不大一会儿,宁文强赶到了,一看到平车上的“老白”和“花脸”,他也傻了似的,只知道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宁文强仿佛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宁玉胜说:“儿子,事已至此,咱俩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得想个法子,把“老白”和“花脸”处理了才是正事。”
宁玉胜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怎么处理?食品站会要两头死猪?”
“和他搞搞价,大不了咱少要点钱,快走!猪已经死了,得赶快送去让他们放放血。”
父子二人拉着猪进了向阳镇的食品站,今天卖猪的人多,拉着猪的平车排了一长溜。大家见他们拉来了两头死猪,纷纷凑上来看稀奇。这个拍拍“老白”胀得像鼓一样的肚子,“啧啧啧”几声,惋惜地说:“唉,吃得不瘦,可惜了。”那个朝平车上扫一眼,不屑地说:“两头死猪,来凑什么热闹。”
秋天的苍蝇本来就缠人,食品站血腥味浓,已招来不少的绿头花蝇。“老白”与“花脸”嘴里流出来的血,更是把这些苍蝇成群结队地招来了,赶也赶不走。宁文强急了,央求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兄弟,你看,能不能让我们挤在前面,这不是……”来卖猪的个个都被这里刺鼻的气味熏得直想呕吐,被成群苍蝇袭击得忍无可忍,谁也想尽快把猪交了,快快离开这里。对宁文强的央求理也不理,父子俩虽心急如焚,但还是耐着性子排队等着。
好容易轮到了他们,验猪的是个满脸络腮胡的粗大汉,他来到宁文强拉猪的平车前。宁文强将手伸进口袋懊悔不已,刚才只顾着生气了,连盒烟都没买。此时,只好把笑容全调到了脸上,低声下气地叫了声:“大哥,你看……”话没说完,他已在心里后悔得骂娘,验猪的虽满脸络腮胡,但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自己怎么能称他大哥哩。络腮胡拍了拍“老白”的肚皮,问:“送来之前,你让它吃了多少红薯?”宁文强眨巴眨巴双眼,怯怯地问:“你怎么知道?”
络腮胡从喉咙深处哼了一声,鄙夷地说:“你们那点鬼把戏,能瞒得过谁去?卖之前喂猪生红薯,猪吃了不屙不尿,能多挂点分量。可猪吃得太多,你们一捆,它一挣扎,吃进去的红薯把肠子撑断了,猪还有不死的?”
络腮胡的话说得宁文强鸭子嘴里顶柴,半天接不上腔儿,只好觍着脸一个劲地说好话:“大兄弟,嗨,大侄子!哎呀,我都不知道称呼你什么好了。你看,都是老百姓,养猪不容易,你就……”
络腮胡不等他说完,把手一挥:“快拉走,食品站不收死猪。”
父子二人不住地央求:“大哥、同志,你就行行好,价钱便宜点,这不是……”
络腮胡毫不通融,一边走一边说:“不要钱我们也不要。死猪肉红咯咧咧的,卖给谁去?想占小便宜,偏偏吃大亏,活该!”
父子二人仍跟在络腮胡屁股后面乞求。络腮胡火了,扭回头把他们连推带拽,推出了食品站的大门。
宁文强拍着“老白”的头一边哭一边说:“老白啊老白,我们待你不薄,你怎么能给我来这一手?”给“老白”和“花脸”挖那两荆条筐红薯,足足挖了一畦子,这畦红薯如果长到霜降挖,至少可以挖一平车。如今把正长的红薯糟蹋了不说,还把两口猪搭了上去,这是一年的心血啊!宁文强越想越后悔,越后悔越觉得窝囊,回到家连饭也没吃,蒙头便睡。宁文强一直睡了一天一夜,嘴里咕哝着:“哎,人倒霉时烧开水也糊锅。”他爬起来决定出去跑跑,再找个进钱门路。
这时,宁玉胜背着一个口袋从外面回来了,他看爸仅一天时间人憔悴得仿佛老了十几岁,便安慰道:“爸,想开点,人的一生难免有走背字的时候,猪赔了,我们再从别的地方赚回来。”
“赚?从什么地方赚?”
宁玉胜指着自己刚从外面背回来的口袋说:“我一个同学的亲戚在镇上收购药材,我捋了一把连翘问他要不要,他说要,有多少要多少。爸,咱们大峡谷里到处都是连翘,你看,我一小会的工夫弄回来一口袋。”
“真?”宁文强一下子跳起来,他满脸放光,连声叫嚷:“这下,你们的学费有指望了。咱明天全家总动员,都到大峡谷捋连翘去。”
“峡谷里连翘是不少,可全都长在那石尖上,你腿不方便,我妈和我姐也干不了这活,要去,还是我去。”
“他们干不了我去,不就是捋点连翘么,早点把学费凑齐,早点静。”
宁文强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好过,连翘为他展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致富路。他不仅今年可以靠它为儿子、女儿筹足学费。明年、后年直到娃娃们毕业,他都可以靠它来钱了。宁文强兴致勃勃,想到高兴处,他不由哼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