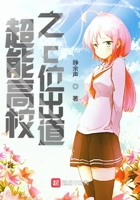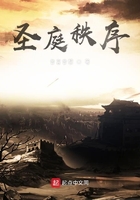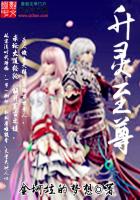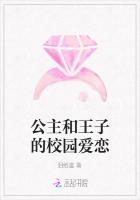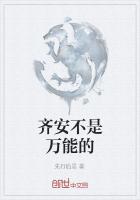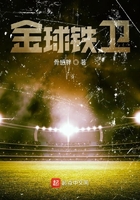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的唐诗学研究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学术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顾这段唐诗学研究的历史,对深化21世纪的唐诗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章对此略作述论。
一、新时期对唐诗学建设的倡导及理论性探讨
唐诗研究历来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重头戏。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唐代文学研究的蓬勃开展,1983年,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唐诗讨论会。会上,傅璇琮先生首次向学界提出了创立“唐诗学”学科的建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人士的响应。1984年,傅璇琮在《年鉴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一文中又谈及这一问题。他说:“唐代文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条件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一门学科之可以建立学术史,是成熟的标志,而它的建立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唐代文学的研究是一门科学,我们应当对它的历史加以探讨,作出总结。”(萧涤非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在这篇文章中,傅璇琮从年鉴编写与学术史研究紧密相连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的构想。他把开展唐诗学史的研究看成了拓展唐诗研究的有效途径及深化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1986年,陈伯海先生在《小议唐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一文中,紧承傅璇琮先生之论,对新时期唐诗学研究进一步予以了倡导和规划。他在肯定“唐诗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上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的同时,指出:“美中不足的是,这门学科在理论建设上还比较薄弱,缺少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陈伯海在简要回顾了历代唐诗研究家的唐诗研究特点之后说:“所以,迄今为止,尽管唐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唐诗学的理论体系似尚处在分娩之中。”为此,他提出“要多多欢迎‘一家之言’”,认为“目前唐诗研究领域(尤其是理论研究),不是个人意见太多,而是独到的议论太少,思想不活跃,引不起郑重的关注和深入的研讨。针对这种情况,应该特别鼓励理论上的创新,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作为‘一说’参加争鸣。甚至可以设想,将来发展出几种对立的唐诗学体系,在相互竞赛中取长补短,长期共存”。(霍松林、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陈伯海此文从提升唐诗研究的高度,提出了建构唐诗学理论体系的主张。这标示出他真正把唐诗学作为了学科建设加以探讨,极具理论标识意义。之后,他在不少文章中都积极倡导推进唐诗学学科建设,为新时期唐诗学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1991年,陈伯海在《积累资料·提高鉴赏·概括理论——多元立体构建唐诗学》这篇小文中,又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强调:“与史料整理与鉴赏活动相比,理论概括是当前唐诗学建设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迄今为止,还缺少材料翔实、体系完备的《唐诗史》、《唐诗学》专著。期望于未来十年间能突破以往偏重作家评论的单一研究模式(作家研究自然也是需要的),努力从多种视角把握这门学科的内涵。”(《社会科学报》,1991年5月30号第4版)执著地提倡从理论概括的角度研讨唐诗学,表现出希冀学界对唐诗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抽绎和概括的殷殷期望。2000年,陈伯海在为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所作序中,又对“唐诗学”之可以为学予以了阐说。他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历史两方面展开论证,其中谈到:“在我看来,‘唐诗学’的名称是可以成立的,根据首先在于它的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唐诗。这不仅仅指唐人的诗作的总和这样一个时间和数量上的集合,更其重要的,是指构成民族文学精华乃至文化精神典型的一代诗风所特具的那种整体审美质性(如‘风骨与声律兼备’,‘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等),以及由此质性而产生的独特的审美理想和诗学传统。”“正是唐诗的审美特质规定了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为唐诗学的建立和推进设置了前程和方向。”(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明确从唐诗学学科如何得以确立的角度予以阐说,并论析对唐诗质性进行理论抽绎和概括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出对唐诗学建设的高屋建瓴的识断。
在对唐诗学建设倡导的同时,研究者们对唐诗学的研究展开了理论探讨。1987年,吴企明在《唐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一文中较早对唐诗学的研究予以了理论性阐说。他认为:“唐诗学是以整个唐诗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它包含、覆盖各个方面的唐诗研究工作,古今中外学者们从事的唐诗研究,都在唐诗学这种学科考察范围内。研究唐诗学,就是对我国从古到今的唐诗研究,进行回顾、反思、总结,以此来指导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研究工作。总揽古今,研究过去,观照现在和未来,这便是唐诗学研究的任务。”吴文把唐诗学研究总体上规划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提出:“纵向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唐诗学递变的轨迹,是唐诗学学科体系的主干部分。”“从横向研究的角度看,考察唐诗研究的各个侧面和环节,研究各个侧面和环节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唐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导报》,1987年第2期,第31—32页)该文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篇对唐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予以理论性阐说的专文。之后,黄震云、蒋成德《唐诗学和二十一世纪》、黄炳辉《唐诗学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朱易安《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等文章都对唐诗学研究予以了理论性探讨。黄炳辉《唐诗学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一文,从“唐诗学之史学性质”、“唐诗学之诗学性质”及“唐诗学走向”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唐诗学研究对象和范围进一步予以了考察。他把唐诗学研究的内容,在横向展开上归入到我国古典诗学的“十大范畴”,即创作论、灵感论、风格论、诗体论、语言论、声律说、意境说、情志说、性灵说、格调说之中。(《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1—7页)黄文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对唐诗学的内容作更为清晰的展开和阐说。朱易安《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一文,则对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当我们研究唐诗学发展史时,不仅要理清唐诗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应该揭示出唐诗学史得以建构的条件及其原因,解释唐诗学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历史面貌而不是其他状态。”该文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唐诗学的形成及其意义、唐诗学的研究体系和建构、唐诗学与社会文化背景、唐诗学与诗学方法五个方面展开了探讨,对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予以总纲式的把握,清晰地阐述出了“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同时阐述上述那些非诗学因素与诗学发展的有机联系,并把它们看成是唐诗学史体系建构的一部分”的论断。(《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第30页)
对唐诗质性的抽绎及其理论的探讨集中体现在陈伯海先生的研究中。1988年,陈伯海出版了《唐诗学引论》一书,该书从“正本”、“清源”、“别流”、“辨体”等角度,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等作出了翔实的考察。其中,在“正本篇”中,作者从唐诗中拈出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进行详细辨析,将它们抽绎、界定为唐诗的特质。陈伯海认为:“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这就是构成唐诗内在质素的几个基本的方面。这些要素汇集、组合在一起,呈现为唐诗的整体风貌,便叫做气象。”但“气象并非与上述诸要素并列的另一种质素,它是各要素的总和,是唐诗的质的定性的外部表征”。(《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33页)此书围绕唐诗的总体观,展开了对唐诗的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交替变换的具体演进过程等的研究,为提升、阐说唐诗学作为学科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该书在阐说上极具体系性,成为新时期唐诗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力作。
二、新时期以来的古典唐诗学史研究
1.对古典唐诗学研究的通观性考察及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唐诗观的研究
对历代唐诗研究的通观性考察是新时期以来唐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成果主要有:齐治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葛晓音《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陈伯海《唐诗学史一瞥》,黄炳辉《唐宋评判唐诗说略》,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纵向地梳理唐诗研究的历史,包括断代研究史和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历史,努力勾画古典唐诗学研究的轮廓。齐治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一文,抓住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由分唐界宋所形成的长期争论这一核心问题,对历时八百年之久的唐宋诗之争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为新时期对唐诗学史的撰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4期)葛晓音《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一文,对“天分”与“学力”这一对概念的形成及其与唐诗研究愈益深入过程的关系展开了考察,为人们了解历代诗论中的宗唐、宗宋之争和宗唐派中的初盛与中晚之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点。(《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第102—108页)陈伯海《唐诗学史一瞥》一文,则立足于翔实的材料和通观的把握,首次对唐诗研究的历史及其分期予以了勾画。他将唐诗研究的历史区划为五个时期,即唐五代——唐诗学的酝酿期;宋金元——唐诗学的成长期;明代——唐诗学的发展期;清及民初——唐诗学的总结期;“五四”以后——唐诗学的创新期。(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页)他的勾画为新时期唐诗学史的研究拉出了清晰的发展演变线索,对新时期唐诗学的研究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
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唐诗观的研究是勾画唐诗学研究史的重要链节,它成为历代唐诗研究有效开展及理论抽绎的基础。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流变》,詹杭伦《方回在唐诗分期上的贡献》,朱易安《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与发展》、《后七子和明末文人的唐诗观》,陈新璋《欧阳修唐诗观及其影响》、《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王琳《论金圣叹的唐诗观》,胡光波《金批唐诗论》,刘海燕《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查清华《明代“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抓住具体历史人物的唐诗观进行考察,以其为关节点透视同时期或前后相承时期的唐诗观念;或考察某个具体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对唐诗的论评及其观念,呈现出由点到面、由点到线或线面交合的研究特征。如:陈新璋《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影响》一文,作者对欧阳修的唐诗观展开详细辨析,认为欧阳修推崇韩愈及中晚唐诗的用意在于抵制西昆习尚,开创一代诗风。他推崇李杜,但并无扬李抑杜之说,后人以为欧阳修将李杜分出优劣,这是不符合欧阳修本意的。欧阳修的唐诗观并不全面和系统,但对北宋诗学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1—66页)陈文由点辐射到面和线,为人们理解北宋前中期的唐诗研究作出了切实的辨识。查清华《明代“唐人七律第一”之争》一文,则抓住由“唐人七律第一”引发的论争,透视出明人诗学观念的时代变迁及其唐诗学的演变与发展。认为,明代“唐人七律第一”之争,体现了诗歌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突出地表现在评判标准以艺术而不是以政教为中心,且坐实于“体格声调”之论当中,由对体格声调的合理接受和娴熟把握,进而领会深层的兴象风神。论争生动地体现出明代格调派审美接受理论渐趋深化、渐趋精微的发展轨迹,也暴露了中国诗学领域一个传统的困惑,那就是“兴趣”和“工力”在走向艺术终极目标时难以协调的矛盾。(《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第78—87页)此文持之有据,论述精切,是新时期唐诗学史研究中的一个优秀成果。
2.历代唐诗选本研究
唐诗选本是人们接触和研习唐诗的一种最切近的方式。对唐诗选本的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唐诗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内容。这方面成果相对较为突出。如:沈家庄《读船山〈唐诗评选〉:蠡测王船山唐诗研究的特征》,孙繁璋《试论唐人选唐诗〈极玄集〉》,宫晓卫《王渔洋选唐诗与其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的诗歌崇尚》,朱易安《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黄炳辉《〈唐诗评选〉评唐诗辨》、《高棅〈唐诗品汇〉述评》,陈国球《简论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说》,俞兆鹏《谢枋得的爱国思想和他的〈注解选唐诗〉》,周兴陆《〈唐诗品汇〉为何列杜甫为“大家”?》,王振汉、范海玉《唐汝询及其〈唐诗解〉》,孙鸿亮、李宏金《从“唐人自选诗”看唐诗审美观念之嬗变》,徐安琪《〈唐诗三百首〉的审美价值取向》,詹福瑞《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的宗唐倾向及选诗标准》,郭勉愈《〈唐文粹〉“铨择”〈文苑英华〉说辨析》,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对单个唐诗选本进行细致考察,由点辐射到线和面;或将唐诗选本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审美观念联系阐说,映证生发;或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唐诗选本比照辨析,呈现出多样的研究路径,为我们更细致而切实地把握唐诗学发展史提供了参考。如:朱易安《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一文,通过考察明代三种唐诗选本的编纂和流传,顺次展示出明人唐诗观念演变的过程及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异。该文循选本而入,揭示出了明人崇尚唐诗的文化心态,以及形成这种心态的文化机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77—84页)朱文以点串线,由点而将考察范围横向扩展,将对明代唐诗学史的把握拓展了开来。陈国球《简论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说》也专就明代盛行的几个唐诗选本——《唐音》、《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古今诗删》的唐诗部分进行考察,由选本的兴替揭示唐诗在明代受承纳的情况,以及其与复古诗论的相关链接,得出了甚富启发性的结论。如言:“其中《唐诗正声》和《古今诗删》的举拔精纯之作以为唐诗的表征的做法,配合了复古诗论追求正宗、正统的理想;《唐诗品汇》则大力推动了复古诗论家的文学史意识;而《唐音》则对这两个方向又有启迪之功。”(《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第120页)该文将明人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说的关系阐述得甚为清晰。
3.对唐人唐诗的接受研究
对唐人唐诗的接受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唐诗学史研究开展的又一维视野。研究者们往往对唐诗史上具有典范性,或具有转捩意义,或广有争议的诗人诗作,围绕其文学地位的起伏,读者接受侧重点的不同,历代诗论家对其的各异阐释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这方面研究虽比较零碎,与历代唐诗研究的联系也显得稍见间接,但对夯实唐诗学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方面成果也不少,其中,诗人接受研究如:棘园《东坡论杜述评》,朱易安《明人李杜比较研究浅说》,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明代诗学批评中的李贺论》,聂巧平《宋代杜诗学论》,等等;诗作接受研究如: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吴祁仁《从唐代的〈金陵五题〉到清代的〈金陵怀古〉——对宋代“融化”“隐括”及其影响的思考》,陈文忠《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高洪奎、刘加夫《李贺歌诗的接受史研究——中唐至五代》,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出如下几方面研究取向:(1)通观性地考察单个唐人唐诗作品在后世的批评接受;(2)截取断代考察其对唐人唐诗的接受;(3)择取单个历史人物对唐人唐诗的接受进行考察。如: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通过选择唐诗中经典名篇《春江花月夜》的接受作为考察对象,向人们展示出了文学接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极为复杂的情形与错综变化的时代特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第18—25页)该文成为唐诗个案接受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对新时期诗人诗作接受研究的开展甚具启发性。又如,拙文《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通过考察诗学批评中杜甫论的繁复的历史轨迹,揭橥出古典诗学批评中杜甫论不断趋向辩证、深入的特征。文章认为,杜诗在唐代不为世人所普遍赏重,激赏者寥寥,但其论评却能切中杜诗骨髓神味;宋代,杜甫及其诗作受到普遍推重,然随之出现穿凿和拔高的倾向;元明两代,人们普遍尊唐而不宗杜,不少人受格调论影响极力区划唐音与杜格,出现对杜甫的批评之声;清代,人们从总结诗学理论的高度进一步审视杜甫,杜甫人格形象与诗作价值得到辩证深入的剖析。(《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68—73页)努力在历时视野中对唐人个案接受进行通观性的观照,成为该文的显著特色。
三、新时期以来唐诗学研究的著作成就及唐诗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唐诗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唐诗学理论的建构上,出现了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这一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在唐诗学史的撰著上,则出现了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年),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两部著作,虽在唐诗学史的研究上,更多侧重于以点串线,显示出对唐诗学发展史叙述不够充分的特征,但它们为唐诗学史的更系统、更深入地撰著打下了基础。之后,又有傅明善《宋代唐诗学》(研究出版社,2001年)的出版,这标示出唐诗学史的撰著已推进到断代研究的阶段。还出现了专题及分支形态的唐诗学史研究著作,如: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简恩定《清初杜诗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此外,还有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等。这些著作,为唐诗学研究的更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新时期以来的唐诗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唐诗学史的撰著上,或偏重于专题,或局囿于断代,个中一些材料和论述也尚嫌缺略不齐。这当然一方面表现出学科开创初期研究著作所具有的普遍形态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离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又是有距离的。因此,作为对唐诗学史的通观、细致的把握,仍有待进一步开拓。值得提及的是,正缘于此,陈伯海先生现正主持编写一部较为系统的《唐诗学史》著作,拟作篇幅近60万字,该书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望于2004年与读者见面。二是对唐诗学的理论探讨还显得甚为单薄,人们对唐诗的研究还大多停留于考证性、赏析性及阐释性研究,对唐诗美学质性的抽绎研究还见欠缺,对唐诗作为独特诗歌范型的本体性研究也还不够。陈伯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期望出现的几种不同的唐诗学研究体系并未出现。三是唐诗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拓展。选、编、注、考、点、评、论、作,这之中,每一种形式都有关于唐诗的学问包含其中。新世纪的唐诗学研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更为深邃的理性辨识,在宏通的视域中进一步拓展其研究层面,开掘其研究对象,从而,将唐诗学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