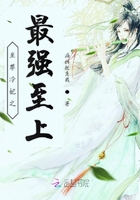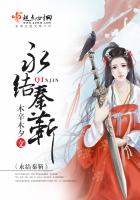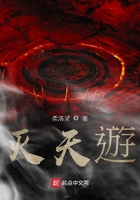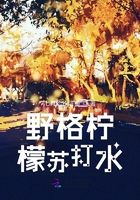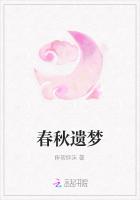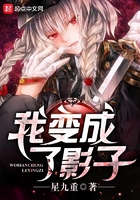一、中国近代文学时限的界定
通常认为,中国的近代文学,与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同步进行的。但史学界在近代史起始时间上的认识并不一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注重对历史事件本末的记述,对近代史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注重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将近代史的上限定为1840年,以鸦片战争作为开始的标志,而对下限则无确切的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进行了大讨论,虽然在具体的时期划分上存在着分歧,但一般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结束;而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将1840年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但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
近代文学与政治联系紧密,文学风貌的变化也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1922年,胡适应申报馆之约,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年特设的纪念专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了著名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上限定为1872年,这一年“桐城派古文中兴第一大将”曾国藩去世,也就标志着“古文运动又渐渐衰微下去”[1]。胡适以一个新文学家和新文学史家的立场,梳理自1872年至1922年这一段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这五十年的文学呈现出三种新趋势:一、作为“死文学”和“半死文学”的古文学逐渐地死亡;二、作为“活文学”的白话小说逐渐地成为“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三、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中,虽然胡适没有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对这五十年的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观照。他已经意识到这五十年来的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差异,把这五十年以来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主观臆断地把“五四”作为两种文学的分界线。陈子展不满于胡适对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时代划分,在以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首次提出了“中国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近代文学的起点是戊戌变法,也就是1898年,他的依据是:“这个运动虽遭守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故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一点近代的觉悟。所以我讲中国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2]而在仅一年后发表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却又提到新文学“起自甲午”。他认为,虽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但只有表面形式的变化,而实质精神没有变,直到甲午战争,生死攸关,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社会的生活之剧变而生剧变,将至转而成为显示将来的新时代新社会的一种标识”[3]。虽然陈子展在对近代文学的上限的时间划分上前后有异,但他首次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名称。1930年,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把近代文学的范围扩大至明洪武年间,并指出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发酵,近代文学是历代文学的积淀,意识到近代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与今天的近代文学的概念大有不同。钱基博所谓的“现代文学”与现在的近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大部分重合。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根本方向是相同的”[4]。将新文学的源起追溯到明末的公安派。郑振铎在同年5月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第五十六章《近代文学鸟瞰》中指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5]他认为“近代文学的意义便是指活的文学,而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6],虽然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到来,近代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但其中有一部分文体”[7]在现在依然延续。但这里对近代文学的界定与现代的概念大相径庭。在这一阶段,近代文学成了一块任人分割的蛋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呼吁加强对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的研究,但还没有提出系统的近代文学概念,近代文学仅仅作为古代文学的附属品。五十年代中期各院系开始编撰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史和整理近代文学资料,必然面临着时间的限定问题,一般把近代文学限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段,也基本上形成了中国文学古代、近代、当代“三段论”的断代模式。“文革”之后,伴随着改革的东风,近代文学研究开始复苏,但学界对近代文学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用晚清文学、清季文学、清末文学来替换近代文学,认为文学与历史同步发展,采用历史学家的划分方法,上限为鸦片战争(1840),下限为“五四”运动(1919),前后约八十年。1982年在河南开封召开的首届近代文学研讨会上,研究者们对近代文学的界限提出了两种意见:一些人将近代文学的上限推到1821年也就是道光元年,下限下移到1929年,并认为从“五四”到192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缓冲区。其立论点,一是文学虽然受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不一定与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致,要依据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文学的性质来划分,同时注重内部文学观念、语言形式的变化,也就是上启道光元年(1821)晚清“宋诗派”兴起之际,下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1929);二是要虑及近代文学的复杂性,近代文学跨清代和民国两个阶段,多种文学因素在这个时代并存,这是一个过渡期。如果简单地把鸦片战争定为上限,如李汝珍、龚自珍等对近代文学但开风气之先者,就被划分出近代文学,而像林纾、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鲁迅等在现代依然健在,并且产生了重要的文学作品和影响,说明在“五四”运动之后近代文学还没有结束。另一种观点是,把近代、现代文学合一,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时期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理由是:一、在这百年内中国的社会性质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二、从文学的任务来看,反帝反封建依然是中心任务,倡导白话文,向西方学习,提升小说的地位,强调文学反映现实的社会功能;其三、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文学革命的任务和口号在前八十年中诞生,在后三十年间延续。因为“五四”前后的时代是一个整体,能够如实地体现出文学发展的性质、主题、任务,而且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近代文学家在“五四”运动后依然有重要的文学活动,所以不必进行细部的分割。郭延礼在《“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三论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问题》中则指出,上述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范围有待商榷,从文学总体上来看,“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不论表现的社会生活,抑或是艺术形式,乃至审美理想、思维方式,近代和现代有很大的差异”,近代文学的下限应恪守“五四”。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仍然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上限,将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下限。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8]随着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学者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整体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理由是十九世纪末“世界文学”的概念已形成,中国的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发生断裂,进入与传统有别的现代“世界文学”;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依然是中国的民族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显现出的美感特征渗透出危机感和焦灼感,与十九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迥然相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重大的形式革命,具体来说,就是文学文体、语言形式、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这并不是因政治因素而被迫进入现代化的进程。这种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8年,章培恒、骆玉明在以人性论贯穿始终的《中国文学史》中将以中华民国的建立作为近代文学的下限,而在2007增订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则把1900年作为近代文学的下限,仅仅把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附庸。施蛰存在《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中提出:“‘近代文学’是文学上的近代,‘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9]他在自己编撰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指出,“近代”的时间界定不应该采取历史学家的分期法,近代文学的下限不应该是1919年,而是1917年胡适回国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号召新文学之时。编选作品应以1916年为下限,而上限因不同文体而有所差异。他认为翻译文学和近代小说的上限应为1900年,因为这一年翻译文学勃兴,体现近代文学精神的新小说才产生。虽然学术界对于近代文学内部的划分有些差异,但一般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文学的上限,而下限定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
海外和中国港台地区一些近代文学研究者试图用“晚清”替代“近代”这一概念,但在时间界限的划分上略有差异,港台学界一般认为近代文学是指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就是1840年到1911年这段时间的文学。王尔敏的《晚清政治思想论丛》、周阳山和杨肃献编著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汪荣祖的《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林明德编著的《晚清小说研究》和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都持此种观点。薛化元在《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中,将晚清起点定为1861年洋务运动,终点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认为晚清从太平天国起义(1849)始,至清朝倾覆(1911)止。虽然他们在对时间的起始点的界定上有所差异,但不难发现界定晚清文学时间的重要依据仍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本论文中,将近代文学的时间上限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定为1919年“五四”运动。这样既尊重了学术界的规范的界定,又突显出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巨大变革,同时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文学的下限,又显现出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二、文献综述、研究现状
中国的近代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变革期,也是中国文学的总结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中国文学的内容、观念、语言形式都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的文学观念、文体形式不再是简单地接续中国的文学传统,而是要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两种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冲撞中存在。并非被动地硬性地接受输入,中国人开始审视世界,在中西体用之间权衡,中国文学的内部已发生了松动,文学观念、文体形式不断地更新和重组,文学观念、文体形式、文学理论一步一步地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材料的收集﹑编选工作十分繁重,一些材料也难于寻找。就连郑振铎在编辑《晚清文选》时都慨叹“材料不易的”。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果丰硕:阿英整理出版了《晚清文学丛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为了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选了《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上海书店出版了六集三十册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了八十册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钱仲联编著了《近代诗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张枬和王忍之编选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钟叔河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为研究者整理出了全面的一手资料,有利于研究者深入地了解近代文学的全貌。同时产生了一批关于近代文学家和作品的整理和研究资料,仅《康有为全集》就有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两个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章太炎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国维全集》,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全集》等。魏绍昌编选了《孽海花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河北师大薛绥之、张俊才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牛仰山编写了《严复研究资料》,安徽师大孙文光主编了《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等。而且,有的学者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又重新扩充编选,如薛绥之、张俊才编选了《林纾研究资料全编》。在对原始资料编撰和整理的同时,上海书店、人民出版社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了一批近代报刊,如上海书店影印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吴趼人等主编的《月月小说》、黄人和徐念慈主编的《小说林》。首都师范大学影印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汇编》,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原初的媒介生态现场。而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资料最为丰富,现已出版正编、续编、三编共285辑,包括近代名人奏折、政书、年谱、笔记、日记、诗文集及经世文编、碑传集等,其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这些资料不仅全方位地反映了近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也为研究者回到文学现场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对近代文学理论进行整理的成果,仅有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在五十年代编选的《近代文论选》,而进入八十年代后,不仅影印了胡适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还有徐中玉编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贾文昭在完成《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之后,又推出了《中国近代文论类编》,分类编选深受原有的文学概论体系的影响。王运熙又主编《中国文论·近代卷》,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同时对不同文体理论进行整理的成果也层出不穷,较为重要的有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丁锡根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蔡毅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秦学人、侯作卿编著的《中国古典编剧资料汇辑》,王水照编的《历代文话》整理出当今学术界稀见的近代文章理论和文体理论。此外,有的学者遵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理念,陈平原、夏晓虹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严家炎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在全面对近代的文学理论进行整理和编选的同时,研究者注意到对个别文本的校释、笺注、汇编。有的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人间词话》上,仅校注、汇编本就十余种,而其中不乏力作。如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校注》,刘锋杰、章池集评的《人间词话百年解评》,周锡山编校的《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等,王气中的《艺概笺注》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还有对近代文学书目、年谱、文集、选集的整理和校释,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对近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编撰、整理、校释,既丰富了近代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又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有利于研究者如实地再现近代文学的文化语境,回到近代的文学现场。
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同步的,早年,虽然学者们已经有近代的意识,但还是在摸索之中,而对近代文学的文体研究还是散见于序跋、介绍、诗话、评论之中。二十年代以降,史论辈出。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清代的小说文体归结为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及公案、谴责小说这几类。1927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界定了文学的本质、范围、对象、起源等文学的基本问题,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变迁中言志和载道是此消彼长,他立足于新文学的立场,把八股文和桐城派作为文学发展的反动,将“五四”新文学的源流追本溯源到公安派的“三袁”。而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偏重于白话文的文体流变。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语境,他系统地梳理近代文学、文体、学术及文学流派的演变。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首先使用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并界定了近代文学的时限,陈著着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如文学界的“三个革命”,桐城派、宋诗派古典主义的新进变化,翻译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在新旧两种文学的选取上绝不偏颇,较为客观地再现了文学现场。而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以诗、文、小说、戏曲文体为切入点,又兼顾民间文学和文学革命运动,系统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文体的变迁和发展。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那个时代的又一部力作,他在《绪论》中界定了文学、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这里所谓的现代是指辛亥革命以后,他将新文学分为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将现代文学分为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此书以人物代史论(以此认为现代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亦传亦录,材料丰富。1940年,吴文祺在《学林》上发表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带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他依照着历史的演进,对文艺思潮的脉络进行了梳理。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也是这个时代的力作。此外,这个时代较为重要的文章还有1937年刘然章发表在《民钟季刊》上的《中国近代文学变迁大势概说》。针对个别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等问题的文章屡见不鲜,涉及文学文体问题的文章有瞿宣颖的《文体说》、陈灨一的《论桐城派》、周振甫的《章太炎的文章论》等,还先后出版了薛风昌的《文体论》、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施畸的《中国文体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等著作。也有著作立足于近代文学文体史的梳理,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郑震的《中国近代戏曲史》。这个时期的近代文学文体研究者,多数为近代文学变革的亲历者,由于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多数时候,近代文学还是涵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中可以看出。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更是认为“近代文学是近古期文学的第二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个乐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为止”。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完成了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近代文学也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独立出来。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佳作辈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得风气之先,将1919—1979年间有关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分为概论卷、小说卷、诗文卷(在1949—1979年的选本中改为诗词、散文卷)、戏剧卷(在1949—1979年的选本中增加了民间文学,改为戏剧、民间文学卷),结集为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七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五四”到新时期近代各种文学文体的文章的总结,也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钱仲联校注近代文学作品的同时,将研究清代和近代文学的文章结集为《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任访秋由古典文学转向近代文学,所著的《中国近代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正本清源,兼顾古今。关爱和也完成了《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论历史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古典主义的终结》,这些著作产生一定的影响。郭延礼在完成《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著作之后,宏观地审视近代文学,于1998年又推出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而后完成《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他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撞和交流中,重新梳理和阐释近代文学。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和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多有新意。黄霖继承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完成了《中近代文学批评史》。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裴效维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等。有的研究者撰书对中国近代美学史进行了梳理,如聂振斌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史》,这些著作大多以史代论,侧重以人物为中心。卢善庆在《近代中西美学比较》中有意识地构建西方美学和中国近代美学、美学家的关系,同时对近代、现代美学概论式的著作有所介绍。1983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不定期出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期刊,到了九十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也出版了一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书》,展现了对近代文学的系统研究成果。
八十年代以来,文体学研究不断升温,一批文体学著作先后出版,如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调公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张寿康的《文章学概论》和《古代文章学概论》,秦秀白的《文体学概论》,钱仓水的《文体分类学》,王凯符等的《古代文章学概论》,张毅的《文学文体概说》,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纪君德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形成及其他》,宋常立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谭帆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朱玲的《文学文体建构论》。这些著作着力于理论文体学研究、文学文体的基本问题,涉及文体概念的界定、文体的分类、文体的特点等。同时,国外文学文体学的著作也被译介到国内,如雷蒙德·查普曼的《语言学与文学:文学文体学导论》,申丹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和《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侯维瑞的《文学文体学》,喻子涵的《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等等。文学文体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以童庆炳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以吴承学为首的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两个学术团体,前者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文体学,而后者侧重于历史文体学研究。童庆炳学术团队敏锐地觉察到学术界“语言论转向”的思潮,把研究中心转向了文学文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体学丛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王一川的《语言的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童庆炳的《文体和文体的创造》,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文化意味》,蔡原伦、潘凯雄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这些著作为理论文体学提供了多种的可能,在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童庆炳的《文体和文体的创造》兼顾中西文体和文体学理论,可以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文体学著作,他把文体作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注重文体与作者个性、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开拓了文学文体研究的空间。正如季羡林对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的评价:“‘文体学丛书’是一套质量高、选题新、创见多,富有开拓性、前沿性的好书。”而吴承学的学术团队的学术兴趣主要着力于中国古代的文学文体的历史,已经出版了三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其中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在学术界影响最大。一批博士论文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吴承学的《中国古典风格学》开风气之先,此外还有于雪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贾奋然的《六朝文体批评研究》,李长徽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潘莉的《〈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郗文倩的《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马建智的《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理论研究》,郑萍的《论周作人的散文文体》。也有论文借鉴西方的文类概念对文学进行理论研究,如陈军的《文类研究》。还有的博士论文注重媒介的变迁与文体演变的过程,如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周欣荣的《传播媒介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研究》,徐萍的《晚清到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也有极少数的博士论文中只对近代文学一种文体进行梳理和研究,如贺根民的《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靳志明的《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何云涛的《清末民初小说语体研究》等。目前还没有系统地、理论地、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文体转变的博士论文。曾枣庄的《中国古代文体学》从文体学的基本问题、文体史、文体学资料的整理三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文体进行了系统的、通论式的整理研究。李南晖、伏煦、陈凌的《1900—2014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收录1900年至2014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出版的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著作和论文,对论文和著作分类编撰,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索引。而冯光廉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以文体样式为学术切入点,翔实地分析了文体的内部结构和语言样态,立足于文学文体本身的审美特性,对近百年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季桂起的《现代转型的历史渊源——明代中叶到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变迁》,以现代性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本土资源和西学东渐的作用,描述了文学文体的内部格局的变化及文体形式的新迹象,认为近代文体的形成是西方文学的渐进和传统文学形式变通的结果。有的学者把近代文学的文体演变作为文学观念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探讨,侧重文学的内部研究。章亚昕在《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流变》一书中吸取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卡冈的艺术形态学和文化环境论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转换和变化进行了解析。章亚昕在《文风·文体·文论——近代文学观念的三个阶段》一文中认为,文体是近代文学观念变迁的重要阶段,文体更新是文风演进和文论转换的中间环节,带有过渡的性质。赵利民的《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研究》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通行的文学概论为范式,从文体论、创作论、价值论和悲剧理论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内部重构出发,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并设专章从纯文学的确立、近代文学的语言观和近代文学的“三个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几方面,对近代文学文体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袁进的近代文学研究围绕着近代文学之“变”展开,虽然他关注西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他的研究还是立足于近代文学的自我独立生成性上。他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小说变革》《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近代文学的突围》,都重视对文体之变的研究,把它作为文学内部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文学变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以“言志”和“载道”为主的实用主义观,他以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为参照系,对近代文学的运行机制、文学的内部结构和作家心态的转变进行分析。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以历史事件为断点对文学现场进行再现研究,对近代文学的流派和文体都有所论及。郭延礼的《近代西中学与中国文学》和《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强调西学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和文体转换的影响,翔实地分析近代文学不同文体的历史实际状况。关于近代文学单独的文体样式的研究也不乏力作,如欧阳建的《晚清小说史》,季桂起的《中国现代小说体式的现代转型与流变》,连燕堂的《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谢飘云的《中国近代散文史》,贾志刚的《中国近代戏曲史》,等等。随着中国文学文体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一些学者更加关注文体学研究,一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古代文体学理论和方法建构的论文为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如吴承学、沙红兵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吴承学、李冠兰的《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吴承学、何诗海的《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吴承学的《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解志熙的《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蒋寅的《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等等。有的论著关注文学文体理论研究,如童庆炳的《谈谈文学文体》,陈剑晖的《文体的内涵、层次与现代转型》。关于近代文学文体的研究著作有关爱和、解志熙、袁凯声的《论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孙宝林的《近现代文体演变的历史鸟瞰》,夏晓虹的《“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郭延礼的《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丁晓原的《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邱江宁的《现代媒介与文体变革——以王韬报章政论文为核心探讨》,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国内学术界目前缺少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文体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和全面描述的论文。
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在建构文学理论知识框架和编撰《文学概论》教材时,不得不面对文学的文体、文类及风格等基本问题,这类教材编撰者往往先罗列古今中外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再加以分类界定,最后再道出自己的文学文体观,如张健的《文学概论》在文类论中把文学的类型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柯庆明在《文学美综论》中认为“这种追求的‘美’的语言形式往往固定而成为普遍因袭或应用的文体或文类。透过文类或文体的观念化、规约化,往往人们就在不知不觉中,把文学的基本特征认同于一些固定的语言美的形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文学研究者深受M.H.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说”的影响,大多结合中国文论将其进行改造。王润华在《从四种立场四种观点看文学作品》中对“文学四要素说”进行了具体分析中,提出了多元、辨别类型的文学批评观。高明在编选的论文集《高明文学论丛》中,对各种文学文体的流变进行了全面概述。而梁容若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不仅对文学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而且慨叹中国文学的研究深受欧美、日本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影响,往往文学观念先行,没有如实地呈现中国文学文体发展的历史。李道贤在《王充文学批评及其影响》中既对中国文学的内涵进行了界说,又注重文学文体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同时总结了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林童照在《六朝人才观念与文学》中着重分析了文学与政治及近代思想的交互影响,这方面的著作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韦政通的《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卷,薛化元的《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986—1900)》,丁平的《中国文学史》,等等。黄维樑的《中国诗学纵横谈》注重文学理论批评,而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学纵横谈》则侧重于对文学文体和文本的分析。黄永武在《中国诗学》中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龚鹏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从中国文学的范畴入手考察文学观念的起源,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理则部分,侧重于对《文心雕龙》的文体学研究。王更生的研究生刘渼也完成并出版了《〈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此外,还有简翠贞的《从〈文心雕龙〉文体论看刘勰的小说文体概念》等。有的港台学者的研究着力于晚清小说的文体,这方面的著作有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林明德的《晚清小说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张玉法的《晚清历史动向及其小说发展关系》,尉天骢的《晚清社会与晚清小说》,吴淳邦的《晚清四大小说的讽刺对象》,赖芳玲的《论晚清的华工小说》,李健祥的《清末民初的旧派言情小说》,林明德的《晚清立宪小说》和《梁启超与晚清小说运动》,胡婉庭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曙光——梁启超小说理论取向及其实践意义探讨》,张巧瑜的《谴责小说在文体规范上的经纬结构历程关系——以曾朴的〈孽海花〉为例》,纪俊龙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重印本广告语境探析》。台湾学界对近代小说的研究最初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后来扩大了研究范围,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此外,还有其他文体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如张堂锜的《黄遵宪及其诗研究》,林峰雄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新风尚》,胡志德的《清末民初“纯”和“通俗”文学的大分歧》,黄克武的《严复与梁启超》,崔灵芝、黄涛的《黄遵宪及其诗歌的政治性》,郑雅伊的《清末民初古典诗学的自我转化——以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为探讨对象》,罗秀美的《从闺阁女诗人到公共启蒙者——以近代女性报刊中论说文为主要视域》,王心美的《文体分析的历史教育——以“经典研读”:梁启超〈新民说〉课程事件为例》。他们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在材料的具体使用上,有值得借鉴之处,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个别观点失之偏颇。
(二)国外研究现状
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影响深远。而美国学者也没有摆脱M.H.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说”的影响,刘若愚改造了艾氏的坐标系,把中国文学理论按照文学要素的趋向分为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美国学者王靖宇认为,从李贽到王国维,他们的小说批评都包含了艾布拉姆斯文学批评四要素。李贽的“童心说”显然是表现理论(艺术家)的性质;金圣叹强调从艺术观点出发,对特定的作品细加推敲;黄摩西在《小说小话》中提出的小说“好比如实反映现实的镜”的观念,而关于实用(欣赏者),冯梦龙的白话小说教育大众比古文更佳。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著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在翻译细读他所编选的文论时,有很强的文体意识,注重中英文体的转换。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中,解析了严复和梁启超的三篇小说理论文章,较为客观地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美国学者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阿·列·勒文森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捷克的汉学家米琳娜在其编选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的情节、叙事、人物进行了论述,涉及了晚清小说的基本问题。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二传手的角色,很多概念、词语和思想都是由日本改造输入的。太田善男在《文学概论》中对文学的定义直接影响了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日本文学研究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这里不再赘述。日本学界一直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对近代小说尤为关注。有些学者认为文学近代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内,没有独立的文学史地位,近代文学的主导还是古代文学,前野直彬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持这种观点。也有的研究者把中国近代文学独立来看,泽田瑞慧在《中国的文学》认为,近代文学应该是与政治一致的,清末文学就因民国的建立而结束了,它的余绪留至民国初年。小野忍在《中国近代文学运动史略》中认为,中国的近代文学,是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主张,可以将西洋文学及思想的输入看作中国近代文学的开端,“然而梁启超的新体文章(这种文体从汉语式的日文中剔除了假名)却获得了成功。他们都是广东人。当时古文家吴汝纶门下的福建人严复、林纾两个人已着翻译文学之先鞭……在清末就是这种程度的欧化”。关于近代文学文体论研究的论文,有中野美代子的《说部考》,乔木高胜的《通向梁启超小说的道路》,金九邦三的《王国维的词论》。而冈崎俊夫在《王国维的悲剧》中指出,文学是有时代性的,强调文体要适合时代需要。此外还有具体针对文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著作,如麦生登美江的《李宝嘉的创作意识》,大野实之助的《从形式看黄遵宪的诗》,樽本照雄在《〈官场现形记〉的真伪问题》《〈老残游记〉试论》和《刘铁云与〈老残游记〉》等。樽本照雄在《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广为收录和整理小说书目,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书目资料。狭间直树编撰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报告》,对梁启超进行了全面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九十年代出版铃木真美的《日本的“文学”概念》时,中译本改题为《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这一节中,她认为在十九世纪中叶“文学”=“polite literature”(“风雅文学”);十九世纪末,史诗、小说、戏曲等被纳入“集部”;二十世纪前期,近代文学的概念才被普遍使用。
中国近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直吸引着国外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他们在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既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丰富的材料基础,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本论文的研究本着“历史优先”的原则,立足于“问题意识”,既注重视点,也不忽视面,基本方法是宏观入手,微观着眼;论从史出,考论结合,力图梳理清楚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转换,缕清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流变脉络。
在研究方法上,力图还原近代文学现场;在材料选取上,回到原初语境,尽量少使用整理过的二手资料,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和分析近代文学观念和文体;在文献使用上,注重对原始材料细读的同时,又兼顾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推本溯源,注重材料之间的联系,借此理清思想脉络。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宏观与微观,文字与图像,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按年代、关键词分类整理,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分析现有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发现问题,加深理论,深入研究。
创新之处是力图最大限度地收集第一手资料,如实地还原文学现场,梳理清楚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演变,呈现出近代文学的文体复杂性。
从宏观研究来看,主要内容是探求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源流、发展脉络;描述中国近代文学的文体走向,以及对现代文学文体及其确立的影响,注重经史等学术走势的交叉与互动;分析个人的精神诉求、时代思潮及其对文学传统的态度;力求全面地反映近代文学的文体流变。
从文献方面来看,研究涉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生平、交游以及著述,尽量参考正史、笔记,包括家谱与方志材料等,尽量呈现其思想全貌。以期刊为中心进行研究,力图发现新材料、新观点,全面地再现近代文学的风貌。
从史论研究方面来看,区分近代文学各流派,分析它与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渊源关系,将地域性研究与个案思想以及作品联系起来,揭示出它与传统思想、西方思想的内在联系。
要充分注重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多种古代的文学形态并存其间。同时,近代文学又孕育着“五四”新文学,起到承接转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