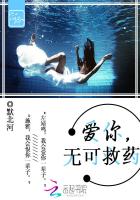钱德拉被电话吵醒了。
“查尔斯?”
他打开床头灯,结果把他的书和白兰地杯子打落在了地板上。
“嗯。嗯。怎么了?”
“我们找不到贾斯敏。”
“她在哪儿?”
“我说的是,我们找不到她,查尔斯。”
“啊,上帝呀。现在是什么时间?”
“差不多四点。”
“我这就去。”
“她在博尔德。我去找你吧。”
他走进卫生间,开始刷牙。电话又响了。珍妮想不起他住在哪家宾馆。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史蒂夫待在家里,以防贾斯敏回去。
钱德拉刮了胡子,穿上昨天穿的衣服。在宾馆大厅里,他看见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男人正通过旋转门,一只手搭在一个女人赤裸的背上。那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穿一件黄色的夏季连衣裙,脚蹬蓝色高跟鞋。她摇摇晃晃地朝他走来,目光呆滞。那个男人近乎面无表情。
珍妮抵达时散发着酒气。她上身穿一件灰色卡迪根羊毛衫,下身穿白色裤子,脸上无妆,更像他记忆中的她。
“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她的朋友苏茜打了电话。她说贾斯离开了聚会,显得很古怪,她想知道她是不是已平安到家。”
“她的朋友是在半夜给你打的电话?”
“史蒂夫说不用担心。她肯定是和一个男孩子离开的。女孩子们都那样干,我应该允许她长大。他说,她要是瞧见了我们,会疯掉的。”
“也许他说得对。”
“如果他不对呢?”
“我这就去开车。”
钱德拉乘坐电梯来到停车场,钻进他租的车里。当他把车停在宾馆外面时,珍妮仍在打电话,但立即挂了电话,上了车。
“我们去哪儿?”他问道,打开了GPS。
“我会给你指路。”
当然了,博尔德现在是她家嘛。
“我担心她,查尔斯。”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她不快乐。史蒂夫说,所有的小青年偶尔都会抑郁,它对他们的危险要小于对我们的危险,但我不相信他。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他,但她还是不快乐。那我为什么不该担心呢?往左拐。”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用不着担心,那对谁都没好处。”
“人们究竟为什么要那么说,查尔斯?我的意思是,我是因为担心才来这儿的。做母亲的担心很正常。我们担心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他们能够感受到。那也让他们有安全感。”
“对做父亲的来说也正常。”
“我知道。”
她的手碰到了他放在变速杆上的手。他想,他们会永远拥有贾斯敏。然后,他意识到,这不可能。她很快就会像另外那两个那样,生活在一千英里之外,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也许她还会有自己的家庭。那意味着,珍妮和他之间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在他人生的迟暮之年,他将独自一人,回顾往事,像个营造商那样,查看他花了数十载建造的房屋,然后才交出钥匙。
珍妮把他带到了一座两层郊区房屋。那座房屋的车道很宽,上面停了至少六辆车。两块窄窄的草地充作前院,上面也停了两辆车。已是凌晨四点半,但窗户里仍亮着灯,楼上窗帘后有人影晃动。
“就是这儿。”珍妮说。
彩色玻璃房门上方的信箱上写着:甭想把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东西塞到这里。他们能够听见音乐,爵士乐风格的,节奏感很强。钱德拉敲了敲门,听见了里面好像在喊警察。他拽开信箱,说:“我是贾斯敏的父亲。”
“好极了。”珍妮喃喃地说。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绑着辫子的金发女孩。由于戴着眼镜,她蓝色的大眼睛显得更大了。她穿着斜纹工装裤,唇彩鲜红,欣喜若狂地咧着嘴笑。
“我能帮你们俩什么忙吗?”她问道,手抓着门框。
“苏茜在这儿吗?”珍妮问道。
“在啊。”那个女孩说,吸吮着她的手指,“苏茜!”
钱德拉看见一个深褐色头发、年龄相仿的女孩走下楼。她只穿着一件长T恤,T恤前面印着雷蒙斯乐队。
“嗨,贝诺维茨夫人。”她说。钱德拉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说的是谁。
“嗨,苏茜。”珍妮说。
“天哪,见到你太好了,”那个女孩说,“我的意思是,哇,你在这儿,那就像……哇。”
“你给我打了电话,苏茜。”
“我没给你打呀,贝诺维茨夫人。我是说,那不意味着我不喜欢你。我只是没给你打过电话。”
有人在她后面喊道:“你没打过电话,骚货。”苏茜用手捂住嘴,哧哧地笑了。
“你给我打了,苏茜。我知道是你打的,因为我听出了你的声音。你说贾斯敏出去了,你想知道她回家了没有。”
“噢,是的,贾斯。”苏茜说,“你是贾斯的妈妈,贝诺维茨夫人。没错。啊,我的上帝呀。”她一边说,一边看着钱德拉:“你是她爸爸?”
“无论她在哪儿,告诉我们就行,”钱德拉说,“我们很担心。”
“你们在找贾斯?”一个男孩子问道。他高高的个子,光着膀子,下巴上长出了一簇黑胡须。
“是啊,”钱德拉说,“她在哪儿?”
“她走了约两小时了。不过,你也知道,她神志有些不清醒。我的意思是,她看上去迷迷糊糊,真的累垮了。她没回来,我们都很担心。”
“那是什么意思?”珍妮说,她现在有些恼了,“你说‘累垮了’是什么意思?”
“给她说说‘斯鲁姆斯[40]’!”屋里有人喊道。
“闭嘴,乔希!”苏茜说。
“她吃了蘑菇,先生,”那个男孩说,“问题是,我觉得她还不习惯。她就那样,好像……”
“完了。”苏茜说。她又用手捂住了嘴。
“她搞得一团糟,”那个男孩一边说,一边点点头,“她真的出去了,没人能搞清她去了哪儿。我们觉得她肯定回家了,但接着有人看见她的车还停在这里,于是我们想,她可能打了车。”
“我不敢相信你们居然让她那么走掉,”珍妮说,“居然还吸毒!你们想让我们喊警察吗?你们想吗?”
“主呀,不要!”苏茜说,“我们打电话了,因为我们担心,贝诺维茨夫人。我们应该阻止她,我懂,可这里的事情太多了。”
“你们谁都没想过去找找她?”珍妮问道。
“我们打了电话,可她的手机在屋子里,”那个男孩说,“我应该去追她。怨我。”
“我们聚会差不多开到了一半。”苏茜说,她回过了神,“我想说的是,谁想离开都可以。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不想有任何不敬。”那个男孩说。他举起手,仿佛遭遇了抢劫。
“把她的手机给我们,我的天。”珍妮说。
苏茜犹豫了下,然后转身,朝楼上走去。
她回来时手里拿着手机,然后交给了珍妮。
“祝你好运,贝诺维茨夫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真的很抱歉。”
“我们希望你们能找到她,先生。”那个男孩对钱德拉说。
珍妮关上了门。她的呼吸很粗。钱德拉分辨不出那究竟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着急。
“没事。”钱德拉说,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今夜挺暖和的。她会没事的。我们去找找她吧。”
“好的,”珍妮说,“好的,你开车。我在这附近找找。你带手机了吗?”
钱德拉点了点头:“我可以报警,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还是先找她吧,”珍妮说,“如果我们半小时内找不到她,我们就报警。好吗?”
“好的。”
珍妮绕着房屋,走入黑暗中。那里肯定是后花园,钱德拉看见了松树高大、挺拔的剪影,像高等法院法官,后面还挂着一轮水汪汪的月亮。他上了车,摇下车窗。他能听见珍妮在喊贾斯敏的名字。
钱德拉开始在附近的街区兜圈子。他看见一个女人在遛狗,就放慢了车速。
“打扰一下,”他问她,“你见过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女孩吗?”
那个女人瞪了他一眼,说了声“流氓”之类的话。几分钟后,他遇到了两个女人。她们有二十多岁,手拉着手。“我在找我的女儿。”他对她们说。
这两个女人比较愿意帮忙。她们问了她的长相,要了他的号码,说如果看见她,就打电话。
钱德拉一直想消除担忧,但现在他的担忧更重了。如果贾斯敏被强奸了,或被车撞了,或被割断喉咙,躺在沟渠里,该怎么办呢?他打开了收音机,希望可以平静下来。收音机在放萨姆敳库克的歌,歌名叫《丘比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他和珍妮曾随着它翩翩起舞。那是他第一次当众吻一个人。即使是现在,他也能嗅到她的香水味。
钱德拉的手机亮了,有个未接电话,号码他不认识。他打了回去,一个女人接了电话。
“嗨,我是雪莉。”
“哪个雪莉?”
“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帮你找女儿的。”
“哦,是的,对。”
“听着,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但有个人坐在康奈尔街和第四大街交叉口的一个垃圾箱旁边。她不理我们。”
“她叫贾斯敏。”他说。他骂骂咧咧地运行着GPS。
“贾斯敏。”他听到那个女人说,“你叫贾斯敏吗?宝贝儿,你是贾斯敏吗?”
开车到那里需要两分半钟。他给车挂上了挡。
“她什么也不说。一直瞪着眼。”
“好的。我正往那儿赶呢。”
钱德拉把手机扔到了乘客座上。他能嗅到血腥味。他一害怕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她们不是已经发现她了吗?
他在第四大街停了车,看见那两个女人站在角落里。他没找到贾斯敏,不由得再次恐慌起来,直到一个女人指了指她们左边的一条小巷。
“她就在那儿,”她说,“她不理我们。”
钱德拉点了点头。由于着急,他忘了感谢她。他还是没看到贾斯敏,但当他抵达小巷中间的那个垃圾桶时,他看见她坐在地上,膝盖顶着下巴,看着前面的木栅栏。钱德拉想让她起来,说地上脏,她一晚上惹的麻烦够多了,但她不怎么正眼看他,他的怒气消了。转而掏出手机,给珍妮打电话。
“爸爸,”贾斯敏说,“别打电话。放下。”
她说话慢吞吞的,仿佛费了好大劲儿,但声音听起来还算正常。实际上,她的声音很平静,比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平静。
“我在给你母亲打电话。”
“暂时不要。”
“她很担心。我也很担心。你在干什么?”
“让她再担心几分钟吧。她死不了。”
“不。我要给她打电话,贾斯敏,然后你要回家。”
“家?家在哪儿,爸爸?”
“什么?你说什么?我们走。起来。”
“你有家吗?”
“起来,我的老天。你那样坐在地上像个流浪汉,想干什么?”
“一起坐,爸爸。”
“起来!”
“你也可以坐下来,要不就滚。可我希望你坐下来。”
月光照着贾斯敏一侧的脸颊,让她看上去像一座雕像。他穿着他压平的裤子和夹克坐下来,肩膀几乎碰着了她的肩膀。地上很凉,但至少还干燥。借着如水的月光,他可以查明附近没有老鼠。
她还是穿着一身黑衣,但她的头发里现在出现了条纹,他分辨不出那是什么颜色的。也许是橘红色?贾斯敏的肤色比她的哥哥、姐姐的深,有时候会被误认作希腊人或意大利人,但她仍旧抹着那种幽灵般的粉底霜。虽然她化了妆,但她长得像他,她的鼻子,她的额头。他不再懂她了。他想爱她,但不知道怎么爱她。
“那你想干吗?”他问道,“你想报复我们?”
“为什么要报复你们?”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过去对你做过的无论什么吧。”
“就算报复了你们,又能怎样呢?”
“我不知道。”他说。他用手拍了拍地面,想知道有没有人能听见他们说话。
“也许我就是想和你坐在这儿,看看天空。你为什么不试试呢,爸爸?看看天空。来呀。”
钱德拉抬头仰望。
“嗯,我看过了,”他说,“那是一片天空。那又怎样?”
“都在那上面呢,”她说,“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天上。”
天空的边缘现出空白,色彩逐渐变淡。黎明将至。他看见右边的地平线上升起灰色螺旋,西边的某个地方可能在下雨。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非得是某种东西呢?”贾斯敏问道。
“我听不懂。”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非得做些什么呢?我不过是坐在这儿,就让你那么生气。”
“我们很担心。”
“可你现在不担心了。”
“我还是很担心。”
“为什么呀?”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几乎什么也没说,爸爸。你难道没瞧见吗?我在这儿。我不过是走到这里,待在这里。你却吓坏了,就好像发生了灾难。就在这里陪着我吧,爸爸,几分钟。”
“你妈妈太担心了。”
“就几分钟。”
他默默地坐着,瞪大眼睛,盯着栅栏。他心烦意乱,尽量不看贾斯敏。他想掏出手机,但害怕如果他这么做了,她不知道会说什么。他试图闭上眼睛,但这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一阵婴儿的哭声从某个地方传了过来。
“我是唯一无足轻重的人,”贾斯敏说,“苏尼一直想成为你。拉达一直想成为你的对头。我,我什么都不是。我不像你,也不像妈妈。我根本不重要。”
“不是的。”
“我什么都不是,爸爸。你们总以为我不重要。没关系,我不介意。”
她真的这么想吗?真是这样吗?钱德拉再也不知道了。他只知道他需要他的女儿(他直到现在才明白了这一点),而他就要失去她了。
“你并非什么都不是。你是我的全部。全部。我什么也没有。没有妻子。一无所有。我才什么都不是。你是我的全部。”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没事了,爸爸。”
“我不明白。”他说。
“我也不明白。谁会明白呢。”
他捡起一个石子,朝栅栏扔过去。石头从两根板条间穿了过去,但他没有听到它落地的声音。他又捡起了一个。这次它“啪”的一声砸中了板条。
“不怨你,爸爸。”
“怨谁呢?”
“谁都怨。谁都不怨。不重要。”
他再次掏出他的手机。珍妮没有打过电话。
“我觉得你最好给妈妈打个电话。”贾斯敏说。
“贾斯敏,你生病了吗?你需要看医生吗?他们说你吃了蘑菇。”
“致幻蘑菇。是一种毒品,爸爸。”
“毒品?”
“就像迷幻药,”贾斯敏说,“不过是天然的,没什么危险。我有点儿疯癫,不过我现在好了。真的。”
“你是从哪里搞到它们的?”
“他们想分享,可我想,去他们的吧,他们要上大学。于是我就把它们都吃了。”
“什么?”钱德拉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把它们都吃了。”
“你也要上大学啊。”
“我把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全搞砸了,爸爸。我只能去上社区大学,其他的哪儿也上不了。我被困在这个地方了。”
“不,贾斯敏,不。你可以去英国。无论什么地方。我们掏得起钱。”
“都要看分数的。你不知道我考得有多差。我哪儿也去不了。”
“没事的,贾斯敏。我会搞定的。我是个教授。我能解决。”
他想伸出胳膊抱住她,但他做不到。他不习惯肢体上的安慰,他畏畏缩缩,害怕遭到拒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爸爸。一切安好。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月亮已经落下。他拨打了珍妮的号码。
“好的。”珍妮说。他跟她说贾斯敏找到了,她听上去并不意外。
他和女儿向汽车走去。钱德拉想起了他在池塘边说的那些关于规矩的话,说它们如何不存在,说就算存在什么意义,他们谁也不会知道是什么。那不就是贾斯敏一直试图告诉他的东西吗?她比他早五十年领悟到了,这可能吗?
刚坐到车里,他就说:“我觉得我明白,贾斯敏。”
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真的明白?”
“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就好像一切都根本不重要。我懂。”
“是吗?”
“可毒品不管用,贾斯敏。根本不管用。”
“你又怎么会知道呢,爸爸?”
“毒品危险,贾斯敏,大家都知道。要解决问题,有别的办法。”
“你想想看,爸爸,谁真的在乎呢?”
“我在乎。”
“可你在乎吗?你真的在乎吗?”
“是呀,我在乎。我有时候会忘记一些事情,有时候会说傻话,可我在乎。那是我唯一确信的事情。”
回去路上,贾斯敏把车窗摇下来,盯着大街。天空现在泛着灰白色。也许再过半小时,天就亮了。等他们抵达苏茜的房子,珍妮坐到了后座。让他意外的是,珍妮一言不发,既没理他,也没理贾斯敏。
到了史蒂夫和珍妮的房子,大门已经打开。贾斯敏拉着珍妮进了屋,一句话也没说。钱德拉不知道该干什么,就绕到了房子后面。史蒂夫正站在池塘上方的低跳板上,在清晨的寒意中浑身赤裸,做着深呼吸:“呼——呼——呼——”
“早上好。”钱德拉说。史蒂夫已从边缘上退了回去,像个螺旋桨那样转着他的胳膊。
钱德拉尽量不看史蒂夫的阴茎,但他不由得注意到,史蒂夫的私处刮得干干净净。
“早上好,钱德拉塞卡。”史蒂夫说,他离开跳板,从池塘对面走过来,“我猜你昨晚没睡好。”
“我们不得不找贾斯敏。”
“是呀,你们找到她了。我说过,她没事。”
“不是的。”钱德拉说,他走近了一些,这让他不太容易看见史蒂夫的阴茎,“她吸毒。”
“毒品?”史蒂夫说,“真的?”
“致幻蘑菇。”
“噢,是的。我们谈过这个。”
“你们谈过蘑菇?”
“谈过一般的毒品,”史蒂夫说,“你瞧,她在尝试。”
“你对她说什么了?”
“我对她说,要远离硬毒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就是让那东西给毁了。”
“关于致幻蘑菇,你给她说了什么,史蒂夫?”
“迷幻剂不一样,我的朋友。它们打开心灵之门。那正是东方的灵性带给西方的东西,你懂的。”
“不,史蒂夫,我不懂。”
“我不过是对她开诚布公,实话实说。我对她说,少量的迷幻剂伤不了她。吸大麻也不会。”
“你对她说了这个?”
“是呀,钱德拉塞卡。我说的是实话。”
“你知道我在哪儿找到她的吗,史蒂夫?”他说,“在垃圾堆里。”
他现在可以想象出,她面对着一堆垃圾,血从她的嘴唇滴落。这幅画面是那么清晰,他几乎要相信了。
“听着,钱德拉塞卡,小青年无所不为。等坐下来,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史蒂夫害怕了。钱德拉能看出来。史蒂夫甚至朝池塘边缘退了一步。
“她有可能死掉,史蒂夫。”
“不,不,不,不,不,我的朋友,不会因为裸头草碱而死。贾斯会没事的,我向你保证。不过是另一个故事而已。”
“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怂恿我女儿吸毒了,史蒂夫。”
“哦,我的朋友,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再也不要了,史蒂夫。”
“好吧,老兄。再也不了,我保证。”
钱德拉朝他走去,直到他们面对着面。
“我还想让你道歉,史蒂夫。向我,向珍妮。”
“得了吧,钱德拉塞卡。那只是个误会。我们进去吧,喝杯咖啡,一笑置之。”
“快道歉,史蒂夫。”
“我很抱歉。真心的。来吧。”
史蒂夫伸出了手。钱德拉盯着他。这只手是什么意思?如果碰了,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同意小青年可以吸毒?
“对不起,史蒂夫,”他说,“我拒绝和你握手。”
“哦,好吧,没关系。”史蒂夫一边说,一边垂下了胳膊,“可我对你的期盼不止于此,钱德拉塞卡。”
“还有什么期盼?”钱德拉塞卡问道。他看着晨光的触须悄悄伸到了池塘边缘上。
“我曾期盼一种更开明的方式,而不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样。当然了,随意吧。”
“贾斯敏是我的女儿。”
“是呀,好吧,我一向认为,孩子们不属于任何人。那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的错误,你懂的。”
“别扯了,你说得不对,”钱德拉说,“她属于我,我属于她。她不属于你。”
“这是我的家,”史蒂夫说,“不过我懂你什么意思。你感到愤怒,因为你对权力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我对什么的需要?”
“权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吗?你感到无权无势,就拿我出气。没关系。我懂。我可不愿意身处你那种处境里。”
“哪种处境?”钱德拉问道。他想,如果史蒂夫再往后退一步,就会跌入池塘。
“和珍妮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史蒂夫说,“我不想惹你生气。”
“这和珍妮无关,”钱德拉说,向前探了探身,“事关我女儿,而你却怂恿她吸毒。我在外面找了她整夜。她有可能死掉,而你,史蒂夫,却不在乎。”
“我在乎,我肯定在乎。我只是觉得,你在发泄你的痛苦,钱德拉塞卡。我们都知道贾斯敏没有危险。我们都知道这全是因为你妻子离开了你,因为她现在和我在一起。这很难适应。我懂。我同情你。”
“我觉得你什么也不懂,”钱德拉说,“我同情你。”
“那我们打住吧。”史蒂夫说,再次伸出了手。
“甭想。”钱德拉说。他一拳砸在史蒂夫的鼻子上。
史蒂夫用手捂住了脸。一汤匙左右的血从他的指尖滑落,闪着光,滴落在亮闪闪的地砖上。钱德拉扭了手。事实证明,揍一张脸和揍一台冰箱区别不大。史蒂夫正在倒下。他的后脑勺先碰到了水,接着是他的背部,最后他完全消失了。
几秒钟后,史蒂夫浮出了水面,在阳光下伸展着四肢,脑袋周围有一圈粉红色的光晕。这圈光晕慢慢膨胀,成了一团云。他翻过身,侧身游向平台,用肘部支撑在平台上,伸出几根手指,轻拍着鼻子。
“史蒂夫,”钱德拉说,“你没事吧?”
“还好。不碍事。我没事。请把毛巾给我。”
钱德拉绕过池塘,从沙发上拿起毛巾。太阳已经升起。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上方的碧空飞过。
“给你,史蒂夫。”他一边说,一边把毛巾扔了过去。
“谢谢。”
史蒂夫的声音听起来很滑稽,仿佛刚吞了氦气。血在池塘里依然可见,不过现在变淡了,正在溶解。钱德拉转过身,穿过纱门进屋。
珍妮正坐在早餐吧台上,背对着池塘。当他进来时,她把脸稍微转了一下。“嗨,”她说,“昨晚可真难熬啊。”
“她怎么样?”钱德拉说,避免眼神接触。
“她睡了。”
“我们要不要叫个医生?”
“不了。她没事,但她不想去参加毕业典礼。最后我不得不同意。我的意思是,她爱怎样就怎样吧。”
“哦。”当珍妮坐在他旁边时,钱德拉说。
“我很抱歉,查尔斯。让你白跑了一趟。”
“哦,不,”钱德拉说,“我们不能强迫她。我懂。”
“主呀,”珍妮说,“我们以前干过这样的事吗?”
“我们承受不起。”
“我觉得她真的想看见我们在一起,”珍妮说,“也许这一切真的让她受不了。”
“都是大学闹的,”钱德拉说,“她对我说了。”
“不是,查尔斯。她之所以那样说,不过是因为你想听那样的话。”
“那事关她的未来,”钱德拉说,“她在考虑未来。”
“她现在正考虑着呢,”珍妮说,“她只是需要看见你、我、史蒂夫和睦相处。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待一天,直到她醒过来。让她看看我们处得挺融洽。如果她去上一年社区大学,世界不会就此终结。”
钱德拉闭上了眼睛。对他来说,世界会终结。但是,问题是考试。珍妮希望他能更宽容,就像史蒂夫那样。
“我不那样想。”他说。
“我很抱歉,查尔斯,”珍妮说,“我知道你想让他们都上最好的大学,但让她快乐更为重要。她眼下可不快乐。对她来说,在家里再待一年甚至可能是好事。”
“从长期来看,接受良好的教育才会快乐。”钱德拉说。
“我不同意,”珍妮说,“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你不能就那么告诉她,什么对她好,查尔斯。你必须见到她。你必须倾听她的心声。”
钱德拉断定珍妮其实想说的是“就像史蒂夫做的那样”,或“就像史蒂夫倾听我的心声那样”,要不就抖落出二十年前发生的某件事,用来证明他不具备理解她的能力,或理解任何人的能力。他反过来会告诉她,他刚才像印地语电影里的场景那样,把史蒂夫揍进了池塘。
“你说到了规矩,”钱德拉说,“规矩之一是她要上大学,努力学习,不能破罐子破摔。”
“我同意。”珍妮说。
“史蒂夫会同意吗?”
“不会,”珍妮说,“但贾斯敏不是他的孩子。”
史蒂夫正拉开纱门,朝屋里走来。他穿着晨衣、拖鞋,鼻子里塞着棉花。他的鼻子看上去又红又大,但没有破。
“啰啰啰啦啦啦。”史蒂夫哼着曲子。
“啊,我的上帝呀,”珍妮说,“出什么事了?”
钱德拉的身体僵住了。有那么一会儿,他想逃掉,钻进他的车,一边驶过大门,一边晃着拳头大喊“嘿哈,干得漂亮”,或同样洋洋得意的话。他没有那么做,而是转过身来,看着史蒂夫。史蒂夫冲他微微一笑。
“我磕到了脸,”史蒂夫说,“在做那些欠考虑的翻滚转的时候。”
“哦,亲爱的。”珍妮边说,边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了她一直坐的凳子上。
“在电视上看着挺容易的。”史蒂夫说。
“没伤着吧,史蒂夫?”钱德拉说。他尽量装出亲切的口吻。
“我去给你拿些冰。”珍妮说。
“不碍事,”史蒂夫说,“我撞得不狠。”
珍妮走向冰箱,把一些冰块放在一块茶巾里,按在史蒂夫脸上。
“问题不大,亲爱的,”珍妮说,“只是擦破了皮。”
“贾斯怎么样?”史蒂夫说。
“她不想参加毕业典礼,”珍妮说,“不过她没事。”
“这么说吧,”史蒂夫说,“我几乎无法责备她。毕业典礼是一种毒品。三个小时,纯粹是受罪。”
“她永远不会再有一次这样的毕业典礼了。”珍妮说。
“那真要为此谢谢上帝了。你首先要听那些致告别辞的学生告诉你,他们将来会比你过得好,然后某个笨蛋会告诉你,要追寻自己的梦想,尽管他那一代完全扼杀了你的梦想。是吗,钱德拉塞卡?”
“是呀。”钱德拉说,他断定,无论史蒂夫说什么,他都最好同意,“我觉得你说得对。”
“贾斯待在家里更好。她昨晚和朋友在一起,玩得挺开心。那就够了。”
“史蒂夫,”珍妮说,“我觉得她不开心。”
“我知道,亲爱的,”史蒂夫说,“我的意思是,你在高中领悟不到人生真谛。大学也不行。贾斯是个聪明的孩子。她懂的。”
“那人生真谛要从哪里学啊?”尽管此前决定要顺着史蒂夫,但钱德拉还是这样问道。
“请不要扯什么生活的大学。”珍妮说。
“好吧,就像我昨晚说的那样,我从研究吠檀多派以及在伊莎兰的休息中获得了我一半的知识。”
史蒂夫把手放在珍妮手上,把冰袋向下拉了拉。
“是呀,”钱德拉说,“你说过。”
“那其实是两名斯坦福毕业生创建的,”史蒂夫说,“有趣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个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进了精神病医院。另外一个去了朋迪切里,奥罗宾多的静修处。”
“那又怎样呢?”钱德拉想这么说。他瞧不起嬉皮士,但他更讨厌那些所谓的圣人。他们不过是身上抹灰、抽大麻的乞丐,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希望获得普通劳动人民的尊敬。
“总之,”史蒂夫说,“1962年,他们回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另外几个家伙聚在一起,其中包括赫胥黎、瓦茨,开办了伊莎兰学会,以过去生活在那里的部落命名。对你来说,那不过一种单足跳、一种跳跃或是一种弹跳。你可以在那里待几个小时。”
“啊,我的上帝呀。”珍妮说,用手捂住了嘴,“你该不会真的建议查尔斯……”
“哦,我确信钱德拉什么都想试试,”史蒂夫说,“把iPad递给我,可以吗,亲爱的?”
史蒂夫慢腾腾地走了过来,直到他的肘部碰到了钱德拉的肘部。
“看呀,”他说,“这里有那个地方的一些照片。漂亮,对吧?”
钱德拉看了看。他看见了一些花园,以及一个面朝大海的游泳池。史蒂夫点开了以前的教师的名单。他们大多是常春藤联盟学校的博士,理查德敳费曼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是钱德拉认识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这里有一些即将开办的研讨班,”史蒂夫说,“‘自然歌手:心灵的独唱’‘高级瑜伽’‘情侣密宗按摩’‘夏至日成为自己’‘西藏大手印之路’‘禅宗之道’‘女人狂喜之舞’‘克服上瘾:不用十二步,只用六步’。有你喜欢的吗?”
钱德拉摇摇头,然后注意到了史蒂夫的表情。史蒂夫的表情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恶毒。这是报复,是在迫使他开口说话。
“上瘾,用不着。”钱德拉说。
“除非你算上工作。”珍妮说。
“我没算上工作。”钱德拉说。他发现“工作狂”这个词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矛盾。“瑜伽,算了。”自从来到加利福尼亚,他已经开始把瑜伽视为现代生活最大的恶行,“情侣,用不着。唱歌,算了。”
“这个怎么样?”史蒂夫问道。他点开了“夏至日成为自己”。这个研讨班持续三天,花费两千美元。“当我们学会开始无视我们头脑里批评的声音,不再相信智慧在外,转而求之于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常常会在个人发展上得到最大的飞跃。这个研讨班将有助于我们开始聆听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不这么认为。”钱德拉说。
“我掏钱。”史蒂夫。
“啊,上帝呀,别呀,”钱德拉说,“别呀,别呀,别呀。”
“我坚持。”史蒂夫。
“别傻了,亲爱的,”珍妮说,“查尔斯就是做梦也不会干那样的事情。一万亿年也不会。”
如果是半小时前,可能还真是这样,钱德拉想,但他现在别无选择。他揍了史蒂夫的脸,这是他的报应,他们俩都知道这一点。
“那我就去吧,”钱德拉说,“可我不能让你掏钱,史蒂夫。”
“上帝呀。”珍妮说。
“好极了!”史蒂夫说,“你将和鲁迪敳卡茨在一起。鲁迪挺了不起的。”
钱德拉正在看明星代言:阿里安娜敳赫芬顿、鲍勃敳夏皮罗、阿兰妮斯敳莫里塞特……让他感到吃惊的是,居然还有约翰敳加尔布雷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他很熟。“我有偏见,”加尔布雷斯写道,“但我想说的话发自肺腑:我也许是他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学生。”
“我希望你清楚去是为了什么,”珍妮说,“它不是剑桥,查尔斯。”
“是的,”钱德拉仰起头说,“是的,我知道。”
“对你有好处。”史蒂夫说,钱德拉此时能够想象他头上长了角。“棒极了。”
“好吧,”钱德拉说,“我们以后再谈这个。我现在要回宾馆了。”
“好吧,”珍妮说,“我们都需要睡一觉。查尔斯和我折腾了一夜。”
“好的,当然了,”史蒂夫说,“但我们下午见,好吗?”
“贾斯敏什么时候醒了,给我打个电话。”钱德拉说。
“好好休息,查尔斯。”珍妮一边说,一边握住了史蒂夫的手。
“你也好好休息。”
他绕过房屋,来到车库,找到了他的车。他花了几秒钟找钥匙,直到看见它插在点火装置里。他开着车驶向大门时,看见拉斐尔在给附近的花草浇水,挥手和他道别。
“再见。”钱德拉说。
“再见。”拉斐尔说。
开车下山时,钱德拉想起了他的拳头碰到史蒂夫的脸时的感觉。当史蒂夫的身体跌入池塘,太阳分外明亮,似乎要爆炸了,水变成了粉红色。钱德拉也扭到了手,指关节刺痛。现在,他头晕眼花,极度紧张,仿佛他巨大的汽车随时都有可能从路面上飘起来,飘到空中。
“就这么着吧,”他对自己说,“我要参加研讨班。我要追随我的天赐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