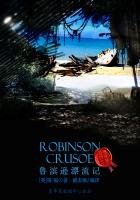如今正是六月天,夜晚此起彼伏的都是山虫鸣叫。远处草堆里好像有什么动物跑过,不时发出“沙沙沙”的骚动声。
龙五陪着谭阿婆已经走了大约半个时辰,门外留着一支火把,倒映进来的火光摇曳不定,防止野兽靠近。
曾陵昏昏沉沉的,但一直悬着心,所以睡不踏实。
又过了片刻,外面果然起风了。
不知为何,曾陵依稀觉得哪里隐约传来一阵哭声,像是一群年轻女子围拢着凄切地抽泣,哭声随着那风起起落落,时隐时现。但再竖起耳朵细听,好像又完全不对,倒像是隔着山传来一些打锣吹唢的喧杂声。
她艰难地动了动,听着七妹的呼吸声,感觉七妹也没睡着,便试探地问:“七妹,阿婆他们这么晚做什么去了?”
七妹果然侧过身来,夜色中曾陵看不到七妹脸上的神情,只听得她低声回答:“龙潭西那边一个老舅爷身体不太好,他重病有一阵子了,脾气又倔,一个人住在江上,那会儿是他养的鱼鹰飞来报信。东西村但凡有人出什么事,都会找我阿婆过去的,没事,你睡吧。”
曾陵只得闭上眼,又迷迷糊糊一阵,但感觉那个时隐时现的哭声还是在屋外盘旋,而且周围越安静,那哭声就越清晰,甚至曾陵觉得那哭泣的女子正在朝泥草屋靠近。
“七妹……我听到有人在哭。你听到了吗?”曾陵终于忍不住了,又问。
“有人哭?”七妹静听了一会儿,才低声答道,“原来你也听到了,那是‘山哭’。”
“‘山哭’?”曾陵困惑不解。
“是风声,从五姊妹山传过来的。江上的风穿过山石岩缝和树木,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七妹给曾陵把薄被拉高一些,摸摸她的额头,“你还烧着。”
“五姊妹山?”曾陵不禁往七妹身边挨近一些,虽然是夏天,但山中的夜晚却有些凉意。七妹戴了草药的香囊,曾陵靠近七妹闻到一股檀香树根的气味,很像家中书桌上那块檀香根雕的味道,闻着让人想起家里,安心了好多。
“但也有人说,原本五姊妹山不会哭。很多年前,龙潭西有五姊妹,不知什么缘故,一天夜里一齐手拉着手,哭着走进了那座山,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从此每当起风,大家都能听到山上传来哭声……不仅龙潭西,就连我们龙潭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从小到大都听习惯了,没事的,睡吧。”
“哦。”曾陵点点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后半夜龙五回来,七妹起身出去跟他说话,曾陵没在意,转过脸朝里继续睡,这一觉直到第二天早上。
外间依旧是蝉鸣和鸟叫,曾陵起身出来却没看到人,只有门边放着一盆清凉的净水和一碗草药粥。曾陵心中涌起一阵感激,收拾好自己,之后便躺在门边的草垛上看天。
阳光和白云在澄澈的蓝色天际上游走,她闭上眼睛,和煦的风拂在脸上,有些昏昏欲睡。忽然不远处草丛中传来一阵“沙沙沙”的骚动,曾陵原本以为就是山鼠或鸟类,但那“沙沙”声持续不绝,还夹杂一种危险的“嘶嘶——”的声音……
曾陵倏地感到一股寒意袭上心头,猛地睁开眼,就在声音发出的方向,密扎扎的灌木中暗影攒动,无数花纹斑斓的鳞甲闪动着,一些三角状的尖尖小头,齐齐朝她所在的方位冒着鲜红的芯子,随时就要靠近过来。
是蛇!不止一条……是许多大小不一、颜色斑斓的蛇!
它们就像从山石和树丛深处逐渐聚集过来的,晃晃悠悠地竖起一截身子,最近的与曾陵相距不足五丈远,曾陵几乎能闻到空气里蛇群的腥气。
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蛇……曾陵的头脑“嗡”的一片空白,手脚僵硬,根本不记得要逃,只怔怔地定在那里,与蛇群对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很短的一小会儿,在几棵丛生的杂树背后,幽暗的阴影里,忽然又蜿蜒着冒出一颗簸箕般大的扁黑脑袋,是一只巨蛇的头!
曾陵终于倒吸入半口凉气:“蛇……”
她生平最怕蛇,偶尔在禹门坊的家中,会有一些无毒的家蛇从屋檐上游过,她都能吓得全身发软,大喊大叫飞奔着跑出很远,可现在在这陌生的野外山林小屋间,遇到这样的蛇群,她该怎么办?
曾陵下意识地撑着身子后退,但胳膊使不上力气,勉强往旁边挪动几下,整个人便重心不稳地跌伏在地。
那条巨蛇慢慢游出了树丛,所有蛇好像都是它的随众一般,自动两边让开,大蛇探出一截身子,曾陵不由喉咙里也哽住了,目测那蛇身竟有她的大腿那般粗,上面遍布幽暗五色的粗大鳞片,巨蛇伸长脖子的时候,它脖颈上一段的鳞还会片片膨胀起来——
“救……救命……”
那巨蛇已经转眼游到她脚边,还冲她脚底吐出蛇芯。曾陵忽地想起小时候,乐婶吓唬她说,蛇吐的芯子尖尖的,就像锥子一样,能在人不注意的时候,把人的脚底刺出一个血孔,脚底的血一流就不止,蛇就在那孔上不停吸血,直到人的血被它吸干。
曾陵想把脚往回收,但全身抖得跟筛糠一样,根本动弹不得,直到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锐拉长的呼哨:“呜——嘘——”
紧接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曾陵没来得及回头去看,龙五已经一个箭步蹿到她身边,一边伸手搀住她,一边嘴唇翕动几下,朝蛇群又发出一些高低短促的哨声。
那巨蛇立刻停止了靠近,瞪着一双金黄黑瞳的大眼,整个蛇身陡然向后缩起一段,对俩人端详片刻,蛇芯“嘶嘶”几下,龙五咬唇也发出极低的“嘶嘶”两声,那蛇就迅速往后退去。它身后的那些大小蛇群也自动有序转身钻回草丛里,随着来时一样的“沙沙”声响消失不见了。
曾陵的牙齿还止不住地打战,倒抽几口气,慢慢抬起头望向龙五。这个人脸上淡定,只是用沉着的目光望着离去的蛇群,他肩上还背着一个背篓,篓子里装满一些草木和带着串串紫黑色果子的树枝,像是采药去了。
确定蛇群完全离去,他才低头想把她扶起来。
曾陵目睹蛇群在龙五的驱使下消失,她本能地对这人也产生极大的畏惧。看到龙五向自己伸手,她下意识躲开。
龙五的手伸到半空便停住,注意到曾陵的戒备和疏离,便不动声色地收回,将满载的背篓放到泥草屋门旁,然后自去收拾她撞倒的几捆禾秆草。
曾陵瞪着眼睛一直盯着龙五,看他默默劳作的身影,这几日心中一直压抑的那股哀戚和懊恼突然释放出来,“你刚去哪儿了?怎么会有那么多蛇……”话没说完,触及心中的痛处,连带着这两天对这个陌生境地的提心吊胆,她止不住哽咽起来,眼泪珠串子般往下掉,“你上哪儿去了,我怕……”
龙五没料到她会忽然哭起来,怔怔地看着她,明显不擅长应对这种场面,半晌只能拿洗净的碗又盛了碗水过来,俯身在她身旁,想了想才道:“义爹捡到我时,我身边就绕着蛇,义爹也会吹笛引蛇……这方圆十里的蛇都会听从他的召唤……我已经让它们走了,你有伤到哪儿吗?”
曾陵哭得胸口很痛,只得抽抽噎噎地慢慢止住,两眼红肿地望向龙五,看他有些局促地递过水碗来。曾陵咬了咬下唇接过来,但想想还是觉得不对:“那些蛇……是你和你义爹养的?”
“不是。”龙五摇摇头,抬起一边胳膊给曾陵看,只是普通的少年人肤色,没有山里人的黧黑,“我义爹说我出生时,可能浸过一种瑶家秘炼的药水,所以蛇从不咬我,只是因为药水有些特殊的味道,方圆一带的蛇都会被这种味道引来,包括我住的地方。”说到这儿,他示意一下泥草屋及四周,“它们常会来这儿盘桓,还好义爹会吹哨驱蛇,他也教了我驱蛇的方法。”
“有味道?”曾陵好奇地抓住龙五的胳膊闻了闻,“没什么味道啊?”
这个举动做完,曾陵才蓦然后知后觉有点儿窘,龙五倒没什么,只是看她神情缓和,也就放心转而去收拾他那个背篓。
曾陵看着他把几块木薯、不同的草药拿出来,分别摊放在那儿,然后又拿那盛了水的碗,将几束连枝砍下来的黑果灌木上的小黑果浸入碗中,足有半碗多,转身递到曾陵面前。
“这是?”曾陵有些惊讶。
“这是龙葵的果子,也是散瘀消肿的药,叶子要做熟,不然有毒,果可以生吃。”龙五说到这儿,停了停,才加一句道,“我刚才去了一趟五姊妹山。”
“哦……”曾陵愣了一会儿,等龙五去生火做饭,她才想起自己刚才问过龙五去了哪里。
龙五将木薯用一种大叶子包裹,放到火边的热炭灰中煨下,然后将龙葵的嫩叶摘下煮煮,用树枝削的筷子夹起来,挤掉水再撒几粒粗盐揉均匀,最后从门里的墙上解下一段竹筒,里面倒出一点儿炒米,拿煮滚的开水泡下,搅拌有盐味的龙葵叶子,这样盛一碗递给曾陵。
看着没有半点儿油花的野菜泡炒米,曾陵忍不住又要落下泪来。自从她醒来,每顿饭食再清淡,龙五都要拿白米招待她,这已是天大的恩情。曾陵素来听说过,许多的山里人生活清苦,家里帮佣的乐婶就是山地村里出身的女人,在曾家十几年来,打理厨房灶下的活计时,老菜梗子向来不舍得扔,晒干了切碎再做小菜或烧菜干粥。
胳膊还疼,曾陵怕把炒米再翻洒了,身子挨着禾秆草垛子,双手借着力挪过碗来喝几口。龙葵的叶子不苦涩,倒有股野菜的清香,加上有咸味,十分适口。
吃完午饭,龙五便坐到一旁搓麻绳,曾陵想起来便问:“五姊妹山……远吗?你是专门去采药的?”
龙五摇摇头,似乎思忖了一下,才告诉她:“不太远,不是去采药的,这里人都不上那山。”
“为什么不上那山?因为那山会哭?”曾陵想起昨晚的经历。
龙五摇摇头:“山上有山姥。”
“山姥是什么?”曾陵更不明白了。
龙五却还是摇摇头,不说话了。
此后的几天,每到傍晚时分,七妹都会按时过来给曾陵换药并陪她过夜,而龙五有时会睡在附近的树上,但更多时候是没入灌木之间不见人影,行迹让人捉摸不定。
曾陵也看得出来,龙五和七妹应该当她是不相干的外人,所以不太跟她说太多本地的事。但是他们照顾了自己这么久,曾陵有些过意不去,有次想拿几两碎银子交给七妹,当作被照顾疗伤的报酬,但七妹坚决拒绝了,只说她阿婆叮嘱过,曾陵是得龙五太子保佑的贵人,她和五哥要好好照顾。
也许是七妹家的药效好,曾陵的伤势在迅速好转。
谭阿婆没有再过来,曾陵想她毕竟年纪大了,山林间行走多有不便,但有一次问起,七妹却说,阿婆最近常去看望龙潭西病重的那位老舅爷。老舅爷是谭阿婆的小表弟,七十多了,身体病得极重,那天夜里大家原本以为他扛不过去的,老舅爷的亲生儿子就叫上村里其他亲族后生,连夜将事先预备的棺木都抬出来,没想到天明左右,老舅爷又硬是睁开眼,就是不肯松那口气。
那晚的五姊妹山也哭了一夜。
后来谭阿婆见天亮了,到床边端详了老舅爷一会儿,之后喃喃自语地闭目念了些什么,又让人快去熬米汤来喂,说她这老表弟还有心事没了,舍不得上路。喝完米汤后,老舅爷的病果真逐渐缓和起来。
每次七妹都陪着谭阿婆去老舅爷家,老舅爷独自住在西村的一座江水中搭起的吊脚楼里,吊脚楼距水底足有两丈深,离岸更有数十丈远,每回从他的吊脚楼出入,都得撑个小竹筏,很麻烦。老舅爷从年轻的时候就这儿住下了,据说当时他的独生儿子才两三岁大,他媳妇儿就天天抱着娃娃在江边哭,但老舅爷铁了心不回去,不管怎么追问,他也不肯解释。村里人只看他每天沉默不响地撒网捕鱼赚钱,家中妻小有事也会回家帮忙,但绝不肯留家过夜,忙完事情就回自己的吊脚楼去。
东西两村的人,大家表面上不说破,但实际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讲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曾陵清醒之后,在泥草屋睡的第八天。
外面日薄西山,最后一点儿残阳挂在树影背后,泥草屋四周都是虫鸣,屋里七妹刚给她换完药,便将松明火把移出门外,泥草屋内迅速暗下来。
龙五在外面窸窸窣窣收拾着什么,道了句:“今夜可能起风,后半夜有雨,我到处看看。”
“老舅爷是怎么回事?”曾陵盯着七妹的身影追问。
七妹这几日与曾陵在一起也熟络多了,回来坐在她身边,伸手把她脸颊上一些碎发拂开:“陵姐姐,你说过,你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对吗?你的爹娘,也不会因为你是个女娃儿就嫌弃你?”
“嗯。”曾陵点点头。
七妹轻轻叹了口气:“在我们这里,若生了男孩儿,就会以姜酒供奉祖先,即便家中再穷,也会去买点儿甘蔗糖加到醋里,煮酸甜的姜片四处馈赠,所以只要收到谁家的姜酒或姜糖醋,就知道这家人生了男孩儿。而生了女孩儿,就无声无息的,家里人也不会当一件好事出去传扬。”
曾陵点点头,这重男轻女的习俗由来已久,她自然明白。
七妹散开自己的头发,两个人躺下来,她给曾陵掖好被角才又道:“这些是我们自家人的事,本来也不好跟你说太多,也怕你听了害怕……那五姊妹山,据说过去不叫这个名字,后来之所以改叫这个,跟老舅爷有直接的联系。听我阿婆和村里其他老人说,那座山过去叫‘山姥山’或者‘姥姥山’,每当起风时,山中就会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据说那是一个失去了五个孩子的女人,关于她是谁,老一辈人都说不清。有说是一个进山砍柴的苦命女人,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她怕孩子乱跑就用绳子把孩子们绑在一棵大树下,谁知等她砍完柴回来,五个孩子都已经被老虎叼走了,地上只剩下断掉的绳子和老虎的脚印……还有人说那个女人就是一只母老虎,她生出五只老虎崽没多久,一次离开窝去找吃的,有猎人发现了那窝虎崽,不仅把五只虎崽砍死,还把五个虎头割下来,支在窝旁的五根树枝上。母老虎回来时,起初以为虎崽顽皮,爬到树上朝她摇头晃脑,直到走近才看清,那猎人在旁边伺机跳出来也想把母老虎砍死,但母老虎马上对猎人回击,猎人逃走跌下山崖……从此母老虎成了一只疯虎,本地人都称她为山姥。曾经有人为了平息山姥的怒火,筹集了些钱到山上盖了一座山姥庙,但我们东西村里的人,轻易是绝不上那山的,尤其是小孩子,小时候爹娘就会吓唬说,再哭山姥就会来抓你回去做崽了。”
“哦……”曾陵听得入神,冷不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被吓了一跳。随即一个陌生的男孩声音大喊道:“五哥!五哥!”
七妹一听,马上起身披衣出去:“懵仔?五哥不在,这里只有我和小姐姐。”
那男孩心急火燎地跺脚:“五哥去哪儿了?老舅娘不见了!”
七妹奇怪道:“五哥的行踪我哪知道呢。老舅娘不见了?她那么大年纪又眼睛不好、腿脚不方便的,还能一个人跑哪儿去?”
懵仔急得直转圈:“西村的憨崽说,天黑之前曾远远看见老舅娘一个人在田埂上头走,去的是五姊妹山的方向。现在两村的人都在找,但是要上五姊妹山的话,他们都想叫上五哥。”
“啊?那我阿婆呢?她怎么说?”七妹也急了。
“谭阿婆在村口,大家都在等她拿主意,阿婆叫我来喊五哥。”懵仔又跺了一圈脚,“去哪儿找五哥呢?”
曾陵也扶着墙出来,七妹回头看她,连忙过来搀住:“是西村的老舅娘不见了,我去村子里看看,过一会儿就回来,你自己先睡。”
“哦……”曾陵也不好说什么,七妹拉她回屋里躺下,又习惯性地摸摸她前额,看着她的眼睛低声嘱咐说,“万一五哥回来,你记得告诉他去村口找我们。这里不会有旁人来的,你不用怕,也别乱跑啊。”
“嗯。”曾陵答应着,七妹就跟懵仔走了。
四周安静下来,剩下她一个人。
七妹走后,曾陵就睡不着了。屋外一阵阵晚风吹送,引起窸窸窣窣的灌木林动,还有一些此起彼伏的远近虫鸣,越听就越觉得热闹。
后来……那山姥山又是怎么变成了五姊妹山的呢?
而且,刚才那个故事还没说完呢,为什么说山姥山变五姊妹山,是跟西村的老舅爷有直接的关联?而山上那个失去了五个孩子的女人,或者那个失去了五只虎崽的母老虎,都好可怜……阿娘找不到自己肯定也很难过,会不会也疯了一样到处找自己?
曾陵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脑中一时是阿娘担忧的面容,一时是阿爹卧病在床的样子,一时又是五只小老虎被割下小脑袋,支在五根树枝上晃动,再就是风雨飘摇中,卢香狞笑着将她一把推下水——
“沙拉、沙拉——”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外面的风越刮越大了。远远的山道那边,草中仿佛有脚步碾压的声响,也许是风,又或许是夜行的动物。
曾陵安慰自己,不要因为七妹不在就疑神疑鬼,七妹说过这里没有人会来的。她闭上眼睛屏息静气,想尽量让自己平静入睡,但耳朵还是不由得关注着外面的动静。
“沙拉、沙拉”的声音,确实夹杂在“吁吁”的风声中。
好像真的有脚步声,只是隐在风中不太清晰,仿佛是往泥草屋慢慢靠近,只是有些忌惮似的,走走停停。
曾陵陡然睁开眼,是龙五回来了?但他……不会这样走路。
门外燃烧的火把在风中摇曳不定,曾陵撑起身子,贴在墙下的阴影里,轻轻挪到柴门边,从缝隙往外张望,但只能看到不远处一些舞动的杂草。
曾陵等了一会儿,好像是没有异样,真是自己疑神疑鬼闹的啊。
但随即下一刻,远处灌木丛发出“沙沙沙”一串急切的骚动声,她看到一团人形从草中倏地跳出,落地后,再往屋子所在方向一连几个翻滚,发出女声的尖叫:“救命!”
紧接着,从她蹿出的灌木丛中,猛地耸立起一段水桶般粗大的黑影,借由火光,曾陵看清那是一截泛着暗光的鳞甲身躯,还有那簸箕大的扁黑脑袋,是曾经见过的那条大蛇无疑!
“啊!”滚地的人一边手忙脚乱朝泥草屋爬来,一边回头望向大蛇。
曾陵脚底一软,但好歹不是第一次见这蛇,怔了怔就回过神,连忙把柴门用力推开,冲那人招手:“快……这里,快进来!”
那个人也很机敏,听见曾陵的叫声,立刻转头就扑过来,用力过猛还撞到她身上,两人一同滚进门内。
“嘶——疼——”曾陵被对方撞倒后仰在地,还好那人一手撑着门边,没有整个人都压在她身上。
“抱、抱歉。”身上的人慌乱中忙不迭道歉,并飞快起身,把柴门一把推上。
曾陵没敢轻举妄动,还好只是后背磕在地上,胸口没有什么异样,应该没触及伤处。眼前的人是个十来岁的女孩,个子瘦瘦小小,跟七妹一样穿着大襟蓝干衣,长发打成几股粗辫又用木簪盘在头顶,眉眼透着伶俐的英气,只是脸蛋和额头有一道道黄黄黑黑的污痕。
“你怎么样?”女孩关好门就回头扶起曾陵,两人又挨在柴门缝隙往外看,那大蛇没有再靠近,而是盘着身躯在灌木丛中游走几下,很快又隐没到黑暗中。
女孩终于舒一口气,脱力地靠在墙上:“唉,真吓死我了。”
“你……是谁?”曾陵不无戒备地道。
女孩大喘几口气,才冲曾陵一笑:“我?我是龙潭西村的,大家都叫我五妹。”
曾陵皱眉:“那你……”
“我来找你的,我听人说,他们在这里关着个外人,还是个姑娘。”
“关……着?”曾陵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嗯,是啊。”五妹点头,还凑近些细看曾陵的表情,“你不信?那他们是怎么哄你的?你受伤了,只是让你在这儿疗伤?不图你钱,也不图你别的,还给你吃的和草药?晚上专门让一个人来陪你睡?周边还有那些蛇群看守?”
“你……”曾陵被她连珠炮似的提问弄得瞠目结舌。
说到这儿,五妹忽然又叹一口气:“你也听他们提过吧?我们西村有个老头儿快死了。”
曾陵听惯了七妹叫“老舅爷”,乍一听五妹说“老头儿”,愣了愣才点头:“嗯。”
“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习俗,老人死了,多是送到江中水葬,而且每三年要把一个姑娘装进桶棺推到江里,说是送给龙五太子做媳妇……你在这屋子住了那么多天,应该见过那个男的吧,我听说过他的来历,跟当年的江神龙母娘娘一样,包着襁褓那么大时就睡在盆里,从上游江水漂过来的,村子里的老人就说他必是龙五太子的化身。喏,外面那些蛇都是他养的,也是奇怪,这一带山里、水里的蛇都听他使唤……而且每隔三年,到时间了,他还自己亲手打造一只桶棺,就是为了给江里的龙五太子装新娘子呢,你这些天没看见?”
五妹的一席话让曾陵魂飞魄散,整个人僵在那里,嘴巴抖了抖却说不出话。
五妹转而又去门缝上看了一会儿,说:“欸?那大蛇走了吧?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先见之明的,来之前,我在村里偷了几只小母鸡,刚才在山道上,我每隔一段就把一只鸡割断脖子,让那鸡带着血到处洒,今天刮的是顺风,那些大虫肯定能闻到鸡血的味道,这会儿应该去追鸡了。你可谢谢我吧!”
“谢……你?”曾陵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嗯,我来带你逃的。”五妹理所当然地一点头。
“为、为……什么?你不是西村的人?”曾陵结结巴巴地,话还没说完,五妹就撇嘴打断她话头,“哎!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我也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就问一句,你是愿意在这儿等着,等到后半夜,他们把你装桶里投江,还是愿意活着逃走?”
“当、当然要活着……我、我还要去找我爹娘!”曾陵咬唇坚定地道。
“那不就得了。你的脚怎么样?能走吗?再晚了我怕他们回来了。”五妹起身向外张望。
外面的风好像暂时平息了些,大蛇真的不见了踪影,只有几条小蛇在草丛间游动,不足以构成威胁。
五妹催曾陵快些穿好衣裳,就带着她蹑手蹑脚出了门。她们没有带火把,反正五妹是本地人,路熟得很,而且带着火光很容易被人发现。万一那些人追来,只管藏到林子里就好。曾陵便由五妹牵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深草涧间的山道。
山涧刮着迂回的风,有些地方的野草与人齐高。
五妹一手牵着她,一手不断拨草前行,倒是走得很顺畅。曾陵走不惯这山路,好几次都踩空滑倒,胳膊和脚踝上的伤又在作疼。五妹索性将她一条手臂搭在自己肩上:“来,靠着我。”
五妹分明比自己还矮半个头,曾陵又感动又惭愧,咬咬牙点头,继续迈开脚步,一瘸一拐地再转过两个山弯,就听到脑后“嗖嗖”的风变了声响。五妹陡然警惕起来侧耳听了听:“不好,追来了!”
“什、什么追来了?”曾陵吓得不轻。
“快走!”五妹半拖半拽着曾陵,突然加快脚步。
前面黑黢黢的一片茂密林地,曾陵闻到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酸腐味,紧接着风声更急,好像夹杂着许多“嘶嘶”声,曾陵想到七妹他们提过的龙涡塘和桑林,兴许就是到跟前了,这种沼泽地怕是最多蛇的,她刚想提醒一句,五妹就在她身前蹲下身:“你到我背上!”
“那怎么行?我比你沉!”曾陵吓了一跳。
“别废话了,赶紧上来!”五妹彻底不再耐烦,喉咙里发出咆哮般的低吼。
曾陵还是不敢往她身上趴,正纠结着,五妹却不由分说,双手后背扣住她双腿,一拱背,将曾陵硬是托起来。
“啊!不行,放我下来!”曾陵吓坏了,怕五妹走不了几步,脱力摔跤,却没想到五妹的双手如铁钳般,紧紧制住她的臀部,挺身就朝前疾走。
“唰唰唰”的风和草在四周摩擦而过,不时有树枝草叶扇在脸上,曾陵什么都看不清,只觉得五妹背着她一通左穿右拐,终于在一个地方猛地纵身一跃,睁开眼时前方居然就是一片开阔的田野。
月光淡淡地铺洒在天地之间,远处有群山的轮廓,稍近的一片黑暗中又有几星灯火,也许是东村或西村?曾陵十分惊讶,想再看仔细些,左眼却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
“嘶!”她疼得一把捂住半边脸,可能是风太大,沙尘撞迷了眼睛,所以忽然发作?曾陵想叫五妹跑慢点,可一张嘴,口中就灌风,这田埂上的道路平整,五妹跑得好像更快了许多。曾陵一手死死勾着五妹的脖子,一手捂住眼睛大喊:“放我下来……五、五妹……它们没追了,放我下来!”
但五妹却丝毫没有听到,脚底依旧“噌噌噌”地大步往前蹿,曾陵咬牙忍住左眼的疼痛,摇晃她的肩膀:“你听到没?快放我下来!”
山道时而弯曲、时而高低,两人很快又没入一片丛林,曾陵被许多树枝“噼里啪啦”地拍打在脸上,疼得双手抱头护脸,这时她终于觉出不对劲儿来。五妹的身形是典型的山里妹子的清瘦娇小,但背着自己却跑得“呼呼”生风,山里长大的姑娘再强壮有力,这奔跑速度也超出常理……何况,曾陵挣扎的时候发现,那箍住她臀部的双臂,也在迅速地变得越来越硬,甚至好像生出些藤蔓般的网状物,裹束着她的腰身不断收紧。她伸手去摸,立刻就被一根藤束缚住手掌,并牢牢缚在身后缩不回来。
“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曾陵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吓疯了一样拼命蹬腿,慌乱中,剩下一只手一把拔出五妹脑后那根发簪,攥住发簪往五妹背上刺下去。
木簪不算尖锐,但簪头没入肩背皮肉的瞬间,五妹猛地发出一声类似兽类的咆哮,继而整个身体前扑,伏在地面四脚着地继续往前飞奔。
而她散落的发辫,随即变成有生命的蛇一般,尽数往曾陵身上缠去。曾陵拿簪子的手也被缠住,簪子脱手,一段发辫还游上她的脖子,无论曾陵如何挣扎都是徒劳,情急之下她往五妹的后颈张口用力一咬——
“吼——”五妹仰头发出一声怒兽的大吼,继而甩动头颅,曾陵被晃得重重撞到树干上,一阵头晕眼花后不得不松了口,整个人贴在五妹背上。
五妹随即不再停顿,手脚并用,连续几番纵跃,终于再次蹿出了那片茂密的丛林。
“锵锵锵锵……”
模模糊糊间,曾陵听见远方传来无数金属铙钹的敲击声,其中还夹杂了一些“喔喔喔”的人群叫喊,很像住在江畔的人们敲锣打鼓驱逐邪祟的声势。
曾陵借着朦胧的月光,感觉到前方黑幕般的山影重重,而五妹的行径完全不像个正常的人,倒更像是只兽,而她要带自己去的地方,肯定十分危险!
一想到这儿,曾陵咬牙再次努起一股劲儿,伸手用胳膊箍住五妹的脖子,用力往自己的方向掰,再次冲她喊:“你松开我!”
然而五妹的散发也迅速地缠上来,曾陵的脖子被勒得喘不上气,只有手在混乱间抓到五妹的耳朵,扯住就朝自己的方向拽。这个动作估计也彻底激怒了五妹,她的头顺势扭转回来,面容对上曾陵,女子的五官纠结起来,尤其那双眼睛,眼皮子一抖,翻出两只煞白的眼珠,张开的嘴巴内黢黑如洞,对着曾陵发出一声威慑的大吼——
曾陵只觉黑气扑面而来,也就在这时候,前方近在咫尺的大山方向,整面山峦也刮起波涛般的狂风,千万茂密的林木“哗哗哗”地冲山下摇摆下来。
五妹抬头望向大山,仿佛受到某种召唤,她再次仰头吼出兽类的咆哮,但就在她略有停滞的这个瞬间,她们身后也刮来另一股气流,五妹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弓起背,双肩耸立起来,随即一个倒翻弹跳到半空。曾陵听见金属的破空声,紧接着她身上束缚的树藤一松,人与五妹分开,昏头转向地滚落到地面草丛里。
曾陵挣扎爬起,身上有几段断掉的木藤,还有脖子上的几束散发,她一边撕扯一边止不住咳嗽干呕,五妹早已蹿上旁边一处茂密的树冠,只探出脸来,冲一个方向龇牙咧嘴。曾陵狼狈地回头,借着月色,看到身后数丈远的枝叶间,一条鳞甲泛着褐金色光泽的巨蛇从树丛之间冒出来,与此同时,一个人影也迅疾地从黑暗中一跃而出,再稳稳地收势立在那儿,正是龙五。
而一把柴刀则嵌入两人前方的一棵大树干上。
“嗷——”
五妹像一只暴怒的猫一样,朝龙五拼命咧嘴龇着牙,曾陵才发现,她的脸孔已经不是先前那样正常的人面,她额头和脸颊上那一道道黄黑痕迹,也不是污痕,而是一些黄黑的杂毛,口角更有对称的森白尖牙露出,那模样……就像一只老虎!
“嘶嘶——”褐金色大蟒吐着芯子,慢悠悠地盘起身子停在龙五身后,这条大蟒比泥草屋边出现的那条还要粗大一圈,曾陵惊骇得双目圆瞪僵在那儿。
“吼——”五妹冲龙五发出野兽般威胁的咆哮。
龙五手中没有武器,他看了一眼曾陵,表情十分冷漠,冷硬的线条让他看上去更显疏远。
风呼呼地在空中相撞,龙五再望向五妹的时候,微抬下巴,目光似有挑衅之意。五妹的目光在龙五和曾陵之间来回审视,前身压低,做出前扑的姿势,像是在算计如何避开龙五再次抓住曾陵这只猎物。而龙五这边,大蛇也机警地缩起身子,只要五妹有行动,它会迅捷地出头袭击,双方一时陷入僵局之中。
突然,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一声拖长的呼喊:“大姊!二姊!……五妹啊……呜呜呜,阿女啊!”
声音是从山的方向传来,明显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妇发出的,虽然说的是山里土话,但曾陵听得分明,像是一位正在寻找失散孩儿的悲恸母亲,满腹无助哭腔,声嘶力竭。
“吼——”五妹登时循声掉转头去,眼神中竟溢满怨毒,老妇好像也听到这边的动静,就听她喊着“五妹”一路渐行渐近。
五妹却又忌惮地立起前身,再看一眼曾陵,仿佛权衡一下,忽然纵身跃入数丈开外的山坳树丛,随着“沙沙沙”的灌木骚动声,身影瞬间消失在夜色之中。
“锵锵锵锵……”
这样闹过一场,背后那阵铙钹敲打声也越来越清晰了。
龙五伸出掐诀的手指放在嘴边,吹出尖锐的呼哨,那褐金大蟒也垂头退隐回黑暗之中。
曾陵张着嘴愣怔在那儿,背脊冒出层层虚汗,倒抽几口冷气,也不知自己待在这儿多久。直到有人轻拍她脸,她才完全醒悟过来,看向身边的人,正是皱眉关切的七妹,她身后还有懵仔等几个拿着铜铙钹和火把的中青年汉子。
“啊?”曾陵本能惊得想往旁躲开。不远处围拢的人群却在这时分开,就见两个后生从山路之间扶着一位颤巍巍的老妇人走来,老妇十分虚弱,步履更是艰难,但即便这样她还是不时回头望向身后大山,干涸的嘴唇发着抖,留恋不舍般反复嘀咕着什么。
人群中微微骚动起来,有人唏嘘地摇头,有人低声抱怨,七妹起身走去搀住老妇人,一手按住她手腕的脉门像是诊视,一边又在她身上搜摸几下,像是确认有没有受伤。末了七妹松一口气,才用温和的口气说了几句土话,老妇却好像没听到一样,还不住回头去看。
七妹扶着老妇走过曾陵面前,与老妇目光一触上,曾陵打了个冷战。懵仔俯身背起老妇人,和其他几个执火把的后生一道,朝山道下方村子的方向走去。
其他几个人迟疑着,用探究或困惑的眼神看向曾陵,七妹再过来搀扶曾陵:“陵姐姐,你还能走吗?咱一起送老舅娘回家吧。陵姐姐?”
七妹叫第三遍时,曾陵才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把目光转回七妹身上,但曾陵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牙齿上下碰撞止不住咯咯地响,突然她一把用力推开七妹的手:“她……她、她是谁?”
七妹被推得往后一趔趄,但她没生气,而是细看曾陵的神情,抿了抿唇,与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龙五对视一眼,试探地问曾陵:“是不是……刚才那虎伥跟你说了什么?”
“虎……伥?”曾陵不知道什么是虎伥,但从七妹的表情来看,她知道指的是五妹。
七妹点点头,再次向她伸出手:“咱去老舅娘家……我给你慢慢说。”
曾陵全身发寒发虚,脚软得根本站不住,龙五俯下身让曾陵伏到自己背上,由他背着下山。
龙潭西村位于一片种着玉米和粉葛庄稼物的山坳里,而老舅娘的家,是一栋几乎隐没在木薯地里的破败吊脚小楼。
夏季昼长夜短,现在也不知是什么时辰了,天角边的山巅好像升起一层薄雾。龙五把曾陵背到吊脚楼前,曾陵看见好几位老年的村妇,围拢着谭阿婆坐在楼前的篝火边,还有一个拄着拐杖、只有一条腿的中年老大叔在一旁抽着旱烟袋。懵仔背回老舅娘,那大叔把烟袋在凳脚磕磕,慢腾腾又面无表情地迎上来,搀住老舅娘往篝火边挪。
其他几个村妇则拉着老舅娘在阿婆身边坐下,用土话劝解着什么,老舅娘却忽然激动起来,挥手反驳几句,火光映照在她枯树皮一样的脸上,显出执拗与狰狞的神情。
龙五刚把曾陵放到旁边一棵大榕树下,老舅娘一转头看见曾陵,突然就指着曾陵说:“我明明听见的!你也看见我家五妹了,对不对?”
曾陵满脸错愕,还没反应过来,老舅娘就脚步不稳地几乎扑倒在她面前。曾陵下意识抬手扶她,才发现老人连鞋都没穿,赤裸的脚掌走得泥污带血。
“你说啊,你看见我家五妹了,对不对?我家五妹还有大姊、二姊、三姊……”老人泪流满面,干槁的双手死死扳住曾陵的双臂,“她们恨我的,我这个做阿娘的对不起她们,所以她们不肯见我,无论我怎么上山去找她们……你说啊,你见到的是不是五妹?”
曾陵瞠目结舌,只能点点头。
那瘸腿老大叔突然气愤地拍案而起:“阿娘!您不要再提她们了,她们为虎作伥那么多年,早就没有人性,而且狡猾多端。加上今晚,她们已经拐过多少人了,多少人因为她们而死啊,娘!”
“你闭嘴!她们……她们都是你的亲阿姊……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就想、就想……”老舅娘被瘸腿大叔说中心事,顿时悲恸地坐到地上。
曾陵不知如何是好,求助地望向七妹,七妹赶紧过来把她拉起,谭阿婆也由人扶着走过来,她面目严肃地剜了那瘸腿大叔一眼:“阿丰,扶你阿娘回去,把煮的安神水给她喝一碗。”
“是。”老大叔不敢违逆,旁边后生帮着他一起去扶老舅娘,半哄半抬地把人带进吊脚楼。
谭阿婆的视线转回曾陵身上,原本沟壑纵横的脸上,眉头皱得更深:“你们几个,跟我回家。”
刚刚一路的跌打碰撞,让曾陵全身伤痕累累。龙五背她到谭阿婆家后,就被打发和七妹去屋外做饭,阿婆让曾陵坐在屋内的藤编垫子上,一一检视过她的身体,发现只有些皮外伤,并不严重。只是曾陵的脸色青白,谭阿婆端详片刻,又去拿出一个旧铁罐,抓出许多切碎的干草药,扔进屋内一摊常年不灭的小火堆内,空气中冉冉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曾陵被药气笼罩着,闻了几下就开始恶心作呕,紧接着吐出不少酸水,其中还夹杂少量黄黑色的兽毛。
曾陵惊骇,谭阿婆又用手指在她心口几处按压,居然从她皮肤上拔出几根同样色泽的兽毛,毛端没进肉里,曾陵之前都毫无知觉。
“这是?”
“是虎伥留在你身上的记号。”
曾陵还想再问什么,阿婆却摆手说自己一宿未睡,实在年老体乏了,嘱咐曾陵多喝些竹叶水,有什么想知道的,问她曾孙女七妹,说完就踩着竹台阶,嘎吱嘎吱地上楼去了。
曾陵愣怔在那儿许久,心绪混乱如麻,自己根本无法看懂眼前的困境。她依稀记得小时候听乐婶说过,伥是一种山河江水里都有可能出现的鬼怪,因为意外横死而不得超生,只能不断地把无辜的人害死。但她很难将昨晚说话脆生生的五妹和伥联系在一起……还有五妹说的,龙潭村这些人不怀好意,龙五更是做桶棺想把自己送给龙五太子做媳妇儿,自己……又该信谁的?
七妹端着饭菜出现在门口时,她如惊弓之鸟般抬起头,恰好与跟在七妹身后的龙五目光相撞,龙五的眼神照旧澄澈安定,她却吓得全身往后缩了缩。
七妹看在眼里,朝她一笑,走过来把热饭菜摆下,然后双腿一盘坐下来:“陵姐姐,你别怕,先吃饭,吃完了有什么都尽管问,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绝无虚言。”
而龙五,被曾陵看那一眼,就收住脚步,一言不发转身出去了。
七妹把筷子塞入她手中:“陵姐姐,你别怕五哥,五哥是个好人。”
曾陵看她说得语态坦然,就试探着问:“那你给我说说那虎伥是怎么回事吧?……还有,五哥到底是你们村的什么人?他做那桶棺是做什么用的?”
七妹又把粥碗放她手里:“昨晚我给你说的山姥故事,还没完呢,你问五哥做的桶棺?那是给老舅娘的。”
“老舅娘?”
“嗯。”七妹苦笑了笑,拿过筷子给她碗里夹腊肉和蘑菇,“我曾经对你讲过,在我们乡下人家,身为女儿,或嫁人后生不出男孩的女人,都有些说不出的苦。当年……据说老舅娘嫁给老舅爷后,一连生了五个女儿,老舅爷很不高兴。几十年前,那时五姊妹山还叫山姥山,大家说的山姥就是山中的山神,也是那位失去了五个孩子的母亲,或者那头死了五只虎崽的母老虎。每当起风的时候,方圆数里的人都能听到大山飘出的哭声,大家都说是山姥又在哭五个孩子了。不过也有人说,山姥很灵验,你向她许愿的时候,只要你允诺的祭品够丰厚,能称山姥的心,她就会很快满足你的愿望……不过山姥白天是见不到的,只有在黄昏后上山,走到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一个洞口有歪脖子大树的山洞,然后在洞口跪下,大声说出你的愿望和你能给出交换的祭品,山姥如果觉得满意,就会现身跟你说话……”
曾陵慢慢吃着粥,听到这儿也明白了:“老舅爷去向山姥许愿了?”
“是啊。”七妹点点头,“他向山姥许诺,用他的五个亲生女儿去换一个儿子,他是瞒着妻子和女儿独自一个人去的。起初他也没跟家里人说,直到一次,最小的五妹失手打碎一只饭碗,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件事说出来。五个女儿都哭了,当时五妹还不到十岁,后来再发生什么事,村子里的人也不太知道。只是有人看见,那天太阳逐渐落下的时候,五个女孩儿手拉着手,一路流着泪、哼着歌儿走上了山姥山,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
“那后来呢?”曾陵想起昨夜看见老舅娘的情形。
“从那以后,每当风起时,山姥山的哭声就变成了几个女孩儿的哭声,就像你之前听到的那样。”
“五个女儿……”曾陵想起先前老舅娘的情状,“所以她上山去是想找五妹她们吗?但五妹好像并不想见她,而且五妹……到底变成了什么?”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五妹,据说见过的人都会死——”
曾陵听完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七妹连忙拉住她的手解释道:“我说错了,只是听说的,你别往心里去……村子里的人说老舅爷家的那五个女孩儿成了山姥的伥鬼,填补了山姥心目中五个崽的空缺,山姥对她们不错,所以她们这么多年心甘情愿为虎作伥。传说,她们半夜到官道上诱骗路过的旅人,把他们带到山上给山姥吃掉,只是她们一直都避开龙潭村的人,所以村子里的人一直听闻,却没有见过她们……而老舅娘,在五个女儿上山后,到山上找过,但怎么都找不着,村子里的人怕她有什么意外,总去追着把人拽回来。后来他们真有了个儿子,但老两口都高兴不起来,老舅爷的性情也变得古怪,忽然有一天他就跑到江边,非要自己一个人在江上搭个竹楼住着,大家都说他是怕听到五姊妹山上飘来的哭声,良心上过不去。现如今他快死了,只是还有个心愿,想叫人把他抬上五姊妹山去见山姥,但是他儿子不愿意……前些天,老舅娘刚过七十岁的寿辰,他们儿子叫五哥做桶棺,老舅娘却说自己罪孽深重,不配那么干净的死法,临死前她无论如何都要到山上找到歪脖子树的山洞……她后悔没拦着女儿。她后半辈子都在找女儿,年轻那会儿,在山里头一待就好多天,儿子扔给村子里其他叔叔婶娘看着。他们儿子,十岁大那年,跟着村子的人在江边收网,被一副船锚砸下来磕断了一条腿,所以……他们一家人,各有各的怨。”
曾陵想起昨晚五妹的样子,总觉得还有很多想问的,但七妹说的已经叫人五味杂陈,连面前可口的饭菜也食不下咽,只能勉强吃完一碗粥。七妹让曾陵躺下休息,折腾一夜,大家都乏了,好好睡一觉,醒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