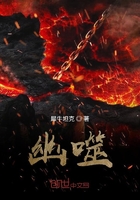我正在读弗雷德里克·普罗科斯的《亚洲人:一部小说》。我读得很出神,可是右手这页读到一半的时候,一行字突然变得弯弯曲曲。起初,我没有注意。这当然有点怪,但是我当时判断,这事儿没有多严重,充其量也就像一粒沙子掉到鞋子里硌得难受罢了。那是冬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正是待在家里看书的好时候。看得见窗外的蕨和喜马拉雅竹子。寒风揪扯着竹子,我眨了眨眼。也许风把细沙子吹到眼里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本《亚洲人》。我是在教堂里偶然发现这本书的。和平常一样,我径直向那堆书走去。乔吉特·海尔[4]、艾瑞克·范·勒斯贝德和汤姆·克兰西[5]的书混杂在一起堆在那儿。我浏览书名,突然出人意料地看见《亚洲人》和别的“伙伴们”可怜巴巴地待在一起。我觉得周围的人都想弄到这本书,便手疾眼快,拿了过来。这本书不是查托·温达斯出版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第一版,而是费伯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美观大方、价格完全可以接受的平装本。封面上印着安德烈·纪德的导语,称《亚洲人》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技艺高超令人惊讶的佳作”。而阿尔伯特·加缪[6]称赞普罗科斯是“一位表达情绪与潜在含义的艺术大师,一位呈现某种感觉的行家里手……”
普罗科斯是一位美国作家,生于一九〇八年,和我的父亲吉尔伯特·约翰·沃克同岁。人们通常管我父亲叫吉尔。父亲未必读过《亚洲人》。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也就能当个小学教员罢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老老实实坐在那儿读点儿什么。阿德莱德的《广告报》每天都会送到门上,父亲却总是站在厨房餐桌旁边随便翻翻,看上几眼。他的兴趣主要在股市上,也喜欢留意婚丧嫁娶的广告。二〇〇五年,父亲的名字也出现在报纸的讣告栏,活了几乎一个世纪。比一九八九年去世的普罗科斯晚走了许多年。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不是来自书本上的那个世界。他在南澳大利亚北部铜矿之乡巴拉长大。一九七九年,这个名字出现在《巴拉章程》上。这份文件为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巴拉和周围的村庄当然有一段与众不同的采矿史。一八四五年,这里发现了铜。世界各地的矿工、建筑工人、工程师以及各式各样的冒险者、投机家蜂拥而至。大多数矿工来自康沃尔[7]。还有一些来自威尔士[8]、苏格兰、英格兰、中国、南美洲和德国。矿山周围,一个个村庄雨后春笋般兴起:亚伯丁,雷德鲁斯,汉普顿,里维赤维尔,洛斯特威西尔和库伦加。矿山一八七七年关闭,但是鼎盛时期巴拉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铜矿之一。南澳大利亚矿业协会那些因一开始就入股而获得有利地位的股东获利颇丰。
我发现吉尔和诗人雷克斯·英格迈尔斯大约同时到巴拉小学读书。我纳闷,他认识英格迈尔斯吗?他认识。不过不是英格迈尔斯已经成为诗人和“金迪沃罗巴克运动”[9]先驱者时认识的。“金迪沃罗巴克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旨在把原住民的词汇、短语引入澳大利亚写作之中。我问父亲认不认识雷克斯·英格迈尔斯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人不无沮丧地瞥了我一眼,说:“那个家伙挺吓人,是个专门喜欢欺负小孩子的恶霸。他弄得我都不敢上学。”
母亲比父亲更喜欢读书,是我们那儿图书馆书友会的会员。她喜欢看畅销书,但是坚信,阅读影响视力,能把好端端的眼睛弄成近视眼。打网球是她为进入青春期的儿子们作出的更健康的选择。我的父母并非完全反对书本和阅读。他们不是俗不可耐的人,只是对有害身心健康的嗜好担心。多年之后,我看到一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案卷。其中一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年轻公务员因为“懒惰”被指责。监管人员的报告说,“这个小伙子花大量时间在国立图书馆读莎士比亚一类的书。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这样做委实不妥”。他甚至明确指出,读书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尽管父亲不看书,看到我的藏书越来越多还是很高兴。我的这些书是在阿德莱德的玛丽·马丁书店和作家、藏书家马克斯·哈里斯的帮助下弄到的。不管我们家情况如何,阿德莱德是一个读书氛围浓厚的城市。玛丽·马丁书店肯定有普罗科斯的书。纪德和加缪的推荐一定为他赢得读者的尊重。玛丽·马丁书店有不少好评如潮的书。还有一些关于亚洲的书。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难能可贵。玛丽·马丁深深地爱上了印度,曾经在那儿生活过几年。而普罗科斯有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写印度的。那时候,我自己的兴趣可以说还没有定型,吸引我的是书,特别是旧书。我曾经在“红十字古旧书店”看到安德鲁·尤我[10]博士写的一本关于英国棉纺织业的书。其实我对书中的内容不甚了了,可也竟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我正经八百“藏书”是从购买安德鲁·尤我一八三四年出版的两卷非常精美的皮革面著作开始的。那两本书的封面是浮雕般凸起的花卉图案。和书的内容相比,花卉图案仿佛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是第一批介绍如何建立和运行新型工厂体系的指南之一。把安德鲁·尤我这部书装在木箱子里,带到南澳大利亚的韦克菲尔德殖民者,一定梦想在这里建造工厂,而不是开荒种地或者植树造林。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买到尤我博士那几卷书之后,我已经积累了许多书。和亚洲有关的书也不断增加。说我拥有一座图书馆,未免有点夸张,不过我确实有一些难得的善本。现在书店组织越来越严密,要想淘到珍贵的版本已经难上加难。现在,似乎只有在义卖市场才有可能淘到好书,让你喜出望外。不过就连那儿卖的书,书商也会事先翻检一遍。互联网为收藏家创造了新的机会。将澳大利亚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书,比方一八九三年出版的阿尔弗雷德·迪肯[11]的《印度的灌溉》就是难得的善本。我现在还在寻找他的另外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印度的寺庙和陵墓》。现在很少有人关注迪肯对印度建筑与宗教遗址的兴趣。我还十分惊讶地发现《万岁!》这本书。那是一个亚洲人入侵的故事,一九〇八年出版。作者是一个匿名的德国人,自称“帕拉贝伦”。我把这本书的详细信息输入“谷歌”,本来没抱多大希望,可是一本装帧漂亮的书《万岁!》跃然荧屏,出现在眼前。“谷歌”还告诉我,尤我博士的《棉纺织业》奇缺,价格与我当年花的一英镑六便士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我又“谷歌”了一下《亚洲人》的不同版本和价格,包括第一版作者签名献给母亲的“豪华版”,价值四千五百美元。
二〇〇八年,回顾百年历史,有许多事情值得纪念。我父亲的诞辰虽然就在这一年,但排不到显著位置,就连普罗科斯也早已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一九〇八年,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白舰队”[12]驶入澳大利亚领海,又一次炫示了美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日益重要的意义。在澳大利亚,舰队每到一个港口,人们都欣喜若狂,登上战舰参观。“打油诗”、“顺口溜”脱口而出:
大地的力量如雄狮,
盛宴的香气随风来。
为了人类的未来,
欢迎你!美国人,热烈欢迎!
在西澳大利亚,“人民诗人”鸭跖草墨菲(笔名),用下面的诗句表达了人们的心情:
如果敌人胆敢侵略,
小伙子,我们都站在一起!
我们高举旗帜,
从露纹酒园到太平洋铁路,
世界的这一部分属于我们。
“敌人”指的是日本。“帕拉贝伦”讲了一个日本人突然袭击美国、导致了打倒白澳政策的故事。C.H.科密斯在《澳大利亚危机》一书中也谈到类似的主题,讲述了一个令人心悸的日本侵略、遭到英勇反抗的故事。我手头那本《澳大利亚危机》一九〇九年四月由沃尔特·斯科特出版公司在伦敦出版。扉页上留下我之前两位收藏者的名字。这两位先生都是爱书之人,这本书现在看起来仍然完好无损。
我们记得哪本书是从哪儿买的,记得买书时的情景。我们和它们朝夕相处,也构建了它们的历史。作为一本书,我的那本《亚洲人》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那一行莫名其妙、不停颤动的字引起我的警惕。左手那页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可是右手有一行字扭曲变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这行字中间缺了点什么,应该是印刷时出了问题。我拿起书从不同角度看,想证实这个假设。我闭上一只眼睛,那行字一下子变直。变得那么快,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被搞了个措手不及。看起来和印刷无关。
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在堪培拉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眼角膜受到损伤,眼睛出了问题。也许这次又是这个原因。那一次的经历当然很不愉快,不过最终的结果还算不错。我从堪培拉电话号码簿上随便找到一个眼科专家的名字,就去找他看病。他做了必要的检查,就说这病他能看好。他对我的高度近视还做了一番评论,说的话实际上比下面这句还尖刻:“你的眼睛糟糕透了,不是吗?”“好得足可以参军。”我对他说。他想多知道点细节,我就解释说,我曾经应征入伍到越南打仗,顺利通过了体检。我得承认,这是我自个儿的错。我一直认为,澳大利亚士兵应该人高马大,虎背熊腰,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个个都像运动健将。而我不是这副模样。我能打打网球,但是不会去攀岩,更不会一边轻蔑地大笑一边把刺刀刺进土耳其人的胸膛。所以,我一直胸有成竹,认为澳大利亚军队一定会(非常正确地)把我这种人一脚踢开。体检通过,当头一棒,彻底颠覆了我对澳新军团的看法。也许我不应该事先背会视力表?母亲听说我体检没问题后很高兴。依她之见,在部队里锻炼一段时间,更能把我造就成一个男子汉。我反对说,也许会把我造就成一具尸体。她听了无动于衷。老太太有时候真的铁石心肠。
但是我很走运,遇到堪培拉一位相当不错的眼科专家。他给部队检查眼睛,明确指出,我不适合当兵。他说,澳大利亚在共产主义的“转身下刺”之下,没有我当兵入伍,就已经十分脆弱了。一个连这种动向都看不清楚的青年人能派什么用场呢?近视眼在部队里不吃香。一个在南澳大利亚应征入伍的视力不好的士兵在越南被地雷炸死。联邦议会正就此事提出种种疑问。现在他们发现我根本就不适合服兵役。
母亲让我觉得近视眼是件丢人的事儿。我敢断定,三十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她不知道在哪儿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一家人要是有几个近视眼就是家门不幸的信号,是“我们这个家族未来”的凶兆。那时候,优生学盛行,尤其她那些见习教师同事更把这个理论奉若神明。非常不幸,她那时候已经生了三个“有缺陷”的孩子,都是高度近视。我是最后一个,而且缺陷最大。母亲不允许我们为这种耻辱“做广告”。等我们不得不配上眼镜之后,父母要求在家里不准戴,在别的地方也尽量少戴。我们习惯了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学会了遇有特殊情况,假装视力不错。我虽然没有多少机会去验光师那儿查视力,但天才别具,背会了视力表头四行或者头五行的所有符号。我父亲(总是父亲,母亲从来不愿意“与魔鬼共舞”)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赶快溜到视力表跟前,记住那些符号,然后就验光。验完光就等待“视力还不太差”的结论。父亲听了之后自然很开心。部队体检时,我又故伎重演。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书。书多就意味读得多,也意味视力不错。可是一旦喜欢读书,就一发而不可收,甚至读得上瘾,成了嗜好。不管怎么说,我的书越来越多,后来的日子里,家无论搬到哪儿,屁股后头都得拖着一箱又一箱的书。我读的书也很杂。就这样,《亚洲人》上那行字变得歪歪扭扭,而且一直没有再“纠正”过来,这个兆头可不好。可我总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连汽车也变形了,倒没有变得不可收拾,但却歪歪斜斜。开动起来走的似乎不是直线,而是像螃蟹一样爬行。我想起参观复活节展览会的情景。站在哈哈镜前,看自己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一会儿变胖,一会儿变瘦的样子,乐不可支。
最大的问题是,我这个新的、被扭曲了的世界无处不在,怎么逃也逃不脱。后来,二〇〇四年十一月,那周刚过了三天,我的视力彻底完蛋了。星期一,我还开着车去上班,读所有我需要读的书,对付得还不错。星期五,我就成了“法定盲人”。对此,人们的反应怪怪的。大伙儿经常祝贺我,看起来不像个瞎子——没有导盲犬领路,没有拄白颜色的拐杖,也没戴墨镜。向中等距离的东西张望时,也不是神色茫然。或许这样的评论只是对我的鞭策?也许我这个瞎子“表演”得还不够娴熟?演员比我强多了。他们可以装得两眼无神,目无所视,步履蹒跚,跌跌撞撞,颤颤巍巍伸出手找一个可以支撑一下的地方。事实上,我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角色。虽然假装视力好是我的长项,但并不就意味着我就长于此道。我们当然都认为自己知道人双目失明是个什么样子。最擅长这“活儿”的是眼科专家称之为NPL的人,也就是完全没有光感的盲人。NPL毫无疑问是真正的盲人。我还不是。我视野的中间部分模糊不清,不能看书,看不见人的脸,也不能再开车。但是“周边地区”还能看见,所以还能走路,给自己弄杯咖啡,或者往CD机上放一张光盘。尽管有时候会拿错。头上戴顶“法定盲人”的帽子,却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瞎子,可不是件让你心里舒服的事情。机智幽默如我,就会向专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法定盲人?”“当然有,”他回答道,“不过有的人装模作样。”这话听起来令人伤感,但也凸显了我面临的问题的真实性。有些假装失明的人长于此道,他们是装聋作哑的古老技艺才华横溢的表演者。难道我现在要和这些老谋深算的“表演艺术家”竞争吗?谁敢保证别人不把我也看成这样一个“艺术家”呢?
我通过了测试——总是会有测试——允许我拥有一根白手杖。但是手杖解决不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从眼角还能看见点什么,还可以有足够的视野让我行走自如的话,手里拄根手杖岂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所以,我不打算用手杖。墨镜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也没有导盲犬。人家告诉我,我还没有资格驱使一条狗。这对我可是个沉重的打击。我宁愿要狗也不要手杖。我一直期待有一个人类最忠实的朋友陪伴着在郊区溜达。现在被告知,好梦难成。他们说,对于导盲犬而言,我能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会把狗弄糊涂的。我们会在街角争论不休,甚至为谁是老板、谁说了算打起来。
父亲听说我成了“法定盲人”,非常惊讶。他那时已经九十多岁,卧床不起,十分虚弱。但头脑还很灵活,还想知道伊拉克局势如何。养老院里很少有人和他谈这个话题。像他这样弱不禁风的老人都喜欢说点轻松的事儿。他一直认为我是个“万事通”,能和我抱着电话聊布什、布莱尔、霍华德、伊拉克,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我打算去阿德莱德看他,在那儿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我会步履轻捷走进他的房间,搂着他的肩膀,有力而又不显得过分亲密。我会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直盯盯地看着他,夸他气色不错,毫无疑问再补充一句,这是瞎子瞎夸奖罢了。他表示同意,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俩虽然一言不发,但都心照不宣,想打破对方的疑虑,确信他和我“表演”得都不错。这次探望本来定在十一月,回去给他过九十七岁生日。可是回阿德莱德之前,我去了两次中国。父亲八月下旬去世,我没能见他一面,只能在葬礼上发表演讲。我讲得那么好,有的人纳闷我是不是真的瞎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葬礼上讲得不好也是视力低下的表现之一。也许我朝错误的方向茫然失神地凝视,或者面对小教堂侧墙发表演讲,就会让我的“表演”更加精彩。母亲对视力不佳有严重的恐惧症,她早去世几年,全然不知儿子成了个瞎子,也是件好事。
我得的这个病医学上叫黄斑变性。成千上万的人有这个毛病。如果我们这些得黄斑变性的人能相互看见的话,也是一支了不起的大军。我们之所以不能“面面相觑”,是因为眼底血管破裂,血渗透到视网膜,中心视力被损坏。这种极脆弱的血管会不断出现断裂。黄斑变性破坏了病人看人的面孔和读书看报的能力。面孔模糊不清,图像不稳定。字母和单词变得面目皆非,一行行文字颠三倒四,支离破碎,相互碰撞。数字就更麻烦了,就像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小学生东躲西藏,跳来跳去,作弄苦不堪言的老师。在支票上签字要非常集中精力,靠运气才能签得像模像样。电子计算机帮了大忙,键盘可以调整,字号可以放大,还可以安装新软件。不过尽管可以把字放得很大,看东西的时候还是少不了猜测。从前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现在变得非常缓慢。《亚洲人》成了我能拿起来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我还能从图书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我新书出版、重要活动、各种比赛的消息。最近有一个通知说,澳洲视障协会——给我提供手杖(不给狗)的团体——给能正确答出一个小测验提的问题的人发放奖品。我没有参加比赛。后来,又来了一个邮件,宣布获奖者名单。奖品是一本会话书,书名叫《胳膊下面的橡胶》,一种证明!奖品如此怪诞的比赛不参加也罢。多怪的书名!显然这是一位被过分激励的作者为博得读者一笑而写的。我沿着邮件上那行字往左面——我视力比较好的那面——看,想弄清楚作者是谁。渐渐地,罗尔夫·布尔德瑞伍德的大名向我“游”来。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奖品,《胳膊下面的橡胶》。
黄斑变性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眼病,可以对已经病变的血管进行激光治疗。我治了五次。激光可以激活血管,延缓退化,但是要冒在视网膜上留下疤痕的危险。事实上这些方法都无法恢复视力。后来,人们突然之间不再谈论激光治疗。今天说是创造了奇迹,明天就成了过眼云烟。激光被一种新药代替。好消息说,这种药可以改善病情;坏消息说,要把它直接注射到眼球里才行。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我无法面对这种治疗方法。给我治病的那位眼科专家并不坚持。他说,注射不注射由我自己决定,那是我的选择。可这真是艰难的选择。一个病人面对有可能改善病情的方法,很难说“不”。我开始用这种新药治疗,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而最好的结果有可能比我们希望的更好。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被损伤的视网膜有可能修复。因为能让我保持周边视力的健康的细胞可以生发出新的干细胞。眼下,我的那些书还放在先前的地方。也许和蔼可亲的阿尔弗雷德的《印度的寺庙和陵墓》、《印度的灌溉》总有一天也都会放到书架上。不过我不会失去自制力。勃·迪伦[13]恼人的歌声在我耳边回荡,挥之不去:“天未黑,但暮色已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