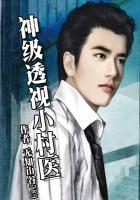于是她把生活当作了表演。比如早上起床伸懒腰时,她会想:我这不是简单地伸懒腰,而是“演”一个小姑娘在伸懒腰,那么如何“处理”才好呢,是夸张地把躯干扭曲成一张弓,还是含蓄地用胳膊肘挡着脸打哈欠?这一个懒腰往往要伸五分钟之久。吃饭的时候她又会想:这次是塑造一个典雅的大家闺秀,一粒米一粒米不露齿地吃,还是一个饿极了的小乞丐,狼吞虎咽呢?到晚上自习时就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但还要把腰绷得笔直,“文艺兵”似的长脖子微微隆起一个弯儿,展示的是灯下的淑女造型。
或者还会把课本上的内容念出来,哪怕念的是“从战国时代起,我国进入了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要矛盾的封建社会”,也要用电影旁白的抒情口吻。边念还边高标准严要求:吐字一定要清晰,杜绝含含糊糊的北京腔。我可不愿被定型为一个“本色演员”。
这些“表演”的目标观众当然是妈妈,每当妈妈在时,节节就“演”得格外卖力。看见了吧,她暗暗向妈妈论证,我已经懂得了“台上一分钟”,从现在就开始下“十年功”了。你当年睡觉也要用沙袋压着腿的精神,我也有。
但妈妈却总是视而不见。顶多评论一句:“咦,今天的坐姿倒是端正。”
这么“绷”到周末,节节又开始着急。时不我待啊,剧组眼看着就要开拍了,妈妈的态度怎么还没转变呀。这时她又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矛盾:假如“表演”的最高境界是和“生活”一致,那么让妈妈“看”出自己在“表演”,不恰恰说明她“演”得不够好吗?听说过还原生活,没听说过还原表演的啊。这个领悟让节节后悔不迭。绕这么大个圈子干嘛?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于是她焦躁地去翻客厅里的小茶几,看到“制片副主任”和“导演”的名片还在电话下压着,便又放心了几分。当初说好了“过几天再打电话”的,那个电话还没打,就说明妈妈还没决定下来,她的演员梦还能再做两天——或者是两个小时,两分钟。
但她又受不了这份煎熬,便把那两张名片从座机底下拉出来,露出关键文字。
第二天,她又发现名片被整个儿压到电话底下去了,便再次把它们拉出来。这次露出得更明显,保证妈妈一坐进沙发就能看到。
终于,这天她正在房间里百爪挠心,就听到妈妈看着电视,忽然轻轻“哼”了一声。这段时间,她对妈妈的一举一动都是格外的敏感,敏感到了一分钟眨几次眼都数得出来的地步。她也自嘲:还没当上演员呢,却先把自己训练成警犬了。而这一“哼”,在她听来是很有特殊意味的,不像是对电视里的人物发出的。
于是节节的脖子僵硬了,手指微微发抖。她听见妈妈把电视调小声,拿起电话,拨错了号,挂掉重拨一遍。
然后妈妈对话筒低语,那声音比电话另一边的还要小。制片副主任气愤的吼叫连节节也听见了:
“不同意?不同意你打电话来干什么?不同意就算了,地球缺了谁还不是照转……”
“还以为你真的在等我回话。”妈妈说,“就是想给你一个交待。”
“交待”这两个字被咬得格外清楚,节节明白,这是“交待”给她听的。自己的一片苦心妈妈不是没看在眼里,但看在眼里也不当回事。刹那之间,眼前就模糊了,泪珠泛上来,追逐着滑过她的脸。她倔强地用胳膊去抹,但重新清晰的世界已经不是方才那个了:一个女孩的美梦刚刚破碎了。
节节踩着棉花一样走到客厅,对妈妈展示她的眼泪。这就不是“表演”了,不用咬枕巾也够真切够撕心裂肺了吧。而妈妈抿抿嘴,眼睛垂下去,又把电视音量调大。调得有点过于大了,耳朵里嘈杂无比,已经足以把委屈点燃成怒火。
“你凭什么你?”节节拖着长声哭道。事情绕了一圈,又回到“副主任”第一次登门后的那句质问。
“凭什么我已经解释过了。”妈妈说,“好话不说二遍。你不明白是因为你想不通,通了就好了。”
什么“通了就好了”,难道自己的悲愤在妈妈看来仅仅如同一次便秘吗?节节痴了一般重复:“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但这时的意思已经变成了:你凭什么有这么强的优越感,如此轻率就决定别人的命运?
她要还之以牙报之以眼——去刺激妈妈最脆弱的地方。这个念头一生成,她的思路、语言就像追光一样陡然清晰,目标准确了:
“你就是嫉妒我。”她用自己能想象到的最尖刻的语气说,并痛恨眼泪削弱了这份尖刻,“你自己白当了个演员,蹦跶这么多年连戏也上不了,所以你心理变态,生怕别人比你强——我就是比你强,别人追着我上戏,不像你,为了上戏去假积极、拍马屁……”
“我可不嫉妒你这个。”妈妈仍不动声色,看来她已经想到了节节的这一招,因此做好准备了,“你要是当上女局长女律师女经理我才嫉妒你。为了这个——我可犯不着。”
“你虚荣!你要不虚荣爸爸也不会走!”这话嘶嚎出来,节节都为之一凛:战争升级了,没底线了。按核按钮了。
妈妈也是一怔,眯起眼睛看她。胸脯起伏了,好,节节快意地想,杀伤了。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杀它个尸横遍野。她反而冷静了,调整到了残酷的状态:
“你就是不尊重别人,过去从来就是这么对爸爸的,所以他才会不要你,跟一个土包子跑掉……他宁可要一个土包子也不要你!我就不明白,你都混到这份儿上了,怎么还觉得自己有资格压人一头呢……”
一边说,节节一边转身,往屋里走。她要造成的效果是:出手之后翩然离去,就像最冷血的剑客,让对手看着自己的背影慢慢窒息。
然而妈妈却命令道:“站着别动。”仍是平稳的祈使句。在一塌糊涂之时,只有这种语调才最有力量。节节已经明白了这个伎俩,但仍被摄住,停在房间门口。
她用余光看到妈妈从沙发上抓起一本杂志,向自己扔过来。哗啦一声打在肩膀上,并不痛,但却有裂锦、碎琉璃的效果。这是妈妈第一次向她动手。
然后她看到妈妈脸色苍白,仍坐着不动。不知是不想动还是动不了。总之像一幅会喘息的人像。然后节节突然想到:原来刚才用于刺伤妈妈的那些疮疤,也是属于她自己的啊。家里没了男人是孤儿寡女共同的耻辱。然后她发现自己和妈妈是如此相像:压抑的样子、爆发的样子、爆发之后疲惫的样子。她和妈妈就像树枝与枝上抽出来的嫩条,一个痛了另一个也会痛。对于她们来说,伤对方就是伤自己,但她偏要用自己的痛去搏妈妈的痛。
然后节节的身子软下去,软下去。她靠着房门,瘫坐在地上,和妈妈遥相呼应地苍白静默。
从这天起,母女两个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陌生人。那套旧房子里的一切人类行为都变成了哑剧:妈妈照常做饭、压腿、看电视,节节照常放学、吃饭、做功课,但谁也不说话。为了避免交流,她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嘛,那好,在家就都低着头,出门再抬头。
在这场“定力”的消耗战中,妈妈自然是优势的一方。没过两天,她就又满面春风的了,哼着歌儿洗衣服时带着得色,向节节传达两个信息:第一,没有你我一样很高兴;第二,你看,我比你可有风度多了。
这自然让节节更憋气。明明是妈妈伤害自己在先,她才奋起反击的,怎么现在倒像是她无理取闹了?那一阵,每天当听到电视里新闻发言人的义正辞严,她就心有戚戚,深切认同:“美方一贯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并打着人权的幌子指手画脚……”
说得何其准确啊。
而这时候她又想:要是小不忍在就好了。要是许洋在,她就有盟友了,不会如此孤立。虽然妈妈一定会大张旗鼓地拉拢许洋,含沙射影地说什么“要是亲儿子就好喽”,但节节的直觉相信,许洋心里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的。当初,那家伙不是为了自己才和妈妈好起来的吗?
只可惜许洋已经走了,回湖南去了。他的学籍在那边,只能到那边复习,参加高考。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别担心,我一定会考回来的!”
当时节节撇撇嘴:“我担心什么呀?你考哪儿是你的事儿。”
但是现在,在和妈妈的冷战中,节节第一次真诚地想念起许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