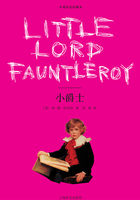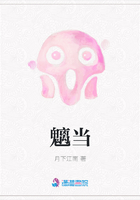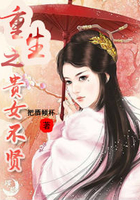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他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战友死去,有时还亲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阵亡的军人支离破碎的肢体。罗丹崇拜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得那些资产阶级能在家里过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战斗了八年后,他才从国内的平民处得知,他们大多对军人毫不关心。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诋毁军队的文章全是诸如严刑拷问俘虏以获取重要情报之类的琐事。这些在马克?罗丹的内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于缺乏机会而逐渐累积的怨愤,他变得极端起来。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国内政府和人民为后盾,军队是可以击败越盟①的。放弃印度支那是对成千上万战死在那里的优秀青年的极大背叛,让他们的死变得毫无意义。而罗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背叛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春天,他离开马赛口岸时,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确信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群山将见证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法国军队将成为全世界眼中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还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在布莱德,他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推翻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词,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宫①,并于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萨特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一九六○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在一九四○年六月听到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一百二十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军组织”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秘密军组织”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军组织”拥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这就是在三月十一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关于刺杀戴高乐行动所面临的问题。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订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秘密军组织”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秘密军组织”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秘密军组织”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看到这些,级别较低的成员都极为泄气。在法国境内,以前愿意提供帮助,藏匿被通缉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的人,现在只说一声“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小克拉马尔行动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全部被迫关闭。法国警察根据内线的情报,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储备武器和物资的秘密仓库;另外两个刺杀戴高乐的计划在组员们刚坐下准备开第二次会时,就被警察破获了。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空谈恢复法国的民主时,罗丹正冷静地审视着床边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所描述的事实:资金短缺,在国内外失去支持,成员减少,信用下降,“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进攻下正在分崩离析。
枪决巴斯蒂安-蒂里只会使士气更加低落。现在这个时候想找到肯提供帮助的人真的很困难;那些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长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个法国警察和几百万市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的任何新计划,只要涉及多个策划和多个组织间的协同,都会在刺客走进戴高乐周围一百英里之前暴露。
罗丹反复思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喃喃地说:“一个没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杀总统的人逐个想了一遍。他们每个人在法国警察总部都有一本和《圣经》一般厚的卷宗。还能是什么原因呢?他马克?罗丹不也是只能躲在奥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馆里吗?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终于有了答案。他曾一度放弃了这个答案,但又带着浓厚的兴趣重新去考虑它。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有这样一个人。慢慢地,很艰难地,他围绕这样一个人制订了另外一个计划,然后用所有的障碍和反对意见来检验它。这个计划全通过了,甚至包括保密问题。
午餐铃敲响前,马克?罗丹套上大衣走下楼。他在大门口遇到了顺着冰冷街道迎面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在过热的房间里抽烟引起的头疼和麻木却一扫而光。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他发了一连串简短的电报,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于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务外出,这几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艰难地走回他那简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最终也胆怯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或暗杀威胁下也要销声匿迹了。他耸耸肩,随便他们怎么想,没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
他用旅馆的优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条。尽管多年印度支那的丛林时光和阿尔及利亚的荒野生活让他对美食没有概念,但这顿饭实在令他难以下咽。当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账单,离开那里独自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找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点,找某一类人,一类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机朝着伦敦机场四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从贝鲁特飞来。在排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英国人。中东的阳光把他的脸晒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尽情享受了两个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不过对他来说,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从贝鲁特一家银行转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沙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掉了。他们的死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扎菲拉式火箭研制推迟了好几年,而在纽约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则觉得他的钱花得太划算了。这个英国人轻松地通过了海关检查,乘出租车驶向他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
罗丹找了九十天,收获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从不离手。回到奥地利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是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店。
他在城里的大邮局发了两份简明扼要的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另外一份发往罗马。电报是召集他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到他维也纳的住所开一个紧急会议。二十四小时之内人就到了。勒内?蒙克雷从博尔扎诺乘出租车来,安德烈?卡松则从罗马乘机抵达。两个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他们两个都排在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卷宗的前列,这个时候特工们正不惜血本地花费大把的银子雇佣眼线在边境检查站和机场找他们呢。
先到克莱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预定的十一点早了七分钟。他让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的街角,下车后,在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花了几分钟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迅速走进旅店大厅。罗丹和往常一样登记了假名,是他最亲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个假名中的一个。被叫来的两个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舒尔茨”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问前台的年轻人。小伙子查了一下登记簿。
“六一四号房。是他约你来的吗,先生?”
“对,没错。”卡松回答,径直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走廊寻找六一四号房。在右手中间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准备敲门,忽然被人从背后抓住。他转过身,抬头看见一张脸——铁青的下巴,眼睛从那道浓黑的眉毛下俯视着他,毫无表情。他身后十二英尺处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隐蔽处,他就是从那里开始跟在卡松身后的。尽管地上的灯芯绒地毯非常薄,但卡松还是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
“你要干什么?”这个大个子漫不经心地问,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有那么几秒钟,卡松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个月前,阿尔古被从伊登?伍尔夫酒店闪电绑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认出了身后这个人,他是外籍军团里的一名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罗丹有时会让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的,维克多。”他轻声回答。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眉毛更是拧成了一团。“我是安德烈?卡松。”他补充道。科瓦尔斯基似乎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六一四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有个声音问:“谁?”
科瓦尔斯基把脸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尽力“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罗丹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拉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