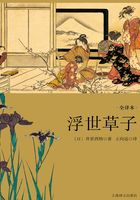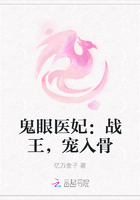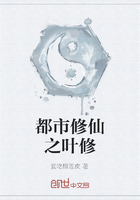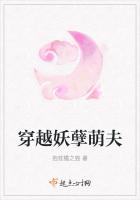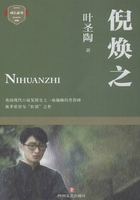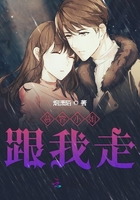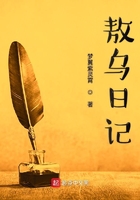泰戈尔来华
1924年,对峙中的南方和北方又有不一样的开局:南方广州的春天早早到来——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总理孙中山任大会主席,秘书长刘芷芬,指定胡汉民、汪兆铭、林森、谢持、李大钊为主席团。孙中山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以及“主义胜过武力”两个报告。这意味着没有党章、党纲,从不开党代会的松散组织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脱胎换骨完成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之际,苏俄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代表大会向莫斯科发出唁电,对列宁逝世表示沉痛哀悼。1月24日,孙中山电复苏俄代表加拉罕贺电,申明完成辛亥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宣言,主张人民集结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打倒直系军阀,扫除帝国主义在华既得权益。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春天来得依旧迟缓沉重——当北京北海边的柳树吐出新绿之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到达北京,为滞重的春天增添了一抹亮色。在此之前的4月12日,泰戈尔乘坐的“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六十多人前往码头迎接。
与前几年的杜威和罗素访华相比,泰戈尔访华更带有某种文艺气息。在徐志摩等人看来,泰戈尔就像是人类的喜马拉雅山,他的境界、智慧、诗意和爱,都是当下中国人所缺少的。中国人由于极权、战争和贫困导致的内心枯干,正需要泰戈尔这样的人注入生趣和灵魂。并且,因为泰戈尔是亚洲人,在文化和心理上更接近。因为泰戈尔的诗人身份,组织者特意安排他与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古体诗人陈三立老人见了面,算是印度诗歌与中国诗歌的碰撞。这一次访问,仍由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主办。按照原订计划,泰戈尔本于1923年访问中国,由于一场“骨痛热病”,泰戈尔不得不推迟了来华时间。泰戈尔这一次中国巡讲,由当时着名的“金童玉女”陪同,男的是《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女的则是秀外慧中的林徽因。每到一处,泰戈尔都在林徽因的搀扶下登台演讲,由徐志摩翻译成汉语。时人这样描述:“林小姐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自始至终阐述东方主义的立场——精神永远高于物质,爱永恒,精神永恒。在泰戈尔看来,所谓的发展物质文明只是一种畸形的状态,会使人的私欲不断膨胀,只知道占有、功利、侵略、掠夺,根本不能体现人的善意和爱;这样的无明,需要东方的精神文明给予调和。在谈到亚洲和欧洲的关系时,泰戈尔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强烈立场,而是阐述亚洲和欧洲的不期而遇——当欧洲人带着力量与理智的傲慢来叩门时,亚洲完全没有准备。亚洲与欧洲不是平等的相遇,而是优势与劣势的关系,一边是侮辱,一边是卑微。泰戈尔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麻木中奋起,证明我们不是乞丐。有人认为我们必须模仿和照抄西方,我不这么认为。”他同时提醒中国人不要忘了他们所创造过的美好事物。现在全世界都在生产巨量的东西、庞大的组织、巨大的帝国行政机构,这些阻碍了生活的道路。相比物质文明,泰戈尔更关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人生并不限于用智力体力征服世界,那样的征服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而在体力和智力(工具理性)之外,人还有精神,泰戈尔把它称为“更悠久、更真切、更深奥的生命”。
不过泰戈尔这一次来华不像前几年杜威和罗素那样受到各界欢迎,很多时候甚至明显感受到来自中国知识层的敌意。除了冰心之类的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之外,很多中国青年因为过于浓郁的政治情结导致了对泰戈尔的反感。在他们看来,泰戈尔对于中国,就像天外来客。最起码,泰戈尔不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良方,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方法和手段,至于其他,包括文学、宗教和哲学,显然提不起他们的兴趣;而泰戈尔的演讲过于主观化,离政治和社会太远,更像是隔靴搔痒的布道。当时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鲁迅、郭沫若、林语堂、陈独秀、闻一多、茅盾、瞿秋白等人都对泰戈尔的举动作了嘲讽。这当中以陈独秀的态度反差最大,陈独秀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这一次,已身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却这样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国民党的“才子”吴稚晖也指责道:“若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思叫老石器人民,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除了遭受党派人物攻击之外,自由主义者也不喜欢泰戈尔。不过出于礼貌,自由派学者一般不直截了当提出批判——胡适在承认自己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的同时,特意点明:“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意味深长,溢于言表。不过胡适也不忘提醒左派应采取客观态度:“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主张不同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胡适清醒地看到,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在他看来,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各方对泰戈尔的批评,大大影响了老人的心情和身体。自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后,泰戈尔取消了中国的所有安排,不再公开露面也不再发表演讲。5月30日,在中国只待了两个月的泰戈尔从上海乘船去日本。虽然颇为失落,不过这个东方智者并没有过多计较他在中国所遭遇的攻击。也许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个落差如此之大的古老帝国,自然是很难平心静气的。泰戈尔仍旧坚持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自己的热爱,以及祝愿。在他离开中国的日子里,徐志摩使出中国传说中的送客习俗——十八相送,随从泰戈尔去了日本,继续意犹未尽的交谈。告别之际,徐志摩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虔诚的大诗人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吴将军如日中天
这一年开春泰戈尔的来华,以及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动静虽然很大,不过似乎都没有引起吴佩孚的注意。在自负的吴佩孚看来,虽然那个印度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因为写的不是旧体诗,加上鼓吹的是与宗教有关的东西,与自己心中“修齐治平”的追求不一,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注意。至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对他的征讨,吴佩孚也不放在心上。这一年,吴佩孚的心思都在中俄邦交的恢复以及关于蒙古问题的交涉上。6月21日,外蒙古通告俄国政府决行共和,与中国脱离关系。7月6日,“外蒙古人民政府”对外宣言改为共和国。蒙古的得而复失,让北京政府坐立不安,吴佩孚此间先后四次出席国务院外交部会议,主张及时解决中俄交涉。吴佩孚甚至跟曹锟商量武力收复外蒙古的可能。当然,对于南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吴佩孚重点是布置苏皖赣鄂豫陕鲁的七省联防,以及暗中与美国商人来往,以求得某种私下的军火支持。
1924年可谓是吴佩孚年,五十岁的吴佩孚如日中天,他所控制的地区北至山海关,南到上海,左右大半个中国;对于国家事务也有直接的影响。开年的1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马克瑞专程到洛阳会晤吴佩孚,观看了吴佩孚专门为之举行的盛大阅兵礼。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23年,前美国驻中国公使、当时的中国政府顾问芮恩施,专程去洛阳跟吴佩孚密谈。美国使馆秘书、武官以及美国驻华军队司令与亚洲舰队总司令等,也先后拜访过吴佩孚。这样的举动,表明英美看好吴佩孚。在对列强的选择上,吴佩孚明显倒向了英美,他的公署墙上悬挂着华盛顿像,吴佩孚时常对来访问的中外宾客表明,很想跟华盛顿联合十三州一样,促成中国的统一。这一年的9月8日,吴佩孚破天荒地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更是向人们传达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对于吴佩孚的看好。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时代》的封面,照片下面有两行说明:“GENERALWU”(吴将军)“BiggestmaninChina”(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他的脸部显示出喜争好斗的表情,看上去踌躇满志、坚定不移。吴佩孚的长相不同于一般华北人氏,他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子挺直。“吴将军”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并不是吴佩孚的影响所致,而是世界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好几年,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关注,目光就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1年8月11日《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只有以吴佩孚这位“受到全国信任的领袖”为中心,而且必须排除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国内其他地方已经完全失掉了信任,倘若他继续保持着僭称总统的职位,那么,重新统一就没有希望”。《密勒氏评论报》在一则社论中说,在中国,吴佩孚、冯玉祥和陈炯明“似乎是更为爱国和富于公益心的”军人。他们“显然是中国的希望”。《京津泰晤士报》还认为“陈将军和吴将军一样,是在中外人士中享有盛誉的人,假如他们之间能为准备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立宪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北京和广州两位不合法当选的总统(指孙中山与徐世昌)间之争执就将成为次要问题了”。同一时期的外国在华媒体《字林西报》、《远东时报》等也持这一观点。这些,都传达了西方对于吴佩孚的看好。即便远在美国,《时代》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儒雅而有魄力的中国军人,虽然没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凭着他的自信和谦逊,他将是自袁世凯之后的一个乱世维治的人物,也是最有可能实现西方政治理念的中国人。
吴佩孚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不过寥寥几笔,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属于他的管辖省份。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大帅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时,吴大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四点半到五点半。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着称。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时代》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将军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立的一派,但却远非“敌人”。更多时候,相比曹锟的平庸,吴佩孚显得更加卓越。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西汉初年刘邦与韩信,或者三国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国文化似乎一直在君主之间维系着这样的平庸和卓越,平庸者往往有着大智慧,聪明者却经常露出致命的软肋。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印证这一点。其实吴佩孚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始终是明确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也是某种狭隘性质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所擅长的治军,也充斥着传统气息,纪律严明,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也不用学生兵。练兵,他效仿的是岳飞、戚继光和曾国藩,带有浓郁的传统“搏命”色彩。从吴佩孚一生所作所为来看,他持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对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强烈排斥的嫌疑,也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仅靠“振臂一呼”为自己挣得很多印象分。
奇怪的是,作为直系二号人物的吴佩孚上了《时代》的封面,而通常认为的直系一号人物,吴佩孚的上级、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却无缘《时代》。除此之外,南方的孙中山,东北的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时代》以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显示着某种美国立场和价值观,也意味着美国对吴佩孚的支持。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时代》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有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将军这位军阀无人能取代。”尽管这位张将军“思维敏捷,权力巨大”,“却非吴将军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刊物没有刊登张将军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MARSHALCHANG”(张元帅)“Histitleisnoempty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已开始注意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