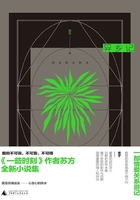我松了手,浑身无力地跨出了电梯门,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疲惫的战役。我败了,流着鲜血,遍体鳞伤。小狗乖乖地跟在我后面,它一定察觉到了我的悲伤。狗都明白的事情,人却不能!人类,真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
进门后我一头倒在床上。很长时间,我盯着天花板,那里是一片漠然的空白。世界在错综复杂的意识中央缓缓旋转。久久不能结束的狂暴的旋风里,我将自己埋进思想与情绪的沙漠,鸵鸟一样昏睡过去。
4
行驶在空中。黑色的风,刺耳的发动机的隆隆声,从耳畔阵阵掠过。脚下是架在半空中的金属轨道,而我驾驶的这台机器,简直像儿童乐园里高空飞车的翻版,少了些刺激,多了些波澜不惊的平稳。有人叫它“空摩”,即空中摩托之意。我驾驶的空摩一路沿着轨道行驶,仿佛长着巨大翅膀的翼龙在中生代的天空翱翔。那时的天是紫色的,大地是绿色的,被茂密的蕨类植物覆盖;蓝色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浑圆的地平线,每天的日升日落都清晰可见。混沌的远古世界里,远古的生物们过着不知所谓的混沌生活,它们吃草或他类的肉体,行走、睡眠、交配,直至倒下死去。腐烂的肉体化入泥土,第二年便长出新的绿色,在坟头开出象征生命的白色小花。
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星球啊。
而我俯视着现在的世界。一望无际的金黄田野,阡陌纵横,几条小径弯弯曲曲地通向周围的村落。有人在地里劳作,身影斜斜地洒落在背后的土地上。天色向晚,村子里一股股升起了炊烟。我加大油门向前开,风越来越大,在耳边呼呼作响。第一次出现了河流。河水随着时间的波纹缓缓流动,逐渐汇聚成宽广的水面;两岸的村落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显现出白色的墙和砖红色的平顶。这时夕阳正从平原尽处落下,一抹残红浸入了村子尽头的河水。人们停下了劳作,观望这并不稀奇的日落景象,就像他们凝视着太阳的升起。每一天都是一样,从远古到未来,每一天又都是新的不同。
夜色降临之际,我终于来到了城市边缘。星星点点的光芒是远处的万家灯火。把车停在一个类似于终点站的地方,我走下站台,仿佛漫步在外太空中,都市夜景都映入眼里。它仿佛是我的城市,又不是我的;它对我并不陌生,我却感觉它远在万里之外。天上没有星光,月亮在遥远的云层背后。我认定,这不是我的家。它不属于我。
城市的光芒依然闪亮。在众多不辨来源的缤纷光线里,在空无一人的圆形广场上,在一低头便能看到脚下重重黑影的地方,我走了过去,拖着虚空的脚步和长长的疲乏的影子。很快地,我发现自己迷路了。
这是哪里?
我惊恐地回望,试图依靠记忆找回来路。但黑暗完全吞噬了来时的足迹,像巨大的蓝鲸吞噬海底的浮游生物一样。我孤身一人,站立于全然陌生的时间和全然陌生的地点之中。不久,我自己也将变成陌生的代名词。
高处吗?是的,我需要高度来辨认方向。不觉间眼前出现了一幢大厦;我推开门,迷迷糊糊地走了进去。一切来自外部世界的光线都被切断了。没有光的场所之中,我的眼睛重新适应了黑暗。我走进电梯,没有按钮,没有任何指示方向。但它无疑是在向上运行;机械运转时,发出均匀的声音,仿佛人熟睡时的呼吸。电梯把我一直带到了顶层。
楼顶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地面平滑如镜,像是黑色大理石打造而成。我扶着栏杆,艰难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像误入冰场的初学者。可我还是跌倒了。我坐在地上,努力想站起来,却无法挪动双腿,想要叫喊,却发不出声音。我叩击栏杆,敲打空荡荡的地面,却听不到任何回声。向外界发出的一切信息、一切讯号,好像都被吸入了宇宙边缘的黑洞,杳无回音。一个被剥夺了声音的世界。这令我陷入绝望。重新与外界沟通是可能的吗?
我试图挪动身体。伏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像一只壁虎,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平台边缘。大楼究竟有多高?几十层?上百层?我总该记得电梯间里闪着绿光的数字吧?不,那里没有数字,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虚空。现在我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城市了,比空中的视野更加震人心魄。闪电般的蓝光流畅地勾画出城区的边缘,构筑起一圈奇异的空中防线。黑暗里涌现出建筑物的重重轮廓,弯折的墙、虚掩的门和窗、险锐的街角、数不清的迂回起伏,像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样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墙与墙之间是狭窄的城区道路。偶尔从黑暗中闪出金色或银色的光芒,火焰一般从通道中疾驰而过,在无穷远处缩减为蒙昧不清的小小光点。地平线的外围被一层轻盈的光焰围绕,仿佛整个大气都在燃烧。闻到火焰的气味了吗?不,空气只是冷冷地凝滞了片刻。大地陷入了僵局。不久,远道的风滑过耳际,我闻到了海洋的气息,惟一与自然相关的气息。而通向大地边缘的最后一道通路都被封闭了。我发觉自己彻头彻尾失去了自由。
我终于明白:我被困在迷宫中了。
——该怎么办?
我无法开口。沉默冰冷的黑色大理石地面光亮如镜,其中映出变幻无穷的倒影。我屏住呼吸,全神凝视。某一个瞬间,黑色镜面中出现了她的影像,恍如火焰之花盛开在黑夜的河流上。一簇簇向上飘飞的淡蓝色火苗映着她苍白的脸,她久久地,以温柔而冷峻的眼神,悲哀地注视着我。
“子渊,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我记起了来时的机动车站,“我是开着空中摩托来到这里的……但我失去了方向。”
“你必须想办法离开。”
“但我被困住了!我没有办法。”
她的声音,字字句句响在我的心中。我的思想也通过某种不知名的方式传给了她。我趴在地上,透过庞大的镜面,艰难地用意识与她交流。
“不,你会有的。”
“我不能从这里跳下去!”
“只要能离开,一切办法都可以。”她高声说,“记住,走不出迷宫的时候,尽快离开,是最好的出路!”
离开……离开……离开……
空洞的重复一遍遍在耳边盘旋,有如防空警报的鸣响。我俯视镜子般的地面,像死神的夜殿上映出空荡荡的倒影。忽如其来的讯号在心中一闪而过。她的脸庞随之迅速地隐去,遁入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无论我怎样呼唤她的名字。
艾叶,你在哪里?
绝望摧毁了我。我将身体探出栏杆,跳了下去。
一模一样的梦。
夜没有消退。我躺在后半夜的黑暗里,被四面严密而安静的墙壁包围。我仍在L城,旅馆房间的床上,未曾挪动一步。我翻了个身,一如往常地回想起梦中的情景。一样的迷宫,一样从高处坠落的恐怖片断。绝无仅有的荒诞经验再次重合为一。
两年前的海边,我从同样的梦中醒来。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那个清晨我看到了她的短信,发送时间只在半小时之前。我下定决心回复了她。那些话语最终挽回了我们的关系。
但她已然离开。不会有下一次了,我知道。
5
余下的几天假日,我和阿苗等去了海边。
海水那么蓝,海岸线的轮廓那么美,一路绵延,模糊了沙与水、天与地的界限。浅金色的沙滩向大海敞开她的怀抱,无拘无束、无所顾忌,一如大地宽广博爱的胸怀。站在浅水里,水面刚没过脚跟,透明的海水泛出令人心动的涟漪,仿佛蝴蝶翅膀上时光雕刻的图案。退潮时海面翻卷着白色的细浪徐徐退去,裸露出细腻的浅褐色沙土和一道道不规则的印迹,那是大海留给沙滩的吻痕。海洋吞吐着百川、侵蚀着陆地,年复一年地将海岸线塑造成各种不同的形态;而陆地却张开热情的臂膀来拥抱她,即使那让它消瘦了形体、磨损了容貌,它也在所不惜。柔和的海潮声,像遥远的风笛在空中吹响,一曲别离的音乐。
这一事实的明了让人悲从中来。我蹲下来,注视着沙地上自己小小的黑影。相比天空的寥廓、海洋的广大,我的存在渺小如沙海中的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