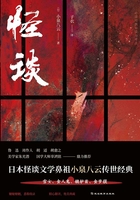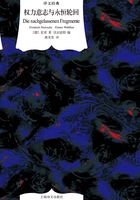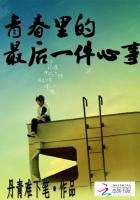尽管几乎所有的“授奖辞”都难免有“好话说尽”的特点,但2012年的“诺奖”《授奖辞》似乎超出了“说好话”的底线伦理,将“夸大其辞”当成了一种没有边界的“话语跑马”游戏:“不同于广告宣传的共产主义幸福欢乐史,莫言通过他的夸张,恶作剧般的戏仿,借用神话和民间故事,对那个宣传出来的五十年(引者按:指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做了令人信服的严厉的纠正。”(Instead of communism’s poster-happy history, Mo Yan describes a past that, with his exaggerations, parodies and derivations from myths and folk tales, is a convincing and scathing revision of fifty years of propaganda.)这里的判断,显然是靠不住的;“诺奖”评委将自己的愿望和想象,强加给了莫言和他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固然以夸张的方式叙述了生活的悖谬和人物的奇遇,甚至记录了作者自己的早年屈辱经历和伤害记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的小说叙事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相安无事”的安全距离。通过一种玄虚而夸诞的叙事方式,他的小说浮游于沉重的现实和严峻的历史之上,并消解了文学与“历史”及“现实”之间的紧张感和冲突性。他没有“纠正”历史的野心和抱负。表面上看,莫言的叙事,赫然武怒,威风凛凛,刀砍斧劈,血肉横飞,但是,深入内里,你便可以发现,他的写作更为内在的本质——气昏志堕,莽撞颟顸,浅衷狭量,粗枝大叶;具体地说,他敢于用尽蛮力来写近乎荒诞的极端事象,有时甚至敢以“二丑艺术”的方式调侃一下,但是,由于与时代生活相关的背景性因素的阙如和细节描写真实性的匮乏,他的叙事和调侃,并不具备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有的可信度和亲切感,也很难产生强大而久远的影响力。
5
在结尾的部分,《授奖辞》最后这样说道:“那些来到莫言家乡的人,可看到丰裕的美德与令人厌恶的残忍的斗争,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冒险。可曾有过如此壮观的春潮席卷中国和世界吗?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咆哮,能够感染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For those who venture to Mo Yan’s home district, where bountiful virtue battles the vilest cruelty, a staggering literary adventure awaits. Has ever such an epic spring flood engulfe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o Yan’s work, world literature speaks with a voice that drowns out most contemporaries.)这几句话,惺惺作态,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我原以为,狃于特殊的文化陋习,只有中国的批评家在吹捧作家的时候,会曲体胁肩、摇唇鼓舌地说好听话,没想到,有些外国人说起漂亮话来,也一样舌灿莲花,也一样天花乱坠,更没有想到“诺奖”的《授奖辞》,竟然也像中国的某类报告会的赞语和颂词一样不靠谱。
其实,细究起来,在评价“东方”作家和“西方”作家的时候,“诺奖”评委的态度与尺度,是有着微妙差别的——他们用更具“正极性”的尺度来评价西方作家,而用更具“负极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作家。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发现了这个极为隐秘的问题,并向“诺奖”的评委们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假如索尔仁尼琴,不是去揭露古拉格,而是对它去开玩笑呢?那么我们还会为他的‘艺术’唱赞歌,并且也欣赏他的黑色幽默?或者,令人悲哀的是,只有非白人才能以这种方式赢得诺贝尔奖?”在他看来,“诺奖”评委“如此”欣赏莫言对历史和现实“开玩笑”的“黑色幽默”,又“如彼”欣赏索尔仁尼琴庄严的愤怒和严肃的批判,于“此”于“彼”,显然是区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的——这说明在他们的评价里,隐含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傲慢和歧视,内蕴着“诺奖”评委的几乎难以为人察觉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这也提醒我们,只有积极意义上的奖赏才意味着荣耀,而那种“宜戒反奖,应呵反笑”的奖赏,则实在是近乎讽刺和羞辱的,——对一个自尊心很正常的人来讲,获得这样的奖赏,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觉得窝囊和尴尬的事情。
那么,对于“诺奖”评委的如此这般的“中国想象”,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呢?假如我们的文学叙事,能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大义炳如”、“雄深雅健”,能像《红楼梦》那样赋予感伤和悲凉以诗意的情调,能像鲁迅那样寓尖锐的反讽于博大的同情,那么,某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虽欲有所言,则无所置其喙。我们还可以拿莫言跟川端康成做一个比较。川端康成也曾经历过日本的毁灭与黑暗、疼痛与绝望,但是,他感伤而不颓废,依然用充满眷恋与挚爱的诗意笔触,来写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通过优美而精致的作品,他将一个“美丽”的日本展现在了“西方”面前。当时的“诺奖”评委主席安德森·奥斯特林在《授奖辞》里,这样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川端先生经历了日本最终的失败,他知道要振兴日本,必须有进取精神、生产力和劳动力。然而,面对日本战后全面接受美国影响的现实,川端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沉稳的笔调呼吁:为了日本,必须保留古老日本民族的美与个性。”川端康成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讲的是《我与美丽的日本》,讲的是日本的“哀愁”与“美丽”,讲的是日本的诗人和诗歌——“春花缤纷兮杜鹃夏啼,秋月皎洁兮冬雪寒寂”,他的演讲禅意幽妙,诗意盎然,令世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刮目相看。然而,比较起来,莫言的小说缺乏塑造“优秀人物”的小说伦理自觉,缺乏严肃地探讨道德主题的能力,缺乏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美好情感的技巧。做为“讲故事的人”,莫言站在“诺奖”的颁奖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述的几个真实性和真诚度大可怀疑的琐碎故事,是纯粹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压根没有“中国”的痕迹,更没有对中国伟大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情赞美。
与这种文化上的迟钝感和目光短浅相关联的,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匮乏。莫言的思想和勇气都不足以支持他与现实建构一种积极的批判性关系。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他的“魔幻”作品所发出的声音显得空洞而虚怯,缺乏更加明确的“及物性”和更加充分的现实感。他对“伤痕文学”和“****文学”都很不买账,认为它们都只在“诉苦”和“控诉”——“控诉政治、控诉坏人”,但缺乏对“自我”的反思,“没有从反面来忏悔”,“灵魂拷问依然不够”。他这样批评索尔仁尼琴:“我觉得索尔仁尼琴依然缺少拷问灵魂的精神,他也一直在控诉,他写那个《古拉格群岛》,写那个《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敢于和当时苏联巨大的反派政治抗争,但他也没有拷问他自己。”莫言关于“忏悔”的见解,尤其是他对索尔仁尼琴的否定,是极不公正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通常被当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精神的继承者,正像“前苏联”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家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叙述强烈有力,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对索尔仁尼琴的严重误解,既反映着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与俄罗斯伟大作家之间的差距,也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差距。索尔仁尼琴说自己“为无声的俄国写作”,这样的话,莫言是不可能讲的;经历了炼狱体验的索尔仁尼琴说自己的写作是“从里面来描写”,这样的话,莫言也未必能深刻地理解。所以,我们可以从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里读到对斯大林形象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而在莫言的作品里,你却不可能看到这种用“从里面来描写”的方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在谈论“控诉”和“忏悔”的时候,莫言混淆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为见证者和抗议者来控诉罪恶,这是一回事;站在宗教的角度,做为同样负有责任的人,反省自己的罪孽,审判自己的良心,则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属于外倾化的姿态,是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社会犯罪和人道灾难的基本态度,后者属于内倾化的姿态,是拯救性的文学面对人性残缺和人类罪孽的基本态度。因此,要求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是不人道的;要求布拉格群岛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是不人道的;要求夹边沟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也是不人道的。不能用“控诉”代替“忏悔”,也不能用“忏悔”遮蔽“控诉”。在一个存在大量人道灾难和********的生活场景里,最为重要的,首先是替无数受害者发出“控诉”的声音,说出容易被忽略和遗忘的“真相”。很多时候,这种直面现实的“控诉”的外倾化写作,远比那种”忏悔”性内倾化写作要艰难,因为,它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考验,意味着威胁和恐惧、迫害和折磨。“忏悔”可以故作姿态,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做秀,但是,“控诉”和“抗争”却必须与对象世界发生直接的冲突,其中容不得一点虚假的东西,容不得你在“现实”之上玩“魔幻主义”的话语游戏。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让无辜的受害者和写作者来忏悔,而是把真正有罪的人和可怕的罪孽发掘出来,诉诸文字,使它无所遁形。
莫言不仅不是一个“抗争”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缺乏那种超越现实的勇气和精神,而且,还常常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那样“奔逐世态”,接受那些本该“纠正”的价值观,甚至接受那些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诡异现实,——这一点,你只要读读他的“丹崖如火照嘉陵”的打油诗句,就全都明白了。从这里,我们不仅看见莫言“瞬间的姿态”(刘再复语,见《明报月刊》2013年第一期),也可以看见他的“本质”,因为,一个人的“本质”通常就见之于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瞬间的姿态”里,正像西美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都体验过强烈的激情和闻所未闻的突发奇想,但是它们的最终价值还是依赖于其对于那些平静、普通和正常时刻的意义,每一个真实的、整体的自我就生长在这样的时刻。”正是这样的“本质”制约着莫言的写作,在赋予他的小说“语出卓特,非常情可测”的夸张风格的同时,却没有同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那样令人震撼的伟大作品。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其实并未发出值得倾听的“咆哮”,也很难“感染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
关于莫言小说写作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就批评得不够充分。我们的为数甚夥的早就被“削掉了棱角”的学者和批评家,本来就像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批评的那样:“他们的风格充满了令人生厌的套话。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新实用主义等套话崇拜把他们送上了九天;对于历史与个人责任重要性的惊人轻视,销蚀着他们对公共事务与公共话语的注意。结果是一种让人气馁的错误的言行,同时整个社会也在无固定方向地、不和谐地漂流。”而在莫言获“诺奖”之后,一些批评家和学者,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陷入了疯狂地说废话和漂亮话的超级狂欢里。“从鲁迅到莫言”,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比超级魔术师克里斯·安其尔更高超的本领,他们一下子就将莫言的劣币兑换成了鲁迅的黄金。虽然他们的灵感和勇气来自诺贝尔的故乡,但是,劣币兑黄金所造成的严重的文化亏空,文学上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补偿和埋单,瑞典人不仅毫厘无损,而且还优雅地显示了自己文明的“先进性”,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东方”的“弱势文化”的强大影响和彻底征服。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视为隐含着“东方学”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从这样的文本里,我们看到的,固然有纯粹属于获奖者一人的鲜花和掌声,也有能够满足部分中国人虚荣心的赞美和荣耀,但是,如果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我们首先看到的,恐怕就不是那些像马赛克一样闪光的东西,而是“诺奖”评委的溢于言表的傲慢与偏见。
2013年2月2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