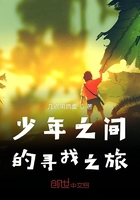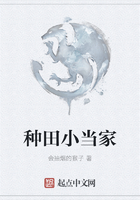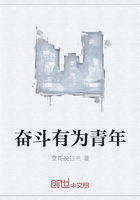1997年。北京。炎热夏季的一天。
因为我所写的一本关于新疆探险的书《荒漠独行——寻找失落的文明》,我意外地接到一个特殊的邀请:邀请我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考察。
一两年前,我应出版社之约写了《荒漠独行》。自从《荒漠独行》出版后,已经接到了数十个电话和信,接待了十数起来访。写《荒漠独行》时,责任编辑的要求是:“不要太费劲,也别反复修改,当作一部驾轻就熟的书稿来写。”这本书我一共只写了四周,可书出版后为它耽搁的时间已经不少了。
上周我还接到过一个读者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打电话时这个热心读者正在从广州市赴珠海的路上,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一路交通要道的繁忙,交警对违章者的呵斥,都清晰可闻。他对新疆的一切都感兴趣,但他的问题却并非我都能解答得了。
在因《荒漠独行》接到邀请的第二天,就要求我确定是否能够应邀去新疆巴州。我当然想去,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去新疆,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过这次确是太仓促了,我不知道自己走不走得开。我得把工作梳理一下,看有没有20天的空当。我告诉对方,我将在两天内给个准信。
这天上午,我静下心来,专门就去与不去作了权衡。
从1992年秋天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结束以来,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1995年底出版了《荒漠独行》,这是有关新疆探险的一部新著。书中我就罗布泊的游移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即罗布泊的特点就是游移,但它的游移,并非仅由风沙所致,也没有一个有规律的周期,它的游移与博斯腾湖的消长盈缩有着不为人所知的联系。孔雀河和塔里木河是楼兰文明和罗布泊区域生存环境的双亲。这只是有待进一步证明的假说。
1996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与丝绸之路文明”国际会议。会上,我提交了题为《罗布泊探险考察一世纪》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详尽地讨论了罗布人的历史、罗布泊的游移这两个问题。在这期间,我担任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主持编译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的执行主编,陆续编校出版了斯文·赫定等人有关罗布泊问题的重要著作《罗布泊探秘》、《新疆考古记》、《丝绸之路》等。我分别为每一部书撰写了一篇导读式的“代序”。
到1997年的夏天,我强烈感觉到,应该就罗布泊问题这名副其实的世纪之谜向20世纪作个交代,到21世纪来临已经没有多少天了。同时,我迫切需要再到罗布人当中去就几个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作一番调查,需要再到罗布荒原去探访和罗布人及罗布泊探险史有关的历史遗迹,特别是阿不旦村。再迟,我就会失去最后的机会。就在这个背景下,恰逢其时地接到了邀请。我会作怎样的答复,还用说吗?
当然,在1997年夏天我的工作相当繁忙,很难临时插进如此紧迫的任务。但这20天并非浪费,而是将对今后研究起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不能没有这个铺垫。我不能使自己坚持了十四五年的探索功亏一篑!
就这样,在接到意外但诚挚的邀请几天之后,我又重返新疆。
1997年8月23日,我从乌鲁木齐越过天山抵达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库尔勒市。上一次我来巴州是在1992年10月,时隔5年,巴州,特别是南疆的门户库尔勒几乎成了一个新城市,如果人间真的有奇迹,这就是个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以仅仅5年时间,就使中国二十分之一的大地充满了蓬勃生机!
离开库尔勒,我们首先前往尉犁极西的喀尔曲克乡。
喀尔曲克与尉犁其他地方的不同在于,世居在那儿的罗布人也是逐水而居的,他们依靠的水域,也正是塔里木河下游的河湖,只不过目前还不能说是塔里木河的终端湖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罗布人的生活在罗布泊和阿不旦终结了,然而它又以某种类似,在喀尔曲克“复活”了。
离开热情好客、古风犹存的喀尔曲克罗布人,我们匆匆赶赴34团。时隔13年,我想再看看“当代罗布泊”大西海子水库。
在本年度的西域旅途中,主题歌(或者“潮”一点,叫“主打歌”)当然不是《北国之春》,也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心太软》了。同行的一位小姐追这《心太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车载录音机就不停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所有问题都要自己扛”,给我们灌耳音,直到我竟以为上了火,开始牙疼。
到达若羌县城,是8月26日的午夜。
一周前,在乌鲁木齐时我就获悉库万老人已去世的消息。就在1997年7月,他以111岁高龄病故于若羌县城。他的遗体就安葬在县城附近的玛扎。
在县城休整时,我心急如焚,我只盼着能尽快见到老朋友、忘年交热合曼老人。而且我下了决心,这次不管出了什么意外,哪怕就是步行,我也要再去探访罗布人最后的首府阿不旦(考纳阿不旦),我要在阿不旦村头的古道旁凭吊我所认识的罗布老人艾买提、塔伊尔、库万……我要在阿不旦村中心为昆其康伯克奉上一束野花,要在依列克河的古岸倾听岁月的潮汐。
从第一次采访起,我始终相当重视库万的回忆,他的回忆不但具体生动,而且与史料吻合。我感兴趣的往事,库万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今后不论何种版本的罗布泊探险史,都应该为他辟置专门的一节。关于阿不旦最后的日子,文献记载零乱而分散,许多内容就要靠库万和其他罗布人的回忆来充实。而阿不旦不仅是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是罗布人历史的终结点,也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关键词,是衔接今天与过去的纽带。
在采访中,库万每每随口娓娓而谈,而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十分认真。从1968年自北京远赴新疆“接受再教育”以来,我就执迷于对西域探险史的往事的探索,难以自拔。但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见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的罗布人交谈。这真使我激情难抑。我毫不费力就可以分辨出,库万的口述从总体的路径走向上是与历史吻合的,他的的确确是世纪初罗布荒原一切往事与变迁的亲历者。在听他谈到“海丁图拉”(斯文·赫定)、“斯得讷”(斯坦因)与“外国和尚”(橘瑞超)的往事时我就认定,他讲的不是“海客谈瀛”,也不是道听途说。
比如,从1984年以来他多次信口对我说起一个名叫“齐诺夫”的外国人在罗布荒原的轶事,比如在一次探险过程中,这个齐诺夫在早晨生炉子时,不小心点燃了唯一的一顶帐篷。而1992年5月、10月,库万两次专门回忆了“齐诺夫”与罗布人的交往。有人对这个“齐诺夫”的真实性大表怀疑:在罗布荒原进出的探险家并没有一个叫做什么齐诺夫的人呀!这肯定是老库万在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当我又一次研读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即《我的探险生涯》)时,不但“发现”了“齐诺夫”其人,也找到了库万所说必真的铁证。
赫定1894~1896年的新疆探险使俄国沙皇十分感兴趣,沙皇许诺当赫定再赴西域时,将给予支持。果然,在1899年,沙皇派了4名哥萨克作为赫定“保镖”,其中之一就叫做切尔诺夫。这个切尔诺夫在罗布荒原的探险考察期间相当活跃,是赫定的得力助手。无疑,这个俄国维尔纳城的职业军人切尔诺夫就是库万记忆中的“齐诺夫”。而且就在《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里,赫定还确实写到了切尔诺夫无意中点燃帐篷的事。在1984年时,库万是不可能从外界获知这件事的,这只能是出自他个人的亲身感受。
再比如,库万一再对来访者谈到在阿不旦时罗布人曾用鱼油拌蒲黄作为一种食物,还说孩子们都爱吃。而一个偶然来访的“有心人”向热合曼求证此事,热合曼回答说,他不知道这回事。于是“有心人”就认定库万在“信口胡说”。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库万比热合曼早一个年龄层次,有关阿不旦的早年生活,有许多库万知道的内容,是别的罗布人所不知道的。而在1997年8月底,热合曼就曾主动对我们谈到“鱼油拌蒲黄”一事,并说明这是听说的,他本人并没有经历过。
关于库万,还有一段插曲。
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曾提到,1984年库万领我初访阿不旦(新阿不旦)时,我问他在阿不旦村附近的那个只剩下一堵一人高的残墙的建筑物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是“营盘”或“炮台”。但别的文章曾说,这个建筑残骸是清真寺。唯独库万坚持对我说是个驻军的营垒。他甚至说,“老将军在阿不旦驻过一营兵,还设了卡子”。这颇难思议,什么人会在阿不旦这个地角天涯派驻军队呢?这个说法从中外文献里就找不到一点影子。我一度也不相信那是“营盘”。但1990年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得到了一部珍贵的英文书:1905年出版的斯文·赫定所著《罗布泊探秘》。这书中有赫定自己画的几百幅素描插图,其中的一幅竟注明:“1899年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的中国要塞。”而赫定画的正是库万独家指认的这个“炮台”!就在这本书中,赫定还说明,阿不旦的驻军归蒲昌城——都拉里的“按班”调动。1899年,罗布人刚刚迁居到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可见晚清时确实曾在新阿不旦附近短期驻扎过军队,以扼守与甘肃、青海连接的古道。库万的回忆是正确的,只是他对“老将军”印象太深,而将其误归于杨增新在位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淤。
这些都足以证明,与其他我所见过的罗布老人相比,库万是属于早一个时期的。
我知道库万对楼兰文明与罗布人这世纪之谜意味着什么,他的去世对罗布人的历史调查有什么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我看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只有他已不在了,人们才会充分注意到他的存在。
“不在了”才“存在”!
1997年夏天,北京的白颐路改造工程正处在紧张阶段,施工使白颐路临时成了一个城市热岛,极难通行,这时候,报纸正在讨论北京所面临的一百年来最酷热的夏季问题。可我却在塔克拉玛干的东端作一次新的探险,一次有惊无险的探险。
1997年8月28日,我们来到米兰镇。
吃过午饭,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二连——现在叫民族新村了。我们在热合曼家的葡萄架下耽搁了多半个下午。
这是我在米兰第五次对罗布人做专题采访。
在米兰的两天采访和重返荒村阿不旦,使我把以往缺失的环节都补齐了。当然,这就像那个“吃到第八个包子才吃饱”的故事,只有这次是不行的,缺了前四次铺垫,这第五次就等于悬在空中。没有十几年的调查、探索、思考、研究,我也不必一再来米兰看望罗布人。可的确是在这一次,我才把为岁月风霜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历史往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卷;我才在画卷上找到了我的位置,我才能够依据这幅未能最终完成的历史长卷,结构出新的画面。
一到米兰,我们直奔热合曼的家。他正好不在,到草滩去打牧草。翻译吐尔逊·马木提把他迎回家。
一见面。我就对热合曼说,他依然如故,可我却老了很多,“早生华发”。我们都没有提到库万的去世,然而,正是因为共同认识的人纷纷谢世,我们都挺珍视这次重逢。
喝过茶,我开始提问:1984年我去过的阿不旦,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阿不旦,并不是真正的阿不旦——考纳阿不旦,它是另一个阿不旦,新阿不旦。是这样的吗?
热合曼点点头。
“为什么?”我急切地追问,“为什么你们以前从不提到除我们去过的新阿不旦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老阿不旦?”
沉默。
“啊……那么就是说,”我换了个提法。“在100年前,昆其康伯克死了,老阿不旦就没有人居住了,罗布人在100年前就迁到了现在的阿不旦——新阿不旦。而新阿不旦的原名叫玉尔特恰普干。对吗?”
据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我才获悉了如下事实:
只有1876年普尔热瓦尔斯基,1896年斯文·赫定这两个探险家,才抵达过真正的阿不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从1898年以来,人们所谓的阿不旦,实际上是另一个新阿不旦,它的原来的地名叫做玉尔特恰普干。
热合曼有点惊异地看着我,略显迟疑地说:“你知道玉尔特恰普干?玉尔特恰普干……对。在离开老阿不旦之后,我们的父辈又选择了一个新定居地,可是刚刚搭起萨特玛,就在一次点火熏赶蚊蝇时,不慎把全村都烧毁了,离开老阿不旦的居民只好从那儿再搬到现在的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那个被烧的村子,就叫‘奥特开提干乌依’了。”
“明白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您……去过老阿不旦吗?”
热台曼回忆着摇摇头。“我的父母离开老阿不旦之后,住在另一个叫夏卡勒的罗布人的村落。我不是生在老阿不旦的,而是出生在夏卡勒。居住在老阿不旦的人,看不起夏卡勒人。几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就领着我去依靠她的父母。而她的父母在离开老阿不旦之后,就定居在新阿不旦。新阿不旦又叫做玉尔特恰普干。我在几十年前去过奥特开提干乌依,那个为火烧了的村子。”
看来热合曼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我又问:“那么,你去过老阿不旦吗?你认识去老阿不旦的路吗?”
热合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继续问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使我极感困惑的谜:罗布人的伯克是世袭的。可是为什么在昆其康伯克死后,他儿子托克塔阿洪却没有继承清廷册封的五品伯克的位置?
“托克塔阿洪……他作‘苏皮’了,出家了!”
我大吃一惊,赶忙打开笔记本。这可是从未见诸记载的新情况。接着,热合曼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在海丁图拉走后的某一年,托克塔阿洪在荒滩打猎。海丁图拉临走留给他一支猎枪。一天,他见到了一支奇怪的黄羊,这黄羊竟叼着一支香烟。他正要开枪,黄羊突然不见了。在追踪黄羊蹄迹时,他又见到一峰头朝西的白驼,白驼是塔里木人心目中的圣物。随着一声枪响,白驼也不见了,却有一个缠头巾很大的老人站在他的跟前。他马上就明白,自己是遇见神仙了。老人给了他一个瓷盘,对他说,这是神物,可以解决罗布人的疑难,你要好好保存它!
受到神仙的点化,托克塔阿洪就在遇到老人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玛札,自己一方面作为看守人,守护玛札,一方面出家在玛札里修行,成了苏皮。这个瓷盘是神仙给罗布人的圣物,就陈放在玛札里。罗布人有什么想法、要求,就来玛札向瓷盘倾诉,而总是有求必应验。
这个老人就是阿帕克霍加显灵。
热合曼叙述的故事挺长,在这儿我只引了有关的段落。这是罗布人当中唯一的有情节的传说。“苏皮”,是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阿帕克霍加,就是喀什噶尔的“香妃墓”的真正墓主。这当然是个传说,但它可以解释有关罗布人融入近世维吾尔社会的许多相关问题。而托克塔阿洪出家,建立了罗布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玛扎,并驻守玛扎,就等于自动放弃了伯克的继承权。这就足以解释我的疑难,回答了探险家们(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的困惑,也丰富了人们对20世纪罗布人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同时,热合曼还说出了罗布人在昆其康伯克以后的首领世系。这个世系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替昆其康的是他的表弟(一说弟弟)买买提·尼牙孜,买买提在30年代去世,本该托克塔阿洪继任,可那时他已经是个苏皮了。以阿不旦为行政中心的罗布人,一直由清康熙年间册封的两个世袭伯克统领,在昆其康驻阿不旦时期,另一个伯克叫尼牙孜,买买提就是这个尼牙孜伯克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热合曼老人是尼牙孜伯克的外孙。难怪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母亲要带他迁往新阿不旦。
最重要的是,这次我终于明白,就是因为罗布人将托克塔阿洪视为实际上的族长,他守望的大玛札在很长时期内成了罗布人的“根”,罗布人最后的圣地。托克塔阿洪在40年代去世,他去世后,玛札才无人主持了。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不愿带外人惊扰玛札。而玛札就在前往老阿不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的路边,所以他们从不主动提到老阿不旦,有意识地回避还有一个老阿不旦这个情况。所以新阿不旦才被当成唯一的阿不旦。
库万·库都鲁克是我认识的罗布人中唯一出生老阿不旦的,而目前仅有热合曼才知道这个大玛札的具体位置——这是我的“独家发现”,因为热合曼早年曾在大玛札作经文学童,就随托克塔阿洪住在玛札。在罗布泊探险中,托克塔阿洪原本相当活跃,可自从斯坦因离去后,他就失载于各种探险记,这样说来,我估计他是在1908年以后出家的。
我为这些发现兴奋不已。突然,一个想法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我进一步问:你知道昆其康伯克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吗?
不。热合曼不知道。
可也许我知道!我差一点喊出声来。我猜想,罗布人最有权威的首领昆其康就安眠在这个大玛札。这才是它的“神异”所在。
哦!这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罗布人中的一员了——最后的罗布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西部贫瘠、板结,寸草不长的热土上收获了如此丰饶的精神食粮!
按说到了99岁高龄,处变不惊是基本的涵养。但这次与热合曼相见却时见他感情外露。热合曼对自治州领导说,我是最早来看他的人。而自治州领导当即决定,在9月中旬请几位罗布老人到库尔勒作客。而且具体作了布置。就在这个月,当地政府(36团)开始给米兰的罗布老人发放生活补助,每个月250元。这都是极有政策水平的举措。
这天下午,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两个罗布老人。在乌斯曼·尼牙孜·亚瓦西家,我们都为老人的质朴、纯真感动了。
亚瓦西是老人的外号,含义是“老实人”。我们进入他的小院时,这年近百岁的罗布老人正蹲在墙边剥玉米。
我们谈到了曾栖息在罗布荒原的新疆虎。
斯文·赫定大概是比较详细报道新疆虎情况的人。他在1900年听罗布人说,这些年来,老虎越来越少,那是因为荒野上蚂蚁突然大增,小老虎一出生,就受到蚂蚁的“群起攻之”,它们专门以带着胞衣的虎崽为食。即将生产的母虎很难找到没有蚂蚁的地方产仔,所以老虎日益减少。这是有关罗布荒原动植物的食物链曾被不明原因的意外因素打乱的意义深远的信息。
为此我特意问老人,你听说过老虎吗?你见过老虎吗?他笑着回答:“我见过老虎,那是在电视上(他指指摄像机)见的。”他的笑容是无法形容的。这是99岁睿智老人的笑容,这也是9岁天真孩子的笑容。哦,“亚瓦西”——老实人,这个外号真是贴切之极!说来惭愧,在这之前,我的理解是:只要别自己明明水深火热,还赌咒发誓要解救世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别给小脚老太太送一双冰鞋,这就算得上老实人了。见到乌斯曼,我才明白,“老实人”在这里就是罗布人的同义词。
有关奥尔得克的情况,主要就是乌斯曼提供的。他说,奥尔得克和自己父亲尼牙孜是好朋友,奥尔得克生前常来他家作客。在1934年寻找“小河”时,就是奥尔得克来约他一同前往的。他不能准确回忆出奥尔得克死在哪一年,但他说应该是在五六十年前,也就是1940年前后。
可以说,我在新疆从未有过此行这样好的翻译。翻译吐尔逊·马木提本人就是罗布人的后裔,我们这次采访的两位罗布老人乌斯曼和亚生,就是他父亲的两个哥哥,他的伯伯。以往在采访罗布人时,常常难以沟通,甚至出现过一句话在场有几个懂维吾尔语的就有几种译法的情况。但这次能有如此透彻的交流,有如此具体的收获,与吐尔逊·马木提在场关系极大。
第二天是1997年8月29日。我重访了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新渔村。在阿不旦,我和热合曼一样激情难抑。他领我寻访了自己早年的家,寻访了新阿不旦伯克的官衙。
他一一指出了故居的“火墙”、壁龛,他从自家的羊圈里抓起了一把还没有被风化的羊粪。也许他已经回忆起正趔趔趄趄地学走路的自己,曾依在火墙上等待家长护持,也许他还记得他在壁龛里藏匿过从古道旁捡拾的几枚古币,他一定无数次在寒风中守候在羊圈前,等待自己特别亲近的羊羔归圈,他一定屡屡依偎在炉火前,凝望着炊烟,结构着对未来的企盼。没有人说得出自己的童年究竟是何时结束的,但热合曼老人想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想象中回到过童年的美好时日!
古道的另一侧,是新阿不旦村村民的公共墓地,他的亲人和同乡就由浮沙掩盖,在这芦苇、红柳之下长眠不醒。
那个清真寺轮廓基本完好,显然直到村子被放弃的一刻,它还是村民精神困惑的评判所。
清真寺北侧不远的地方,是炮台的残骸。1984年还硬挺在风沙中的仅有的一堵墙壁已经扑倒在地。它显然是在驻军撤离后(也许就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不太久),就为人拆毁的。
在新阿不旦村的村头,我见到了一个馕坑淤。你不能小看这个不起眼的黏土台,这表明在新阿不旦时,罗布人已经向塔里木河下游绿洲的居民学会了更多的东西。而放牧、农耕在他们的生活中,也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他们的主食已经不再只有鱼一种了,馕开始端上了餐布。
在阿不旦村背后,就是阿不旦河——依列克河。从目前的情况完全可以推想当年河流奔涌的气势。热台曼老人在这里徘徊的时间最久,也许他还在思忖,为什么世代相依的阿不旦河、喀拉库顺湖竟突然弃此而去,再不回还。也许他还在掂量,如果此刻河湖回归故址,罗布人会有一个怎样的前景。
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热合曼的步履。有关阿不旦的往事,在我已经不再是个难解之谜。我恍若觉得,与我一同重访故地的,不止是热合曼,那清癯消瘦的库万,满眼忧思的塔依尔,表情冷然的艾买提……与我并肩而立。而那久经沧桑的昆其康伯克,忠厚朴拙的奥尔得克,常常陷入苦思冥想的托克塔阿洪……就站在我的面前……
……天一直阴着,可我们的心境却充满了阳光,我们已经拨开了历史的阴霾,驱散了岁月的风霜。在我们的心头,罗布人的天空是晴朗的,西部的天空是开阔的。
离开阿不旦村,我们的车队又驶上大漠。
碰上一个缺乏想象的人,就凭眼前的景物,他是不会相信这儿曾是水乡泽国的;他是无法理解罗布人所经历过的辛酸、梦想和跌宕的。望着满目黄沙,满目凄凉,我这样想道:
罗布人离开自己的家园阿不旦,一定是一个痛苦难言的过程。当年热合曼放弃新阿不旦故居最终搬到米兰时,想必把一切可用之物都随身带走了。可时隔一个花甲再重返故地,他却发现其实自己什么也没有带走。
阿不旦是罗布人的聚落地、罗布人的根。而罗布泊水域则是楼兰民族和罗布人的摇篮、婚床和墓地。无边无际的河湖化解着数不清的往事,稀释着因血泪、征战和仇杀而板结的沉渣;历史只不过偶因感冒而打了个喷嚏,它就升华为天上的虹霓。当罗布人的一部史书写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时,新的历史必然就要在新的环境下展开新的篇章。
离开阿不旦村,车队先向东,然后又折向北。
连依稀可见的小径也看不到了,车队在荒野择路前行。沙包渐渐连成了片,枯死的红柳在沙包上扎煞着,就像铁蒺藜,能扎破汽车的轮胎。一方面,满目凄凉,令人感极生悲,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竟不时可以看到羊圈和房舍的遗迹,尽管它们的年代并非久远。可以肯定,我们现在经过的荒凉死界曾是人类昔日的家园。
我下了车在前方探路,并不时用人力修平沙岗和死红柳枝梢。
车队停在一道沙梁前。在附近寻找路径时,我看到阿不旦河河床又出现在我们的左侧。在这里,阿不旦河依旧气势俨然,风沙未能掩盖它的遗蜕。但走向则折了120度,成了由西南流向东北。
我走到河岸,发现这儿的河道竟比阿不旦村附近还深峻,在一个河湾处,有个深达三四十米的深潭,深潭当然早已干涸,但干涸的潭底是铁灰色的,看上去就好像是湿泥。那就是板结又皴裂的河底。就在河湾附近,出现了一条浅浅的、轮廓不清的小河,是从阿不旦河主干上分出向东的支流,但这支流并不长,也就是一望之遥。
我站在沙岗上,面对着古河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不知什么时候,热合曼老人来到我身后。我指着这浅浅的东向干河,问:“玉尔特恰普干?”
热合曼点点头:“玉尔特恰普干!”
原来这就是新阿不旦村民赖以维持生计的那条为捕鱼而挖成的运河。库万曾告诉我,“玉尔特”是山羊的意思;“恰普干”是人工挖的水道。罗布人为了捕鱼,就在定居地不远的地方,挖一条水道,从河里引出水来,当然也引来了鱼。然后就把水道封死,让它慢慢地干下去,水也就变得带一点点咸味儿,据说这样微咸的水里生长的鱼特别好吃。水少了,以致恰普干里的鱼就像过去节假日前夕公共浴室里的人,挤都挤不开。罗布人守着恰普干捉鱼,简直比从鱼缸里捞还容易。
热合曼凝望着那个河湾处的深潭,对我说,这个地方就是整个阿不旦河最深之处,当年水性再好的罗布人也从未探到过它的底。罗布人甚至相传这就是阿不旦河河神潜藏处所。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本已干涸的阿不旦河又来水了,热合曼和十几个最留恋故地的乡亲(有乌斯曼兄弟)立即回到了阿不旦村居住。但没过多久阿不旦河又滴水全无了。他们不相信罗布人世代依水而居的生活已经终结,还死死困守在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就靠这个深潭的积水维持生计,不愿离去,希望有朝一日,河水还会再返回。他们甚至认为这个深不见底的水潭是上天赐予的,是与罗布泊连为一体的。可直等到这个水潭也干得见了底,阿不旦河河水仍然没有回到阿不旦村……
望着阿不旦河和河湾的水潭,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知道热合曼领我们来到玉尔特恰普干,是因为当年他在这里种下了颗粒无收的希望,是因为他把青春岁月都寄存在这个深潭,是因为他在困守不去时形成了固执的念头,相信迟早会在这里与阿不旦河重逢!
荒野上又刮起一阵旋风。一道尘柱直伸向苍穹,它就像干渴的大地伸出舌头,去舔吮天空的云彩,它也像忍无可忍的大地,向造物主提出挑战,它更像大地在向上苍递交一份新的契约,在这份契约中人类在新的纪元开始后将有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义务和境遇。
从刚才的荒村到眼下的干河,这就是在西域探险史上名著一时的新阿不旦渔村的疆界。望着无际的荒沙,没有人会费心在这个死界寻找生命的绿色。
在这次来米兰之前,我曾认真做了准备,并一一翻检了自己的笔记。我在1992年5月1日的笔记的纸边见到了一行自己随手写下的字迹浅淡的小字:“问库万阿不旦的含义。”但显然我并没有获悉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如此有名的地名“阿不旦”究竟是什么意思,则是任何书籍里都未曾提到的。这次一来米兰,我怕忘记了,在见到热合曼时,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已经不能就此向库万请教了,如果今天世上还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热合曼了!
我首先问:“喀拉库顺这个地名是什么意思?”
热合曼摇摇头。“它……指的就是那片地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期望得到答案,因为在100年前,斯文·赫定就这样问过托克塔阿洪本人,并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米兰呢?”
热合曼又明确地摇摇头。“它的来历很早……”“那么,阿不旦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阿不旦……”热合曼老人慢慢地,但是明确无误地说,“罗布人把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就叫阿不旦。我们每在一个地方定居,准备长久居住,就把那儿叫阿不旦。”
“它的准确读音是阿不旦还是阿布达勒?”
“当然是阿不旦。阿布达勒那是别人骂我们罗布人的话,含义是‘叫花子’,‘要饭的’。我们绝不会把自己的家园叫阿布达勒。”说到这儿,热合曼也许是回想起什么美好的往事,他轻轻地说,“阿不旦,那是我们的幼儿园和学校,如果不是水没有了,我们现在还会居住在那儿……”
……我和热合曼一同凝望着久已生机全无的昔日家园。如今,“阿不旦”这个“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只存在于罗布老人热合曼的回忆中和我的想象里。是出现了什么差错,才使这死气沉沉的荒漠与阿不旦这个生机勃勃的名字联系到一起?
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斯文·赫定的阿不旦,最后的罗布人的阿不旦!我的阿不旦!
难道天意、玄机就这么隐秘难测?难道塔里木绿洲世世代代承受的磨难还没有到头吗?究竟是什么力量或机缘为罗布人设下了这勘不破的世纪之谜?这里面所隐含的深刻意蕴,究竟有谁能够看穿呢?
我们离开玉尔特恰普干荒凉的裸岸,走向已经发动的越野汽车。虽然没人知道此后的路在哪里,但车队即将启程。
我心中很清楚,我还在旅途中。我迟早要踏上前往老阿不旦——昆其康伯克的阿不旦的路,踏上前往奥尔得克的“小河古墓”的路,踏上寻访托克塔阿洪的大玛札的路。在前方,我的路还很长……
望着天地相接处的地平线,我心中充满对生活的眷恋之情。我突然想到了佛教典籍《地藏十轮经》里的警句: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思似秘藏……
苍穹瞑目合十,大漠喑哑无语。
……
告别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光凭悬想,不身临其境,你不会知道与年近百岁的世纪同龄人分别时有多少感受涌上心头。
在那浓阴如盖的葡萄架下,我向热合曼道了再见,并说:“您一定多多保重!过几年我还会来看望您!”
沉思了好长一会儿,热合曼讲了一段话。这话先打动了翻译吐尔逊·马木提,吐尔逊迟疑了片刻,一字一句地复述给我听:
“再见!我等着你。可我已经很老很老了,下次再来,如果见不到我了,请你在心里记住我!”
听到这儿,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