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看云》在《收获》栏目中独树一帜
蔡:《收获》杂志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开辟了很多散文、随笔专栏,我个人很看好你的《沧桑看云》专栏。请问这个栏目是你主动提出为《收获》杂志社设置的,还是编辑部邀请你开辟的?
李:专栏是他们找到我的,因为我跟《收获》的关系,是在九十年代初在它上面发过几篇文章,比如《人生采访》栏目里关于巴金的《云与火的景象》。
蔡:三年十八篇专栏文章写下来之后的结果,和你最初的设想是否相吻合?或者说有没有留下某些遗憾或别的什么?
李:应该说整个过程还是达到原定设想的。但是开始构想的时候,尤其是第一篇不太理想。开篇《沙龙梦》,题目很好,角度很好。但是,由于第一次写这样的东西,驾驭得不好。本来是想提出一些问题的,但是没有展开,结构也不太理想。现在看起来,那篇文章写得有点做作,不是很自然。要谈一个文化问题,但又没有展开谈,包括沙龙和集团的关系,沙龙和形成文化人思想风格的关系,也没有谈得很好。第二篇开始写人物,好像是写郭沫若的。我觉得就得心应手了。毕竟长期写传记,写人物,就比较成功。这十八篇当中,写人物的,我自己感觉很有一些满意的作品。写文化现象的有这么几篇,一个是沙龙梦,一个是“五七”干校,一个是红卫兵。后面两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都还是当时别人没有谈过的。有一定的见解。结构上比较满意。用这种抒情性的,又是纪实的方式来写。其他每个单篇,基本上以某个人物为主的。
蔡:文化现象还有两篇,一篇是谈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争端,一篇是现代文人和基督教的关系。
李:对,这些也都是综合性的题目。后面的比较实,是立足于实基础上的抒情。而《沙龙梦》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虚,是我不太满意的一篇。本来是可以再展开多写一写的。对我个人写作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台阶。过去写长篇传记,我比较满意的是写胡风集团的那篇。比较成熟。现在看起来,还是站得住的。写的是一个新的领域,另外抓住的这个题材、这些人物。包括当时花在采访的时间,用了好几年,以后就不大可能再有这样的机遇。抓住这么好的题材,过去了十几年,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还是有价值的。而且,我当时体验到超越了他们当事人的局限,基本上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历史现象,包括文人之间的矛盾和矛盾中的关系、和历史的关系,还是有一定想法的。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作品。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年基本上是在做翻译。然后,写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那是考证两人关系基础上的故事的叙述。而用随笔的方式来写,还是集中从《沧桑看云》开始的。对我个人来讲,还是一种新的形式。越写越顺,尤其是到第二年更成熟些。第二年以后,主要是写跟“文革”有关的。当时很多刊物不准发跟“文革”有关系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觉得《收获》是很有见地的。但他们又不是盲目的,为了炒作,而是作为有思想性的文学刊物,对历史事件应该有所发言。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游记,或者是些史料、掌故,还是应该有批判性的角度看待历史。这样,我就在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集中写了田汉、邓拓、吴晗、老舍、胡风,还有红卫兵、“五七”干校等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人物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去世的,或者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这在别的刊物不敢发,《收获》成了一块阵地。
蔡:你的文章眼光独特,而且角度很好。运用可读性的笔法,写一些有历史意味的、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人物和事件,充满了思考精神和悲悯情怀。不论在当时,或者在今天,都不失其多方面的价值。在《收获》众多的栏目中,独树一帜。以单个的人物或事件,串起众多的人事,繁复交错的星体。以达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性把握,这是功不可没的。“沧桑看云”总共连续刊载三年,一十八篇文章。《收获》有没有给你限定开三年和写哪些人?
李:没有限定,出于我的自由。我的文章不可能是余秋雨的风格,讲的是大随笔。但我写的还是小的人物传记或叫人物速写,当然后来有的打乱了,也有归入散文里面的,或者叫大散文的概念。我觉得也可以往里面放。这个问题不大,没有具体要我写谁,就按照我的思路,因为李小林也了解我这些年写作风格和一些选材的标准。编辑过程中,我的稿子她看得很细,提出了一些不同见解。包括一些校对,把关是很严的,但是选材基本上是由我自己选的。我觉得好的刊物的编辑,他的重要性不在于出个什么题目给你写,而在于怎么把作者的智慧、作者的感情或者作者的想法让他自己去捕捉一个好的点。就是让你自由,但实际上又在引导。这种引导是潜在的,因为刊物在那里摆着。我在这上面写文章。第一我就不能不考虑文学性。我不能完全按照传记文学写,或者按纪实文学写,或当成报告文学写。《收获》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过去在我们看起来是境界很高的作品。从文字上,从剪裁上,从选择的人物上,都有很高的文学标准,不仅仅是思想学术的标准。这对我来讲,实际上是很大的促进。虽然没有说让你写什么,但你在考虑问题时,别看一万多字,两个月一篇,实际上很累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过去很熟悉的。但你决定要写的时候,你还得看看。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要投入这篇文章。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我写文章特别快。就是写《沧桑看云》的时候,写得特别慢,修改特别慢。考虑到一万多字的文章的容量,废墨不能太多。尤其是专栏,我觉得专栏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考验你的毅力,你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一篇两篇蒙得过去。一个专栏下来,你要是不加把劲,是没资格的。李小林找到我开专栏,本身就是对我的信任。从我来讲,我要尽量做得很好。所以,那三年真的写得很辛苦。她并没有说开三年。她实际上让我一直开下去的。写完三年,为什么自己提出停下来呢?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写了三年之后,自己觉得恐怕难免有一些雷同的东西了。从抒情的方式、结构、选择的人物方面讲,我自己觉得应该停下来。因为过去的东西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如果还硬这样挤下去写,当然还有一些人物应该写、值得写。我后来用别的方式写了。但是,当时按专栏的方式写,写了三年之后如果还继续这样,很可能读者会觉得乏味了,或者厌倦了。从刊物来讲,我觉得三年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的时间。三年比较合适。如果再开一年也可以开下去,但很可能就成了强弩之末。创新的、有新意的东西就差一些。所以,我主动提出来写三年。让我也休息休息。我有一个习惯:一件事干上几年,我就停下来,做点别的事。然后,再返过头来写。因为跳出去可能思路更开阔一些。所以,我停下来之后。过了一年,后来我又主持《陈迹残影》专栏。有一点《沧桑看云》的路子,但基本上还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具体的人来展开,挖掘资料的工夫花得大一些。另外,在叙述上更具体一些。当然就文章本身的成就和水准来讲,可能还比不上《沧桑看云》。三年停下来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再写一年,写上五个人物、六个人物,也可以写。但就很难超过前三年,这样见好就收是最好的。
我最关心的是人物命运
蔡:《收获》编辑部选择作者很有眼光,而且也很见胆识。他们邀请你开辟《沧桑看云》专栏时,既没有限制你写几年和写哪些人,也没有要求你要写成什么样子?
李:没有,都没有。过去我给他们写过沈从文、写过巴金,都是李小林提出的具体的写作意见,觉得我比较适合这样写这些人物。要写之前,我都会跟李小林商量。说我下期要写什么人,她都说可以。她不干涉你写什么,而且修改也不是很多,主要是在一些字句表述上和对一些观点偶尔提出点意见。她对作者是充分的信任和理解。因为我发表作品比较早,第一本主要写的是巴金。1988年出版了我影响最大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三十几万字。后来,给他们写过两个单篇,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两篇文章和《沧桑看云》的路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想他们找我之前,也看过我写的沈从文、巴金的文章,包括写沈从文的那本书。批评我的作者说,巴金是《收获》的主编,而我写过巴金,然后找我开《沧桑看云》专栏。所以,自然而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当时在文坛影响最大的还是那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当时发行十万,在全国,海内外,台湾版,香港版,日文版都出来了。后来,我这么多作品,从单纯的个案研究和从一本书的影响来讲,都超不过胡风集团那本书。因为采访了几十人、上百人,很多人都是不可能再见到他们了。能够体现出我对资料的搜集把握,是当年和贾先生、陈思和一块做巴金研究时训练出来的。后来又做记者,采访,可以比较全面地体现出一种综合的素质。《沧桑看云》则更加突出文学性。我到上海也和李小林聊过。《收获》上发表的余秋雨的随笔、还有很多老人写的散文,一个作品出来之后不是过眼烟云,而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再来看,也还是有味道的。所以,《收获》让我写东西,跟给另外一个刊物写东西,我的感觉就是标准和压力就是不一样,考虑是不一样的。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也给其他刊物、报纸写书评,给《读书》也写过。给《读书》写,我肯定要考虑它的学术性风格和表述方式。给《收获》写,文学性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订《收获》的读者不一定是学者,不一定是对学问感兴趣的。但是,既然《收获》找我写,她当然希望我有一些学术见解,而不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个文学故事。如果那样,她完全可以找小说家、散文家,而不必找我。所以,学者散文是当时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潮流。我自己是报纸编辑、记者,办副刊的。过去也写过评论研究文章。所以,《沧桑看云》出来后,有些评论文章认为是学者散文,说我是作家、散文家、记者三者的结合。不管怎样讲,对我来说,我是把文学性放在第一位的。体现时不是靠虚的抒情的东西,而是靠学术见解,运用史家的笔法去观照人物。因为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历史,但又不是考古、考证的历史学,是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纯粹研究作家作品不太一样。和我在日常生活中和人接触得多,和老先生们接触得多,和看回忆录多有关系。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回过头看,对自己的写作、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来讲,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有很多人研究现代文学史,写过这些人的评论,包括我笔下的很多人物,有很多专著在,但基本上是学者型的论文、论著,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我基本上是按照我个人的写作方式。从这一意义来讲,我还是跟《收获》中很多作者的特点比较接近,是个性化写作方式突出一些。
蔡:的确,我们都读过很多二十世纪文化名人的文章,要么是迷恋于理性辨析的论文,要么是些轻浅空洞的散文文字,很难把二者融合到一块。在当时,能够把学术见解和文学情感结合地那么好的文章是不多的。你的写法走出了你自己的路子。我觉得,《沧桑看云》之后,也许你没有完整的大段时间再来写较大的书了。你所开的专栏,或者写的文章,基本上是沿用《沧桑看云》的路子。当然,多少还是有些变化的。但是,总体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不知道我的看法你能不能认同?
李: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在那之后,只写过一部长的书,是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的传记。但是,叙述风格也基本上是《沧桑看云》的风格。包括这两年我写的关于丁聪的、关于王世襄的、关于杨宪益的,都是两万字左右的文章。包括《陈迹残影》中写冯亦代、黄永玉、戴望舒,基本上也是按照《沧桑看云》的风格。《沧桑看云》的主要特点是这样的:第一,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主观的叙述角度放进去,不是完全纯客观的、第三人称的写法,而是有第一人称在里面,有我自己对人物感兴趣的过程,我自己感受的过程,对事件扫描的过程,让读者读起来更亲切、更近。它的毛病会是把我自己的主观见解强加给读者、给别人。但是,我的大部分叙述,还是并不脱离资料的。我把叙述的资料,都隐在背后。读者完全可以根据我的叙述来得出见解的。他也可能跟着我感情叙述的起伏或者思考的过程,或者随着我寻找某个人物人生轨迹时,跟着走。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读者容易进去,很容易接受,不会有距离感,和我一起对人物命运发出感慨。对瞿秋白、吴晗等这样的人物重新认识,我是根据人物是什么特点选择叙述的东西。像瞿秋白是更客观一些,更有距离感一些,感伤的东西多一些,《秋白茫茫》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因为过去写革命家,写瞿秋白,还没有那样写过,感受的东西多一些,因为没有接触过。写吴晗是理性分析更多一些。
蔡:你在写作中不仅把个人主观的东西放进去,而且好像也尽量选择适合不同人物的情绪方式来进行描述。
李:对。一个朋友,经常读《收获》的读者,是汉中写诗的。他给我来过很多信。他看完我在《收获》上发的文章,认为我的文章有一种诗人的诗意在里面。我认为,诗意就是用一种比较有诗情画意的方式,来描述人物的命运。我是做记者的,有时候需要有一种现场感,又是做资料的,需要一些考证的东西。另外,还是搞研究的,肯定需要一些思想、想法。这样,几者结合起来,写人物就可以更加丰富一些,更加能够打动人。这些我还是比较注意的。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和《沧桑看云》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蔡:除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在你的写作中是不是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李:对。我从事写作和研究也有将近二十年了,一个就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个就是《沧桑看云》,其他作品都比不上这两部。对我个人来讲,这几年要想发展或超越《沧桑看云》所达到的已有的东西也很难。它已经形成了,要想再超过它,恐怕自己也没有能力了。无非是再扩展些思路,多写些别的形式的东西。这两年做了一些和文人没什么职业关系的东西,希望思路能够更开阔一些。这两年主要是做些外国人在中国活动情况的资料的搜集、翻译和写作,更向历史靠拢。去年翻译了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命运的书,扩展一下,搜集当年传教士的后代的情况。单篇的文章写得多一些。最终在这方面要有所超越或突破。我想也许过个五年、十年,用这种方式,或者更简略的方式写史书,应该是可以的。
蔡:你是想用诗性的笔墨来描绘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这会是很有意义、也很别致的著作。
李:用这种方式来描绘中国某个阶段的历史。我看了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借鉴大量访谈的资料写成的。这基本上和我过去的路子是一样的。现在戏说历史的书很畅销,或者是很严肃的正儿八经的历史书。但还缺乏一种以人物为主的历史书,像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把一百年穿起来写,也许挺有意思的。或者是换一个别的视角,或者以事件叙述为主,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所以,我去年写了一组《在历史现场》,反映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像“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等,用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和传记打乱揉进去。这些文章都写得不长。我只是作为一种探索做做看。这也算是对《沧桑看云》的一个新的发展吧。但基本上也没有超越《沧桑看云》,因为有时候你写东西消化完了,或者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了也很难再改变。
蔡:这么多年下来,你虽然也同时在不断积累,但长时间的大量喷发之后,的确是难以避免被淘空或者出现雷同、重复的写法的。
李:一会儿长篇,一会儿又弄短篇,短篇的也有一两万字。
蔡:每一篇都是一个凝缩的人生史、一个文化史。而且,都可以推而广之,用于观照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和思想轨迹,从而形成一个高峰迭起、星体纷呈的地形图或宇宙圈。这是一个浩淼的艺术空间构架图。
李:好多单篇都值得扩展成一本书的。
蔡:我看到你后来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大概就是这种意图的局部体现。
李:那基本上都是又增加了万把字,以图片为主的,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考虑到运用照片和文字相映衬。图文的结合,我们过去往往只讲到版式上的意义。其实,它的照片提供的内容,是更多的文字所难以表述的。
蔡:它有自己的空间。包括在文学期刊中,我就认为不仅文字文本是一个个小空间,构成的整个文字大空间。而且,封面、封二、封三、封底,也构成了图片空间。这绝对使杂志更加立体化、多面多维,更有可看性。我们现在常常强调已经进入一个读图时代。如果还忽视封皮、封面的精美制作和全局性策略,那是很落伍的做法。我觉得,这不简单是文学杂志的包装或装帧问题,而是对一本杂志的总体认识和内涵的丰富定位问题。你加入图片,陈述曾经用文字表达过的人物,我认为不只是增加图片而已,而是丰富了每个传主的精神世界。提供给读者更多维地进入人物的途径,传达了更为博杂的思想信息和与过往历史衔接、想象的可能性,不同人也许就得到了更加不同的感受和创获。
李:过去这方面我们注意得不够。过去图片只是单独的东西。如果我们加些文字说明、补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和文字形成一种互文关系,这样读者读起来可能更生动一些。
《陈迹残影》想唤起人们对文本的重新认识
蔡:你在一九九八和一九九九年又在《收获》主持了《陈迹残影》专栏,选取家书、日记、笔记、题跋、辩白书这些更加私密性、更加个人性的资料入手,你自己也写了有关的文章。请问设置这一专栏有些什么想法,和《沧桑看云》专栏有什么关联或者不同?
李:我想,和《沧桑看云》不同肯定是有的。写《沧桑看云》的过程中要看很多资料,也和出版社合作在编一些书,主要侧重于回忆录,搞了一套“火凤凰”文库。后来,还有“沧桑文丛”,里面有回忆录,有传记,还有一些日记和信件。写《沧桑看云》时,很多老先生都把资料、档案给我。我自己平常、这些年也到旧书摊搜集、买到不少东西。过去研究历史,尤其是这几年,比较火的是什么呢,就是写杂文或者写一些言论。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说得越激烈越好。而且,喜欢有很大的历史观或者跟回顾有关的东西很多,而且一谈就是一百年,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价值。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光注意大的轮廓的东西是重要的。包括我的《沧桑看云》的有些文章,也是在这方面占了便宜的。像我对红卫兵发表言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当历史到细节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不清楚的。而且,到每个当事人的回忆录时,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根据我多年接触的经验,因为我们根据印象写时,有时就不是很清楚的。何况过去了几十年。那些老人写的回忆录,肯定是有所删节、有所回避的。它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回忆录也好,传记也好,它们都不可能完全真实的。只是相对的真实。这时候挖掘大量的信件、日记就非常重要。对于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治运动史,过去做过,但却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写完《沧桑看云》之后,我就在这方面加大力度。这几年除了给《收获》写专栏之外,我还给《百年潮》、《寻根》杂志写些东西,还跟出版社合作编了一系列的丛书和整理了很多资料。包括田汉的档案、赵丹的狱中交代、冯亦代在重庆时候的日记和一九五九年当右派时的日记等等,整理了十来本,陆陆续续准备找出版社出版。
蔡:寻找大历史、大叙事框架中疏落掉的个人性和真实细节。
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找回历史的细节》。我编“沧桑文丛”和“历史备忘”丛书时,包括我正在编写的一些历史档案性质的书,我把它叫做“个人档案”。正是处于世纪之交,很多人都在喊大的口号,搞大的场面。而我认为,越是到这种时候,越是应该对于那些小的细节的东西进行关注。比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包括一九五五年对胡风集团搞外调。那么,到底搞外调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组织构成是怎么回事。有时候这种细节考证,往往能够引发出大的文章。像陈寅恪,能够从柳如是那么小的人物,写出那么个大时代。把考证仅仅当成书斋的、学院的、没有意义的,是不对的。当然像《红楼梦》那样琐碎的考证,我也是不看重的。但像“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全国知识分子命运史之类的资料,我是觉得搜集得越多越好。同样一个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譬如我做过一本不同人谈周扬的书,同样一个人谈周扬某个阶段的时候,回忆时谈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的情况怎么来处理呢?最近到美国国会档案馆,看到一个专门搜集口述的,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很多大学都有口述资料馆。中国这方面很不注重,缺少同一个事件应该有录音,应该有不同人来探讨同一个事件,对事件的看法归在一起,供后人研究,或者供自己写东西,这都是很有用的。我在整理冯亦代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写的日记想到,过去我们对大后方说了很多。但是,对大后方为什么能产生茅盾的《腐蚀》、能产生巴金的《寒夜》,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能够成为小说,正好是一个空白。而冯亦代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写的日记,正好是那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通文人每天感受的是什么东西,每天情绪化的东西是什么,完全可以感受到是不是一种灰色的心情,正好和茅盾、巴金,包括当时夏衍写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话剧能够相互对应。看上去好像是史料,实际上它对于解读历史、解读文学、解读文学史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东西应该越多越好。这两三年,我在这方面下的力气比较大一些。另外,我现在又在把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翻译出来。在策划一套书。我这次带回来不少,别人也借给我一些,很多在中国工作过的,包括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回去后,都写过很多在中国采访过程中的回忆。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左翼作家,像斯诺、史沫特莱、朗特,而对于中性的,甚至是反共的作家、记者的回忆录,我们基本上没有翻译过。我翻一翻他们的东西,有些很有意思。如果把他们的东西翻译过来,那么对同一个事件和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又会有些新奇的发现。应该有出版社、有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蔡:这样对于还原当时的语境下发生的事件,多了些个人性的细节捕捉。应该说,更确切、更翔实了。因为作者是当时历史的旁观者、在场者、目击者。他们的说法,或许要比某些党派、某些政治家做出的结论,多了一份可靠性。当然,也不排除作者个人的倾向性。这里面会有复杂的因素。但是,至少对于还原历史,应该是多了一双注视的目光,来自异域的、他者的目光。我们在审视历史往事和历史人物时,会更客观些、更真实些。做这种事情,需要有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后人负责的精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业。我读到你在《收获》上发表的《陈迹残影》只有五六篇,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发在其他刊物上?
李:对。在《百年潮》发了一些。因为后来事太多,头绪太多,所以那个地方不能保证每期都有,后来我跟李小林说停两期,先做一年再说。
《收获》的专栏讲究文化韵味
蔡:你不仅在《收获》发表文章,而且也和很多杂志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请你比较一下《收获》上的文艺随笔和其他刊物上的文艺随笔有什么不同?另外请你比较一下《收获》与广东的《随笔》、北京的《读书》等刊物。
李:我想《收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有一个连贯性和一个系统考虑,包括《人生采访》,包括《河汉遥寄》。它基本上能够通过这几个专栏文章,把整个中国文化界、中国文化人的状况都包括进去。重要的文化人物肯定都有一篇。而且,都是请的比较重要的人来写。这一点恐怕是别的刊物目前所比不上的。它能够约得来,它能够约到最好的人,写一篇关于某个大家的印象记、回忆录,或者是悼念文章。广东的《随笔》更注重文章的锋芒和思想性,而对文学性是不太讲究的。而《收获》的随笔是绝对讲究文学性的,比如余秋雨的文章、贾平凹的文章,包括阿城的文章,它每个专栏还是有些新意的。像大散文,就是靠它的专栏给弄出来的。包括《沧桑看云》。它有几个专栏之后,就把某类文体的文章提到一个最高的水平。《收获》的文学地位,是不能以发行量的多少来建立的。它的发行量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它的影响力更超过它的发行量。今年的几个专栏,像贾平凹的,包括陈村的对话,等等,它首先要求的是文学性,不敷衍了事,不降格以求的,把得很严。虽然不给你发号施令,但是他们偶尔提出来的一点或者跟你商榷的某些意见,那都是很到位的、很关键的地方。这都是编辑的眼光过人和编辑部的风格独到。另外,它的专栏随笔,都不是追求外在的轰动,而是很讲究刊物的文化韵味。这也是和其他刊物不一样的。
蔡:《收获》现在基本上是四分之三容量的小说,四分之一容量的散文、随笔。它靠散文随笔来保持它的文化品位,来体现刊物的人文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色彩比较浓厚的刊物。虽然经过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它基本上保持了一种跟政治有一定的距离,但又不是媚俗的方向,我暂时用第三条道路来概括《收获》所走的路。
李:像去年的“走近鲁迅”专栏,很多刊物都在谈鲁迅,但还就是《收获》上发表的文章最有分量。这里面不是简单地说几声鲁迅伟大,还是实事求是的,有个人见解的,个人化很突出。个人化是知识分子最佳的写作方式。我觉得个人化也是《收获》很重要的特点。它从策划、组稿,到物色人来写,都不是匆匆忙忙的,草率行事的。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当然,也不是说别的刊物就不行。但是,从实力各方面来讲,可能就比不上《收获》。
蔡:除了两个专栏,你还在《人生采访》中发过三篇文章,在《河汉遥寄》中发过两篇文章,那么是不是都是李小林是你的作品的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在你的写作中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起了些什么作用?
李:就是她,其他人没有联系。前面也谈到了。她从来不会说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她给你充分的自由,充分的信任。然后,写的过程当中或者看了稿子、校样之后,哪一段或哪些地方不合适,她会再打电话跟你商量,非常认真,而且非常到位。我也记不清了。有时候是引文,或者引文不准确,或者是有些话她觉得是不是换种说法更好。这是经常会交流的。但是,具体每一篇来讲,她不干预,你自己怎么写都行。当然,会有些字数不要太长,或者不要太短,这个有时会说。
蔡: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我想再提一下,请你谈谈对《收获》这份杂志的总体性评价。它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是当代文学期刊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扮演什么角色?你也是巴金研究专家,我还想请你就李小林对巴金在编辑杂志上的精神理念上具有怎样的承传关系谈谈看法。
李:我想这不是一份哗众取宠的杂志,不是一份随风转的杂志。它比较稳定。它有自己的见解。有一以贯之的风格。从巴金、靳以创刊的时候起,和当时全国其他杂志相比,就可以看出它不是一份趋炎附势的杂志。相对来讲,它就比较注重作品文学性。像发了老舍的剧作,发了那么多的小说。我们小的时候,看它“文革”前的那些长篇小说,印象还是比较深。当时强调长篇,但是文人色彩是很浓的。巴金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办出版社、办刊物。靳以也办刊物。他们是比较强调同人刊物的特点。虽然《收获》是新中国成立后办的,属于国家的刊物,作协的机关刊物,但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继承了中国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后同人刊物的特点。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特点在里面。它有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有相对稳定的编辑,性情比较接近,这是它的突出特点。同人刊物,文人来办刊物,它有什么特点,它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大量作协机关刊物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角度、思路,这一点《收获》是比较成功的,而且是比较突出的。
蔡:它好像既在体制之内,又企图超越出体制或者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度、疏离感。
李:对,就是这个,若即若离。
蔡:它不可能完全脱离,但又想坚持自己的一点儿什么,这里面好像确实是继承了现代文学阶段文人办刊、文人办出版社的思路。
李:所以你说李小林继承了巴金什么,我就觉得,对于作者,她不是阿谀奉承,或者为了拉一篇好稿子降低刊物的标准,或者为了刊物拉一个名家。我觉得在她眼里没有什么名家,或者以名家为标准,大部分稿子还是以质量来要求的。另外给作家提供一些阵地,比如在小说发展方面,它是有前卫思想的。但它又不打旗号。这个刊物不是靠打旗号来吸引读者的,而是靠多年的积累。实际上它成了一面旗帜。实际上它的旗号和口号是在刊物内部、在作品里面体现出来的,包括开随笔专栏。实际上它是在领先时代潮流的。大量的随笔专栏很火,几个专栏,包括叶兆言的,实际上它是靠专栏在引导中国散文随笔写作的潮流。但它从来不说,不像有的刊物是靠外在的旗号、口号来吸引人。这一点就是巴金当年的传统。现在还继承着。当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是这样。它也没有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扶持无名青年。从来不喊口号的。但它就扎扎实实的一本一本地出,一套一套丛刊出。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收获》
蔡:你从研究巴金起步,至今已有近二十年。后来又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你对巴金主编的《收获》是很有感情的,也是比较熟悉的。想听听你对《收获》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没有感到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李:要说不满足的,那就是它的市场经营方面有些欠缺。
蔡:就是在扩大自身的影响方面,缺乏力量和办法。
李:在扩大影响和市场运作方面,李小林还是太文人气了。实际上它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八十年代应该想方设法创办一个收获出版社。结果他们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现在恐怕就办不了了。其实搞一个出版社,你好多作品自己就可以出版出来。这才是把三十年代巴金的那一套真正学到手了。又有刊物,又有出版社,结合起来。你想《收获》的经济效益,各个方面都好办。现在很多作品发表出来,让人家出版,你的效益受损,对宣传刊物、吸引读者各方面你就不能发挥大作用。你像巴金当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下面几个刊物,同时做,你想它的作用和影响多大。当时中国的体制,私人办出版社或同人出版社很容易的,不像现在什么都要批。但你要是早一点,有远见,搞一个出版社,应该说效果更好。发展它两年,你还可以再扩大成影视公司,好多电视剧,你也可以搞。
蔡:它还是想保持编辑部人少,它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当年创刊时靳以定的规矩,生怕人多难办事。靳以当年可能有他的实际处境和想法,今天是不是应该有些变化,或者说该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是《收获》的掌门人不能不思量的。
李:你可以有不止一个摊子啊。像现在再申请一个出版社就不可能了。但是它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经济上也能持平,也还是不容易的。在中国这么个市场,只要坚持自己的做法,《收获》也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市场的。和其他刊物比,其他刊物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收获》又有前卫思想,也发前卫作品,又具有比较稳重的风格和姿态,包括发棉棉的作品,包括当年发余华、苏童的作品,甚至王朔好的作品也是在它上面发表的,实际上它是领先文学潮流的,但它不张扬,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蔡:不像其他刊物有编者的话,有前言后语,就让作品自己去说话,让专栏,让发出来的作品的影响力去传递编者的声音。
李:它是另外一种风格,含而不露。它从来不搞活动,也不开笔会,也不开作品讨论会。它什么都不搞。就像巴金说过的,作家靠作品存在。这一点也是体现他们继承巴金的思想传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它也是不搞什么活动。那时候他们办《文学季刊》、《文季月刊》,也是靠作品说话。
蔡:还是跟现代文学相互衔接下来的。
李:巴金传到李小林,有这个风格在,而其他刊物是没有的。其他的办了刊物,基本上是由新的人来做。他们没有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的精神传统。巴金也是受“五四”影响的,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是唯一的一个刊物,其他刊物好像没有这种人事关系和传承关系。
蔡:《收获》多少年来人事变动比较小。不像其他刊物,整改、重组、换上一批新的人马,人事变迁屡屡更迭不定,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恍惚感,难以形成持久的恒在的精神力量,影响力自然也远不如《收获》。
李:《收获》至少到目前还是几十年的传统,一以贯之,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
蔡:我真的有些担心《收获》,一则怕它老态萌发,落伍;二则怕它被新潮同化、侵蚀、淹没,变了味。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李:李小林也在考虑新问题,电话联系的时候也谈起过,反正都得过这个关。但是市场化也不是绝对的。像别的刊物感到发行困难,办得不景气,《收获》还能够存在,而且还能很好地存在。说明它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市场化形势下它自己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就是说,有时候你不做广告,不做宣传,不做市场操作,可能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宣传效益了。因为读者订刊物,还是需要作品的质量在,喜欢你这个刊物,他就是喜欢你继续这样。但是,我是觉得刊物本身应该是不变的,应该增加刊物之外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事情,看怎么来做。
蔡:同样都是被认为人文精神比较浓厚的刊物,《读书》就在封底或者插页中刊登了很多广告,当然它还是些跟新书有关的广告。但是,《收获》就任何广告都不做。尽管也有不少人为《收获》出过主意,建议他们可以适当地发些文化信息广告。但是,《收获》始终不为所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李:它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一旦开了个口子,做起广告来,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广告商的左右。比如这一期要登什么,下一期要登什么,就由广告商来决定,而不能自己做主了。而且它是文学刊物,它也要考虑到可能有不少读者不愿意看到广告。当然作为刊物来说,编辑部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刊物之外的活动,或者就刊物本身怎么来做再创造,这是下一步可以考虑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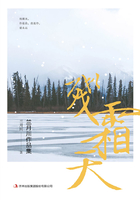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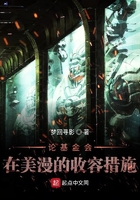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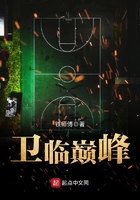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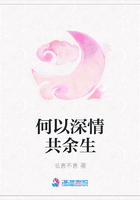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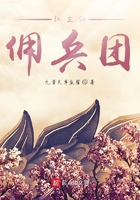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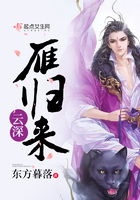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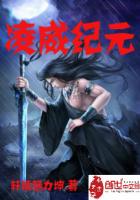


![[空间]学霸向前进](https://i.dudushu.com/images/book/2019/09/26/0535000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