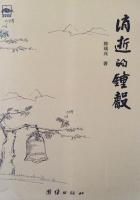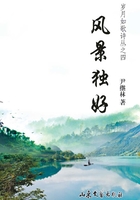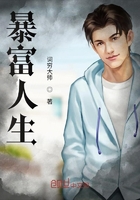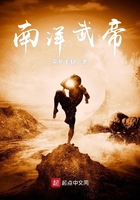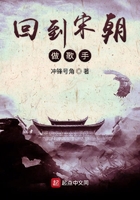《收获》的编辑·读者来信论麻袋
蔡:你在《收获》杂志社工作了多长时间?
邬:我是一九六四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在那里。
蔡:一九六四年《收获》复刊的时候就去了?
邬:复刊的时候就去了。后来到一九六六年,文坛上,我们这些单位都不行了。那时候 “四个面向”,上海搞了几个面向,把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出去,把作家协会都砸烂了。作家协会的这些人都到乡下,等于是劳改一样的。我们是到学校去。作家协会又成立了,开始工作,有几个领导在那里,把我们又调过去,没有多久就到了一九七八年,我是一九七八年调回去的。
蔡:为再次复刊做准备。
邬:去了之后,那时候作家协会只有几个干部,还没有作协,总的叫上海文联。后来作家协会的人多了,才成立作家协会。当时有写《红日》的吴强,有萧岱,他们早就在了。要我回来,继续在《收获》编辑部工作。一九七八年年底开始发稿,编稿子,一九七九年一月刊物就出版了。我到了一九九七年的时候退休。
蔡:你在《收获》工作了近二十年。
邬:一直没有变动。现在萧岱已经去世了,吴强还在他前面走的,下面还有一些离休干部也都退了。我是作为《收获》退休人员的第一个。编制是这样的,离休的人员归作家协会发工资,我是由《收获》来发工资,因为我们是自负盈亏的单位。《收获》碰到我这样的是第一个,单位发给我工资。
蔡: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的时候,编辑部都有哪些人?
邬:《收获》是一九五七年创刊,到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就停刊,跟我们没有关系。当时我是在上海的《文艺月报》,就是现在的《上海文学》。
蔡:你是什么时候到《文艺月报》去的?
邬:一九五九年去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我们来个下放干部政策,我也下乡了。实际上这就把一些不要的人处理掉了,不回来了。《文艺月报》是两个人,我和一个姓杨的就和大家一块回来了。我还在作家协会,他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我就进入到《文艺月报》编辑部工作。一九六〇年的时候《文艺月报》就改名叫《上海文学》。
蔡:《上海文学》怎么过渡到《收获》的?
邬:《上海文学》当时已经搞不下去了,发行量只有四千份。到困难时期搞不下去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才改名叫《收获》。实际上是《上海文学》转成《收获》,整个编辑部转过来。这是第二个《收获》,但是属于上海作家协会。
蔡:第一个《收获》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办的。
邬: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原来编辑部的人,经过那么多年都不能够再回来了,也老了,包括罗洪,当时是编辑部的小组长,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编辑部主任。那时候不讲究这些。还有王道乾,他已经死了,是法国留学生,他是搞理论的,当时是作为《上海文学》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可能这些人都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我,郭卓。
蔡:孔柔?
邬:孔柔跟一九六四年《收获》没关系的,他是后来来的。当时《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人比较多,有一大帮。实际上一九七九年搞《收获》,老的人就是萧岱、郭卓,还有孙毓安,是搞美术的,我,后来再回来一个老的《上海文学》的编辑杨友梅,是我们作家协会前任党组书记的妻子。
蔡:罗洛的妻子。
邬:他们都到青海去了。因为罗洛有问题,后来要回来,经过萧岱同志的同意,就回来了。杨友梅不是《收获》原来的人,不过是《文艺月报》时候的人。她和我们一样转到《收获》编辑部。只有这么几个人是老的,后来孔柔,李小林是这个时候来的。
蔡:一九七八年来的。
邬:我们组成一个班子,就是吴强、萧岱、郭卓、孔柔、我、孙毓安,临时组成一个班子,马上发稿,马上设计,马上找出版社,找印刷厂,当时找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来代理我们编辑的印刷任务。我们全部印刷的东西都交给它,钱也是它挣的。
蔡:那时钱还是好挣的。
邬:好挣!读者渴望看书。
蔡:你们最高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份。
邬:他们出版社在全国有三四个地方进行印刷,因为光靠上海印来不及的,加起来一百二十多万份。钱都是出版社挣的,我们也很清楚。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能力接管过来,我们只拿很可怜的一点钱,一期拿两千块,两个月出版以后给我们,作为编辑费,我们的工资是作家协会发的。《收获》丰厚的利润我们没有得到。到了一九八六年的时候,我们忍不住了,坚决把它弄回来,当时年纪大的萧岱同志有点不放心,认为我们以后接下来不行了怎么办,没有饭吃。
蔡: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邬:我们都比他年轻,李小林比我还年轻,我们大家都说没问题,一定要自主经营。萧岱也是民主的,就同意了。后来搞起来很好啊,但是已经赚钱很少了。当时两百五十六页,一块钱一本。前面赚一块钱赚得开心,他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赚钱赚得好。一百万本,一本赚一毛钱都不得了,大头都是他们赚的,我们小头。后来我们自己在发行的时候,刊物的价钱都在上涨,我们也上涨,但开始我们也害怕上涨,一上涨,印数就要跌下去,这是普遍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看到我们那个数字是不会跌下的,因为各个出版社、各个地方都是需要的,因为巴金在主编,名声很大。销量始终保持在十万册左右。去年开始涨到十二块钱,当时也考虑到会不会掉下,但是觉得不会掉,因为有那么多的图书馆都需要,特别是学校,都是要看《收获》的。尽管涨到十二块,比《十月》等刊物还要高,但也没有受到影响。
蔡:这个数字比较稳定。
邬:说明已经稳定了,到了最低的限数,就是这么多了,不必发愁。《收获》在经济上稳定下来,对发展《收获》是非常有利的。《收获》一出来,特别是连着发了好几篇大胆的文章,对平反作家积极支持,发表他们的文章,影响很大。当时有很多读者的来信,都在《收获》编辑部。当时我们都来不及整理,只能把它们放在口袋里,比如《大墙下的红玉兰》放一个口袋,《蹉跎岁月》放一个口袋,只能这样。
蔡:《收获》人手有限,没有专人有时间和精力来对这些材料进行搜集和归类,真可惜。像《收获》这样的名牌大刊,牵涉到的人和事,还有作品,都很有学术价值、文学史价值,让资料流失是非常遗憾的。
邬:当时要忙于日常工作。都经过我手,我只能用信封把它们套起来。要紧的大家赶快看一看,不要紧的就往里面塞。
叶以群和魏金枝·上面的压力·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头
蔡: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的《收获》,当时是叶以群先当了一段副主编,然后再由魏金枝当呢,还是两个人同时担任当时的副主编?
邬:两个人同时当负责人。那时候没有讲副主编的,就是领导。
蔡:巴金是主编,是肯定的。
邬:巴金是主编,那是按原来的接下来,就不能改,后边这些副主编都没有明确。
蔡:不像现在写得那么清楚,而仅仅是负责人。那萧岱呢,他当时的身份是什么?是编辑部主任吗?
邬:萧岱也是。当时就没有明确的说他是编辑部主任,不见诸于文字的。当时《上海文学》的时候还有小说组的、散文组的组长,到《收获》的时候没有,因为没有几个人,还要分什么组呢。到后来,吴强也是负责人,萧岱也是负责人,没有具体的职位。
蔡: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第二个《收获》的主要负责人是叶以群和魏金枝。请谈谈叶以群的印象,他对《收获》做了哪些工作?
邬:我跟他们坐在一个办公室,一个叶以群,一个魏金枝,一个萧岱。叶以群不是每天都来的,而他们每天都来。他有事才来,掌握那些大家觉得有难处的稿子,比如这篇稿子该不该发,发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时候,他得带回去看看,整个事情由魏金枝和萧岱来考虑。发不发,下一期发什么文章,都由他们来定。负责小说的是罗洪,因为在《上海文学》的时候,她是小说组的组长。一九六四年,当时发不发稿,包括发头条的作品,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叶以群水平蛮高,非常认真,很负责,编辑看稿子没发现的文字错误,他都能够发现,并改过来。魏金枝是老作家,他讲的绍兴话,我们不太听得懂。辅导一些作者,需要修改他们的文章,都由魏老把他们找来。讲过之后,让他们带回去改,包括费礼文、胡万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由魏金枝和萧岱一块见他们,主要是魏老谈,萧岱在旁边帮忙。魏老这种认真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他年纪那么大,来上班,每天准时到。萧岱偏重于编辑部的内部管理,但有争议的稿子他都要看。还有,叶以群掌管整个有争议的作品,由他做决定。
蔡:就是说,最后由他拍板。
邬:拍板重要的文章。
蔡:当时巴金管不管《收获》的事情?
邬:一九五七年创刊的那时候,他是管的。一九六四年以后巴金忙于其他事情。
蔡:忙什么事情?
邬:出国啊,他出国比较多,编辑部没有给他看过文章。
蔡:就是说,具体的事情由编辑部的人在做,就是你刚才说的几个负责人在那里处理。一九六四年之后的第二个《收获》政治色彩很浓,密密麻麻的散发着配合形势的文章,政治对文学形成强暴,你谈谈当时编辑部的压力,怎样处理这一类稿件?
邬:当时停刊的时候,发刘少奇逝世的公告、生平,都是因为政治的压力。那时“左”得厉害,认为文学刊物怎么可以不发重要的政治的东西呢。上面要追究,宣传部不允许刊物独立发稿。当时完全是为政治服务,文学只能屈从于政治。为什么我们发呢,也就是上面有压力。
蔡:刘少奇的生平等,好像没有看到,倒是有越南反美的政治口号诗、宣传画。
邬:这些是政治的要求,不是编辑部的要求。是上面的意思。
蔡:上面到底是哪里?
邬:就是宣传部。我们作家协会是属于宣传部领导的。当时好像没有刊物逃得掉的,全国都是这样。这样办的刊物好看吗?现在看起来一塌糊涂。
蔡:第二个《收获》到后来简直不忍卒读。当然外界环境摆在那里,不是《收获》一家自己去迎合的。当时的负责人也是毫无办法了。
邬: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以后还有,那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面也有“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是《收获》当时领导的思想,也是当时整个气候的影响造成的。还有些束缚,还是在“左”的影响下。
蔡: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还在政治的左右中,还没有解放出来。
邬:当时有一张插画,在每一本刊物中都放进去一张。
蔡:我翻当时的刊物怎么没有看到,可能是掉了。
邬:有一张华国锋的插页。后来是逐步一点一点思想解放,开始发了一些过去不敢发的文章。
蔡:在大形势的影响下,《收获》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头,发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铺花的歧路》、《人到中年》等有影响的作品。后来继续刊登了不少力作,甚至是惊世骇俗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一九七九年复刊的时候,巴金还是主编,萧岱这时是副主编吗?
邬:巴金是主编,萧岱是副主编,这是明确的,过了几年才明确。他一直在负责工作,后来说一定要有副主编,萧岱就上去了。后来是李小林,后来又加上肖元敏,再后来又有程永新,是逐渐加上去的。
蔡:和其他刊物不同,《收获》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标明主编、副主编的名字,发稿的责任编辑更是至今没有写出来。《收获》现在有三个副主编,比其他刊物多,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邬:趁巴金还在,巴金是主编,后面的接班人都得有所考虑。李小林也已经五十七岁了,退休以后由谁来接班,她后面的名字就可以说明这方面的考虑。一个一个上去嘛。肖元敏五十岁不到,她是女的,那么到五十五岁退休,也可能干到六十岁,现在不明确。程永新现在比较年轻,他是男的,可以干到六十岁。那么四十几岁到六十岁,这段时间应该没有问题,保证后继有人。这不是用言论可以决定的,是一种设想,看不见的。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要考虑到后面的事情。
萧岱的变化·李小林的能力·巴金关心《收获》
蔡:你和萧岱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你觉得萧岱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邬:应该说,一九七九年复刊以后,萧岱对“左”的问题就逐渐看得清楚。我们的刊物经常要遭到宣传部的责问。比如说白桦的文章老是要遭到上面的指责,但是萧岱是敢顶的,逐渐顶起来。越到后面,他更不怕你了。因为大家的思想越来越解放了。他说:“有责任,我来负。”他敢于这样做了,这和以前有很大的变化。以前他没有这样的胆子,他是一点点逐渐意识到“左”的危害、“左”的厉害,所以他要顶,哪怕把我撤掉,我也要坚持下去,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宣传部有什么事情找上来,他总是一个人出来顶,因为宣传部来不可能跟下面的人接触,只会跟头头接触的。所以,那个时候他顶得蛮多的。那个时候会一下子说我们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了,说我们右倾,经常有的,总是有风吹草动,根据国家的形势、政治气候在变化。有一阵什么风,就来追究我们什么责任。一九七九年以后,特别是头几年当中,包括原来的宣传部副部长之类的这些人,都会抓我们的小辫子。他们自己思想不解放,但是下面的人思想已经在解放,而且逐渐地敢于顶他们。他们惟恐管不了,所以才会时时刻刻地来“关照”这个,“关照”那个。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章都给你看,给你看你也没时间,被你压着,我们发稿就成问题了。所以,后来萧岱是顶得比较多的。他敢于这样讲:“这个事情我来顶!”应该说,由于大家支持他,所以,他也敢于大胆地顶。后来就逐渐地比较顺利了。现在就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是规定不好发的,现在有哪个人敢讲这样的话?上面的人也不敢这样。
蔡:当时你们发了很多很有胆识的作品。
邬:《大墙下的红玉兰》是第一部描写监狱里面的情况的作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觉得不容易,因为我们从来不能发这一类的东西。写的人自己吃了苦头,自己经历过,所以等于是替作者平反昭雪。还有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是自由来稿,我是第一关。当时我们要编目录,根据领导的意图,由我来编。要发《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时,我们编辑部有人胆子小了,说是不是改个篇名,把“犯人”两个字去掉,结果准备改了。我知道这个事,就跟李小林讲了,说这个名字怎么能改呢,改了还有什么味道呢?
蔡:这两个字确实很醒目,改掉会使标题顿时变得极为平庸、平淡的。
邬:结果我们马上说服萧岱不能改,萧岱也就不改。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是逐渐解放的,编辑的思想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年纪大的比我们胆子还小。这类文章我们也很难发出去。首先我们得了解作者本人的基本情况。比较早的时候要这样做的。现在没有了,用不着再去调查作者的背景材料。我们当时写信给河南作家协会,要他们提供作者张一弓的具体情况。后来反映过来,说他这个人是造反派,是省委里面的一个造反派。河南省不好决定,就要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编辑部的吴强、萧岱,几个人就商量到底发不发这个人的作品。后来我们觉得不管他是不是造反派,关键是文章写得怎么样。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很好,而且是写得很有意义的。我们就决定发稿,后来得了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
蔡:回过头看,这还是一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而且,它的意义恐怕还不仅仅是一部好作品的问题。
邬:还有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也是写得很好的作品,也得了全国奖。反正对于平反的、反右的这些题材的作品,我们都做了一些工作。
蔡:你们当时走在前面,其他刊物都被甩下一大截。
邬:正因为走在前面,后来我们的发行量越来越高。登出来的全国优秀作品,《收获》占了那么多。第一届、第二届,特别是第二届有四部还是几部作品得了奖。正因为《收获》发了很多好的文章,反响很大,所以它到现在始终还继续有好的影响。
蔡:李小林是什么时候开始领导刊物的?
邬:一九八六年。
蔡:在这之前,她只是一般的编辑吗?
邬:是的。
蔡:一九七九年到李小林担任副主编之前,他们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邬:李小林是主编巴金的女儿,也是有经验的编辑所以凡事萧岱要和李小林商量了之后决定,发表哪些作品,哪部作品放到头条上,实际上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们是作为领导小组一样来开展工作。李小林年轻,出身书香门第,看的文章多,所以他要征求李小林的具体意见。时间一久,决策的事情就由他们来做。李小林当时来《收获》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她在杭州的时候已经在那里当过编辑,所以业务上也是熟悉的。她在《浙江文艺》干过,一九七八年调回来马上进《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后来党组决定要恢复《收获》杂志,就成立了一个班子。我那时在文联办公室刚刚待了几个月,吴强就把我调来,开始筹备,准备发稿。李小林、孔柔他们也从《上海文学》转过来,又把孙毓安找来当美编。后来郭卓来了。就这么几个人,开始编一九七九年的刊物。郭卓晚一点过来,孔柔是从云南调过来的,先在《上海文学》待了一段时间才到《收获》的。我们六个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把肖元敏调过来,她原来在《上海文学》,又把李国煣调进来,这样子人就多了。
蔡:这之前应该还有程永新,他是一九八三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就来《收获》工作的。另外,钟红明一九八五年也从复旦毕业来到编辑部工作的。还要提到,可能是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有一位毕业于复旦的唐代凌也在编辑部干过一段时间。
邬:我们只有五六个人的时候坚持了一段时间,一九八五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才决定自己搞。就在这个时候,才把肖元敏调过来。再把李国煣调进来。已经有一套班子了。不久,唐代凌就出国了。一九七九年那时候的六个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蔡:一九七九年那段时间你们的刊物办得的确很有生机,是谁在负责刊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稿子?
邬:当时主要是李小林。她认识的人多。像发表过作品的冯骥才、谌容、从维熙、张辛欣,都是作为她的朋友被介绍到《收获》来的。书信、电话来往很紧密,都是通过她联系。觉得文章确实好,才决定发。发得多了,他们就成名成家了。谌容也是在我们这里发了作品才成名的,连续发了好几篇,所以对《收获》的感情也深。《祸起萧墙》是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在我们这里发了作品之后,作者的名声变得很大。这些作者都环绕在《收获》的周围。现在有余华、苏童,好多,这些作者都是和我们关系比较近的。发了那么多的好文章,主要是李小林的功劳。都是通过她,这也就奠定了李小林做《收获》副主编的基础。发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她当然应该当副主编。当时我们要搞自负盈亏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萧岱不得不做出让步。他认为你们以后要吃苦头的,将来你们会失业的。但是我们认为已经有基础了,有影响在。当时出版社只是负责校对这一块,那么高的发行量已经让它们赚了好多钱。我们自己接过来,发行量照样还在,会比任何文学刊物都活得好,利润也高,福利待遇也好,而且很稳定。
蔡:再多谈谈李小林当《收获》副主编之前及之后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你是看着她怎样一步一步地成长的,而且知道她怎样一点一点把《收获》办得这么出色的。
邬:李小林对于《收获》的功劳确实不能抹杀的。有这么多的作者都环绕着《收获》,这都是通过她自己抓的。当然,下面的编辑也抓了很多作者。各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加起来就比较庞大。刊物办得好坏,就看你作者能够抓住多少。你没有作者,不写给你,不把好的稿子给你,你就办不好。现在作者都觉得我要把最好的稿子给你,为了你的影响,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影响,双方都有益处。李小林还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书看得多,文字能力很强。错误的东西她都能找出来,而且记忆力忒强,看过之后,她可以知道这篇文章哪个地方有问题,校样出来之后,她会及时地要编辑改正。这方面的错误她抓得很紧。所以,《收获》发表出来的作品,错误的地方很少。我们请人家校,要找水平高的。文字上、语法上的功夫,还是她强。很多人发稿时没有发现的问题,她都发现了。因为每一篇文章她都要自己校过。每一期那么厚的文章,她都要看几次。初样的时候要看,复样的时候也要看。翻一翻,找出了问题,消灭了不少不易发现的毛病。我们自己发的稿子也有错误,没有看出来,她也要讲的。不管是谁,她都讲,人家脸红也好,不脸红也好,她都公事公办。
蔡:就是说,她是很严格认真的,为刊物负责。
邬:我觉得她在文字上把关的能力很强,和她积累的语文知识是分不开的,和她家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有一个七八十岁的北京老作家写的文章也有错误,我们年轻的编辑没认真查字典,被她发现了,结果批评得很厉害。
蔡:我们刚才说了李小林的关系比较多,读的书比较多,眼光比较敏锐,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
邬:她从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很有修养,巴金的很多东西都是她编的,功劳不小。她有基础,比其他人当副主编的能力要强。她是现在《收获》的主心骨,主要的负责人。以后要是她走的话,这方面的损失,消灭错别字这一关,恐怕再很难能做到她那样的程度了。作协对李小林的能力还是蛮欣赏的。她来了之后,《收获》一直搞得很好。从复刊以后到现在,《收获》的影响越来越大。你作协的哪一个领导来搞,不一定搞得过她。她把《收获》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每一篇文章她都放在心上。
蔡:她的成绩,她在《收获》的影响跟她的父亲巴金有什么样的关系?
邬:当然和她父亲有关系。所以现在一定要挂巴金当主编。一九七九年以来他基本上不管了,但那时候他身体还好。我记得一九八〇年我们去莫干山休养的时候,他还是很健康的老人。《收获》的事情一直都跟他通气的,许多事情李小林要跟他讲,他都知道的。沟通得很好,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什么事情一讲就通,就明白。所以那时候还管一点,后来就逐渐不管了。但是比较大的事情,李小林还是要告诉她爸爸的。包括调人,调什么人,《收获》的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她都要去告诉巴金,因为他毕竟还是主编。巴金对《收获》一直挺关心的,所以,李小林的水平,跟她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两个方面都有关系。她的确有她自己独特的水平,超过我们这些编辑。她很敏锐,看得清楚,所以大家都听她的。她是冲在前面的,见识也比较广,所以刊物有她的功劳。
巴金的影响始终存在·遗珠之憾·让作品说话
蔡:请你多谈点巴金对《收获》的作用和影响。
邬:前面的影响大,前面奠定的基础好。就连给巴金种花的一个老花匠都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吃巴金的饭噢!”的确是这样,因为巴金的名字还挂着,我们当然是借巴金的光。应该说,巴金的影响始终存在着。
蔡:后期由于他的身体和精力不允许,或许影响了他对《收获》的直接关心。
邬:但是,有后继者李小林,继续贯彻和坚持巴金的办刊精神,广泛地团结了作家朋友,把《收获》引向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蔡:巴金后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从李小林身上体现出来。
邬:继承他的思想,然后继续发扬在编辑部的作用。一九八六年以后,他的精力就不怎么样了,到九十年代以来就更不行了。之前,有一两篇有问题、有争论的,李小林会讲给他听,他会发表意见。
蔡:《收获》有没有碰到遗珠之憾,比如好的作品被编辑部退掉,但被其他刊物发表出来,被证实是相当不错的佳作。
邬:应该说我们不用的稿子,人家刊物采用了,是正常的事。
蔡: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的确非常好的作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你们退掉,令人惋惜不已。
邬:应该说后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的作品是不太有这样的事的。
蔡:方之的《内奸》就是被你们退掉的?我想知道是谁经手的,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发表?
邬:那是萧岱还在的时候。具体哪个人看的,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这篇文章到过我们编辑部,这我是知道的。后来退了,我也清楚,什么理由退的,我不太清楚。现在应该说编辑部是鼓励有个性的作品,毕竟在开放的年代里,人的思想越来越自在。那么在以前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可能会觉得是个棘手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发出去,发出去是不是对自己会不利,这方面的考虑会有,恐怕《内奸》的考虑是在这些方面。
蔡:你在《收获》发过哪些稿子印象比较深?
邬:我发过《大墙下的红玉兰》,但是有些地方的文字,我没有好好斟酌。后来读者来信还指出来。作者自己写错的,“他”和“她”混淆,我也没有看出来。当时我还经验不足。这部作品在当时反响很大。后来我发的散文也有,短篇小说也有,中篇也有,但是影响都没超出从维熙的这部作品。我当时的工作也很忙,刊物的出版、发行、广告、资料的积累、读者来信处理,都属于我的工作。编辑部没人管的事,都是我来做,相当于做了不管部部长的工作。看稿的时间比较少,只能一半工作,一半看稿,事务性的工作多。现在分得比较清楚,几个年轻人专门看稿,搞财务的兼管来稿登记。我们当时都没有搞财务的,这些杂务都是我来做,我只能腾出一部分时间来看稿。
蔡:《收获》一九七九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编者的话》,没有《编后记》,不直接流露出编辑的思想意图,但它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方式,作为多年的老编辑,请谈谈《收获》的编辑风格。
邬:要看来稿的情况,风格很独特的稿子,被认为是特别好的稿子,或者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都会被重视。各方面都可以贯通的,没有一定要发什么形式的作品。各人自己看的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然后汇通起来,形成现在目前这样的格局。没有具体要求都要发意识流的,弄得工农兵看不懂。意识流的东西,我也看不懂。我还是比较习惯于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个人有个人的风格,我们没有强求一定要怎么做。个人自己喜欢的,你认为好的,领导也赞同的,就发。我们没有统一标准。有时候萧岱看不惯的稿子也是有的,程永新给萧岱一篇年轻作家的短篇小说,被萧岱否定了。我看过觉得虽然内容不怎么样,但是写得有味道,气氛也不错,发也是可以的,萧岱还是听了。所以,个人发的文章是按照个人的,没有统一的套路。《蹉跎岁月》是文艺出版社我一位朋友给我看的,当时叶辛还不怎么有名。《蹉跎岁月》发了之后反响很大,然后电视剧改编放映出来,一下子名声很大。刚开始是我给叶辛写信,说要发他的稿子的。
蔡:《收获》在文学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邬:文学史上的地位完全由作品来说话,看看发出来的作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突出的地方。我们发的作品还是站得住的。我觉得我们过去发的作品实在是影响很大的。现在我们没有傲气说:“我们一定要发最好的文章。一定要在全国都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文章。”作品的地位和影响要在发表之后由读者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