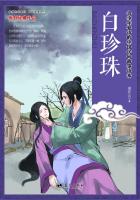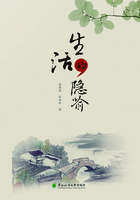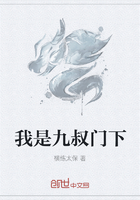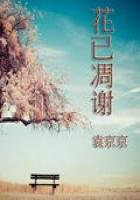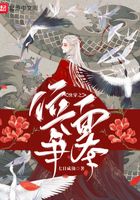当同一种人物频频出现在同一作家的不同的作品中,或者出现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这种平面人、空心人只能是作家们统一使用的符号,无论它有没有原型,无论它是被拔高了还是被扭曲了,也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类型,怎么可能具备真实感?我们常说要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可是那种类型化的人物却只是空架子,不但没肝没肺,甚至连脑子也不必有,只要能把你糊弄过去就够了。所以,当你看到打工妹(下岗女工)接二连三地堕入风尘,看到一个又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饱受屈辱又饱尝艳遇,你不要以为那是月牙儿、骆驼祥子阴魂不散,也不要以为他们与老舍先生一比高低,实在是因为这种类型太招人了,太有潜力了,反正你不写别人也会写,不写才傻呢。
由于“新乡土”、“新现实主义”在当下文坛的盛行,除去进城的农民工,我们还能看到一支可观的村长队伍。但是,同样令人失望的是,那些或姓张、或姓王的村长除了姓名不同,他们的做派、脾气甚至言行,都是那么相似,好像只要是个村长,必定一副德行,形同失去水分的面人,只是干巴巴的一块。从他们身上,你看到的多是奸佞、狡诈、伪善、恶毒,而且总是那么赤裸,不把人逼入死地绝不善罢甘休。过于概念化的写作,使作家不是在以写人、写人物,而是在写类型、写看法;同时也没有把村长放到现实中,放到农村的客观场域中。作家们不但让村长大权独揽,而且常把他处理成光杆司令,顶多配备一个文书。这样写来虽顺手便当,孰知不但削弱了作品的真实度,而且取缔了人物之间不可回避的复杂关系,忽略了生活应有的丰富性,也使作品失之于枯干。或许有人会说,作家塑造这样的村长只是一种艺术性的简化,没必要过于较真,可是我觉得,既然你打着“现实”的旗号,起码要基于细节的、历史的真实,离开这一点去“简化”,只会失之于草率、空疏。
如果向前追溯,村长小说的前驱大概以“农民作家”赵树理为著。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见到“村长”这一形象,而这些村长/支书既可相互甄别,也各具时代特征。赵树理不但注意到了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到了人物的个性,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实际的变化,因此赵树理的作品才被文学史家们津津乐道,而我们当下的乡村故事仍然匍匐在前辈作家的背影里,一群不同作家的用笔却远不及一人下笔的丰富。像赵树理那样的叙事策略、口语化的情景对话,乃至整体语言风格,在某些新生代作家那里可谓衣钵相传,甚至“村长”这一重要角色,也不是“新农村”的特产,而是用“山药蛋”抟制出来的,可惜的是,抟来抟去,非但没有抟出人样,反把原材料也给糟蹋了。何以至此?因为他们塑造的不是百态万象的人,而是千人一面的“村长”。
由此可见,在当下的文学生产中,制假售假简直就是一种程式化的朝阳产业,无论怎样经营怎样炒作,都难改它的虚妄和欺诳。有个爱放炮的德国老头,先说中国当代文学多是垃圾,最近又说中国作家大部分不是作家,而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不成功的话,可以下海赚钱去。”(刘若南:《顾彬:我希望我是错的》,《南风窗》2007年4月16日。)这两炮着实震了不少人,但也不过是道出了某种不宜言传的事实。在我看来,骗子不尽是那些玩文学的人,最大、最高明的骗子还是那些在空荡荡的织布机上忙得满头大汗的人,他们摇晃着光秃秃的梭子,宣称织出了最贴近群众、最体贴民间的绝妙好布,结果不但骗过了众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相信:那些花言巧语确是管用,虽然它不能遮羞,却能蒙上你的眼睛。
现实如何文学——文学如何现实?
无论提倡写贫困、边缘的小人物,为弱势群体代言,还是鼓吹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等,莫不基于一种认识:客观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它所蕴涵的必定是质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而非用来标榜作者自己本人身份的优越与道德的高度。然而,综观当下的中国文学,委实令人沮丧,虽然它披着一层层真实的外衣,却难掩其虚假、虚伪、虚妄,其油滑、夸张甚至变态的方式也仅只能摸摸现实的屁股,所谓的“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实则留给历史的其实不是社会记录,而是在社会中记录。这样的记录如何能找到客观的社会现实?如何能发现历史性的维度?面对现实,文学似乎越来越乏力,越来越无能,越来越滞后,只能像跳梁小丑一样娱人而至自娱,大肆标榜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只是伪现实主义。
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比我们所有人说过的话都丰富得多”。那么,面对如此芜杂的时代,如此丰富的现实,文学应该如何与现实同在,其穿透力应该从何而来?文学何为?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不容回避的问题。
首先,让文学回到写作者自身。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下生活、找题材,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我们习惯于“把心交给读者”,却不知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我们习惯于替别人寻找灵魂,却遗落了自己的灵魂!这种将自身架空的写作怎么可能发出真实的声音?中国作家习惯于置身事外,无论使用哪种人称,其实都没有“你”,更没有“我”,他们像是下意识地抹杀了“我”的存在,更不会让“我”真正进入到小人物真实的内心,只会兴致勃勃或痛心疾首地讲述“他”、“他们”的故事,让与“我”无关的“他”、“他们”出洋相、闹笑话,或者无助地哭泣。这个真切的“我”的缺席,呈现的是写作者自身的匮竭和羸弱,他没有足够的心灵领地包容并葆养现实存在,只会与所写的人物貌合神离。只有先把作者还原为人,把人物还原为人,才有可能写出贴近人心的作品。所以,让“我”返回文本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人称转换,而是精神的还乡,是灵魂的返璞归真,是与大地与万物生灵的自由倾谈。因此,作家对内在自我的关照,对本真生命的省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追问与体恤,才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起点,更是现实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石。
其次,在真实的生活中反刍文学。何为真实的生活?怎样真实地生活?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假象,也许我们听到的全是谎言,所谓真实并非身临其境就容易达成,它生长在你的信念里,甚或也在你的怀疑中。其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用心生活,有没有将文学置于生活。顶着“法学博士”学衔的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坚持住在贫民区,当过火车站值班员、钢铁工人、废纸打包工,甚至专为舞台上拉幕布的拉幕员,“只是为了同周围的环境和人们滚在一起”,从而“体验一下震撼人心的事件,观察人们心灵深处的颗颗珍珠”。正是靠着与生活“滚在一起”,把这样的经历当作“爱情事故”,他才会采得“底层的珍珠”,写出《过于喧嚣的孤独》([捷]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杨乐云、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赫拉巴尔曾说,为了这部作品,他推延了自己的死亡。他未曾想过为底层代言,只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现实,从而在仅止五六万的篇幅里,抵达了丰饶而又惊人的真实。再看我们的作家,有几个主动融入生活,有几个调动了全部的身心酝酿生活?我们只会功利媚俗地贴近实际,只会蜻蜓点水般贴近生活,只会居高临下地贴近群众,这种表面的、姿态性的、浅尝辄止的贴近不但于文学无益,而且破坏了文学的质地,使其尚未成型便已腐朽、坏死。世间只有一个赫拉巴尔,我们不敢奢望谁去照搬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把心灵完全打开,对现实生活给予充分的尊重与沟通,从一般现象、普通题材的窄门,向未知的广阔疆域挺进,从而获得真实的力量。
再次,在文学中创造新人、新生活。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绝非对生活的机械复制,更不是对生活的仓促跟进,哪怕是写历史小说,也少不了作家的主观创造,否则言何“创作”?李敬泽也曾谈到,中国小说作家“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他们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夏榆:《2007年度中国文情报告》,《南方周末》2008年2月15日。)。其实何止“自己的形式”,我们又何曾拥有“自己的内容”?很多作家似乎很明白该“写什么”,因为生活中的素材总也写不完,就像贾平凹所说,总有题材等着他,不用他找题材,是题材来找他。这样看来“写什么”的问题已解决了,可是,究竟是“要你写”还是“你要写”?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题材要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写什么”真能决定你的作品占尽先机?“写什么”未必一定要指向某个制高点,相反,我们总是看到有些作家不但自己粗鄙、低俗,还要放大那种粗鄙、低俗,不但把一切搞得俗不可耐、臭不可闻,还要教唆人们去欣赏那种恋污哲学、追从畸态生活。所谓作品的精神向度,仅是作者的个人“趣味”。有人写了一大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诗,可他所喜爱的可能仅仅是一种事物的名称,未必他真正热爱大自然。这个人之所以娶一个女人做老婆,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再如有礼赞佛陀,不在于他看到了众生平等,人的可贵,而是因为他懂得神像的威严,作为人可以拿出身家性命为之献祭。所以,在确定“写什么”之前,先要确立为什么写,如此,才有“怎样写”,才有你的取舍甄别和创造性超越。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段话我们大都耳熟能详,拿到现在似乎有些过时,但是,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恰恰需要从这最基本的要素做起,从真实的细节出发,去塑造真实的人物、表现真实的现实。太多的作家只会抄袭生活,太多的文学只会画虎成猫:那些人物看起来精神焕发、活灵活现,骨子里却是废人、病人、“死魂灵”;那种“现实”展示的不是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多的是画地为牢、不战而败,多的是物道、官道、钱道,少的是人道、心道、灵魂之道。可见,文学创新首先要立人、立心、立精神,只有写作者满怀激情,排除干扰,才能创造出独立、特出的作品。
总之,文学不是从汗毛孔排出来的,而是让心灵冲破种种拘限,在梦想和现实之间透一口气。
当文学遇到现实,当现实遭遇主义——伪现实主义批判之二
一
还是先从一场闹剧讲起吧。话说某作家发表了一部以“文人”为主角的“小说”,引来一帮“文人”纷纷对号入座,认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对他们的“恶意中伤”和“人格丑化”,因此,“数十名被伤害的作家无不愤慨”,其中一个更是怒火中烧,多次扬言要“打死”那个“给文坛抹黑”的“文学败类”,之后果真带人闯入该“败类”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围殴”——据自称挨打者发帖说——“其头部、颈部、胸部、手部多处受伤”。另据打人者自陈,他只是“打了他一个耳光,但绝对不是殴打。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这个耳光大家都叫好”。写小说吻合了现实——或者说冒犯了现实,竟被“现实”抽了一个耳光,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委实不怎么“文学”。我们不禁要问:小说却是这样写、这样读的吗?文学与现实,竟是中伤与被中伤、耳光与被耳光的关系吗?
因为写小说被人抓住把柄,甚至吃上官司,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尤其是这种靠吃窝边草增肥的“仿真小说”,更容易露出未夹紧的尾巴,让恼羞成怒的“现实”逮个正着。套用另一位作家的绕式“幽默”来说,就如同你以为逮的是兔子,其实是一只鸭子,你杀了鸭子,其实也没杀死,只是煮熟了,其实也没煮熟,因为它飞走了,其实也没飞走,因为它又掉到了鸭塘里……这种来自“现实”的小说就这样死不瞑目地返回了现实。当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诧异,如果乐观一点,还可以称之为艺术与生活的互动:虽然作家们炮制的“文学”形同槁木,但他们闹腾的“事件”却足够生动,为这个娱乐时代平添了许多搞笑的种子。所以,尽管文学(特别是小说)一再以非文学的形式搔首弄姿,非文学一再以文学的面目招摇过市,却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所谓“文学”,不过是一只人人可以得而烹之的兔子或鸭子。
所幸中国作家一向不甘寂寞,也从未停下奋勇前行的脚丫子,他们不急不躁,不等不靠,有条件要写,没条件也要写,生生用一支支枯寒的笔写出了一条条宽广的康庄大路。各路好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文学的油彩涂抹出的浮光掠影。“文学”的处境也由此日益暧昧,之所以还能不时引起“关注”,要么是一种感觉良好的自我幻觉,要么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狂欢,没有人在乎你是否文学,只要你敢于像那位什么姐姐一样把POSE摆得不屈不挠,自然会赢得海量的眼球和口水,从而获得空前的“成功”。作家们的大S造型一点也不比那些××姐姐啥的差——有走上街头挂牌乞讨的,有脱光衣服朗诵梨花诗的,有骂文坛是个屁的,有咒评论家为疯狗的,有抄袭抄进中国作协的,有愤愤然退出中国作协的……总之,就如一位老先生说的那样,只要著名作家,不必著名作品。不过,上述“文人秀”大都过于直来直去,缺少足够的技术含量,比较起来,还是那种不露声色的“无辜派”更显大家风范,他们善于隐在幕后,只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地现身说法,“万般无奈”地争辩几句。此番举动也很能产生品牌效应,不仅红了作家,而且火了作品。此类作家虽然为数不多,却俨如瀚海航针,宰控着主流文学的整体航向。他们大多遵行着质证生活、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写作品基本离不开人间万象、世俗民生,与常态的“现实”有着纠缠交结的紧密联系,即使某些钩沉往事的“历史小说”,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的烙印。比起素有神学背景的西方文学来,中国文学似乎注定要迷恋“一地鸡毛”的现实,注定要把“活着”、“受活”标举成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
好了,不再兜圈子啦,下面讨论阎连科。
关于这位作家,近来最让人振奋的莫过于网上流传的一个消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有八九要花落中国,并且,那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要被诺贝尔之花砸到的人十有八九该是阎连科。为了证明阎连科具备获奖实力,就拿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首发于《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单行本)粗略展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