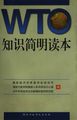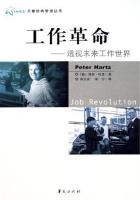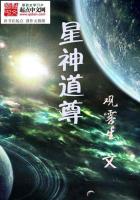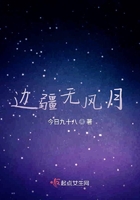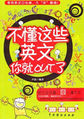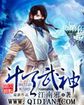曾经有过寂寞的倾听。2009年赴澳大利亚采访铁矿石贸易,到了海外方感受到华人的亲切。中钢集团澳大利亚公司陪吃陪喝,一位叫商木元的经理每天亲自给我们开车。其中有一天开了900公里,深入西澳大利亚腹地中西部地区去看矿场。西澳大利亚的路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两侧是雷火烧焦的树木和广袤的农场,弧形的地平线压下来,像在一个孤岛上开车。这么长的路,多少话也耗尽了。我们就默默地坐着,看路边荒凉的风景,也并不觉得别扭,寂寞也有自己的声音。每当现在想起老商,心中还是暖暖的。和你一起哭过笑过的人可能都会忘记,默默中陪你走了那么长一段路的人不会溜出记忆。
曾经有过五味杂陈的倾听。2010年丰田危机爆发后,我来到日本。英语尚一塌糊涂,更不用说日语,幸亏有一位朋友自愿做翻译,他就是曾在国内风云一时的王惟尊先生。他担任过健康元(太太口服液)、喜之郎等公司的执行副总裁,但因为牵扯进一场说不清的官司,2005年就到了日本。人到中年,从顶点跌到谷底,有家难回,有国难投。4天来,听他讲当年的恩怨,获得签证的波折,打工的艰辛,一次次陷入绝境。在他高潮迭起的讲述中,我把自己想象成他,恐怕已死过几次了,而他的传奇至今还未完成,依然有曲折的发展。分手的时候,我送他到地铁口,看他走进滚滚的人潮中。他乡当故乡,只是一种醉醺醺的潇洒吧。
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我的生命里,其中的多数今生都无缘再见,即使再见面,可能也忘了彼此的名字。然而正是他们和这份职业,让我走出狭小的自己,来到一个喧嚣而广阔的世界。
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回忆录中讲了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座城市叫做亚特兰蒂斯,因骄傲、自大和贪婪而沉没入海,有个水手在船触礁后,发现自己身在其中。而在这沉没之城里还有很多居民,每当星期天,他们会去奢华的教堂中做礼拜,希望在其他6天里可以把上帝抛到脑后。水手目瞪口呆,他提醒自己必须小心,不能被发现,否则他将永远见不到陆地与阳光,无法享受爱情、生命和死亡。德鲁克用这个水手来影射他的书名--《旁观者》。
而我是一个倾听者,想叫住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亚特兰蒂斯居民:嗨,停一停,告诉我你的故事。
(文/何伊凡,《中国企业家》高级记者)
雷晓宇:雷人雷事
来《中国企业家》之前,我有过一份不当真的工作。那会儿我研究生还没毕业,什么也没研究出来,眼看快要毕业了,就在一家还没出刊的时尚杂志找了份编辑的工作。杂志面市遥遥无期,而且编辑部里全是女的,于是我就很向往去一个男的多点儿的地方工作,要是每个月还能看见自己的字被拿出来卖钱,那就更好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研究生校友林涛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很鸡贼地问我,要不你来《中国企业家》好了,我们正在招生活版记者。后来,每每回忆此事,林涛总是得意扬扬,老觉得他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类似黑暗中的灯塔的角色。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北窑的单位打车来亚运村面试。我一共面试了4次。第一次是跟生活版高级编辑边杰。此人性格长相都有古龙遗风。他喜欢讲不高明的黄色笑话,还请我去鼓楼吃过一顿狗不理包子。他说,你来吧。于是我有了后面3次面试的机会。之前,我看杂志的版权页,心想,主编牛文文必定是个穿套装戴眼镜梳包头的女的,烟抽得凶,严厉得很,执行主编一个叫李岷,一个叫房毅,应该是像狄仁杰和来俊臣一样忠心耿耿的铁腕人物,一心辅佐自己心目中的女王。虽然我是个没什么职业野心的人,我还是禁不住想,这么看来,《中国企业家》还真是一个适合女性职业发展的地方呀。
最后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捡了100块钱。这像是某种神启,让我觉得此行必定成功。后来,如你所知,我对于几位领导的性别判断全都错了,更别提性格判断了。牛文文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你。我要么要一张白纸,要么要有丰富职业经验的人,像你这样两头不到岸的半桶水,我不感兴趣。”不过,他又说:“既然老边、李岷、房毅都已经同意了,你就来试试吧。”
照理讲,我自尊心这么强的人,听了这话应该很不舒服才对。但是我没有。还在学校的时候,我看了《三联生活周刊》出的一本叫做《十年》的书,一直揣兜里,走哪儿都带着。忘了里头哪篇文章写到,如果你要做记者的话,记得一定要跟比自己聪明的人一起工作。这话我记着了。后来我旁听过一次《中国企业家》的评刊会,有个红脸大汉迟到了,怯怯地坐在角落,默不作声,但是每篇文章最后都有人询问他的意见。他还是默不作声。最后他终于有机会证明他不是哑巴。他说,这篇文章怎么用了“悖论”二字,悖论是指逻辑上无法解决的情况,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应该叫做“两难”才是。我一打听,他叫刘建强,是生活版的资深记者。我愿意跟他一起工作。
2005年7月1日,我正式入职。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和刘建强一起工作。甚至早先几年,我们连正常交流都少得可怜。他是大牌,单位都很少来,来了也很快就回家吃饭去,来了也不说话。我曾经心生邪念,考虑要自制一件T恤衫,上书“刘建强请你跟我说说话吧”。我很快打消了这个不理智的念头。我不好意思惊扰他,显出一副蠢相。这下可好,作为一个没什么职业规划的人,我也没有老师。一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驱动力纯属本能的自尊心使然。那就是说,时刻提醒自己,以不要做出丢脸的事情为职业圣杯。
我是个记者,可是打一开始,我的工作就很丢脸。我的任务不是做活人,是做死人。领导们交代给我重要的使命,在全国各地寻访民国商业家族的后代,骚扰之,攀谈之,总结之,以把到中国商业命运史前史的脉搏。我对商业一无所知,花的都是蠢力气,经常上网用百度搜人名,打114寻找采访对象。我口吐白沫,每个星期都很焦虑,后来面部皮肤严重过敏,长了一脸流脓的红斑。《中国企业家》叫我毁容了,这该算工伤吧,我心想。可我不敢提出赔偿要求,因为我觉得我啥也没给人家贡献出来,心虚得要命,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地方支撑多久。2006年夏天世界杯,意大利球员在齐达内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咒语,结果齐达内就被罚下了。那会儿,我一天到晚琢磨死人的事儿,去上海出差,去扬州出差,去太原出差,可心里一直在想,嗯,到底什么时候辞职好呢?这话像句咒语,又像抖擞的秃鹫,在我那一片职业废墟上空盘旋不已,却始终不落地。这导致我一直处于悬而未决但来日无多的惊恐中。那时候,我很不快活。
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家》既有钱又有耐心。我一个菜鸟,竟然有机会去全国各地出差采访,尽管回来以后写出烂得要命的稿子,也没人指名道姓地骂我。半年以后,我报了个选题,要去绍兴做个师爷的选题。房毅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让我在申请出差经费之前先写个采访提纲给她。不知道我那时候脸皮为什么这么厚,我心知这是给我的最后通牒,如果还是不成,我也没脸再待下去了,不过我也不怎么紧张。我照常交了提纲,照常跟财务领了钱,照常去出差,照常写了稿子。不过,这一次的稿件好像评价还比较好。几个月之后,我又做了一个卢作孚的选题,又过了几个月,我做了一个国民资源委员会的选题,再过了几个月,我做了一个山西商帮的选题。牛文文在评刊会上击节叫好。我觉得没什么好的,不过既然他说好,我也就能继续待下去了。
后来,这些“世家”系列文章结集出版,起名叫做《中国商业老灵魂》。这书我不敢再看,也不敢叫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觉得害臊,觉得这是对我的才华的伪证。那时候,我对于写字还没开窍,更谈不上有什么个人风格。
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了一年半之后,我对于《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文字风格算是能够熟练把握了,对于领导们的选题取向也知道个大概。不过,我始终还是在做死人。我对于现时现世发生的商业事件和商业人物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当初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麦当娜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文本分析”,有时候我自己也纳闷,我怎么会来做一本商业杂志呢?
晴天霹雳来了。边杰被调动做了编辑部主任,生活组没编辑了。我开始陷入没人管的孤独工作状态。同时,牛文文跟我说,你不能再做死人了,再做你就废了,开始做活人吧。可是我特别困惑,活人在哪呢?我坐几路车能找到他们呢?我又开始感到秃鹫盘旋的惊恐。这时候有时尚杂志找我去做资深编辑,我有点动心。要不是觉得时尚这东西实在肤浅,说不定那时候我真去了。
我来《中国企业家》半年之后,编辑部来了一个新同事。这个人瘦得不像话,性格也阴沉得不像话。他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你,让人觉得他的基本修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过,偶尔开选题会的时候,他能说出一些新鲜的好主意,有时候还跟生活组挺有关系的。有一次单位聚餐,牛文文喝醉了,跑来问我说,要不你做生活组编辑怎么样。我吓坏了,惊魂未定之间,我眼角余光看到那人正在远处跟人推杯换盏,于是我说,还是丁伟来做生活组编辑吧。
就这样,丁伟成了我的直接领导。说是领导,其实说拍档比较合适。他身上总有一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感,老是把每一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在过。就职业危机感而言,我觉得在他脑袋上盘旋着的秃鹫比我的要多得多,也凶狠得多。我觉得他写字不好看。我觉得我的文字比他的水灵太多了。但是他是一个采访高手,对于我这么一个初入活人世界的人来说,这很重要。
从2007年年初到现在,我又在《中国企业家》的活人世界里干了3年。5年的时间过去了。一开始,我觉得我在这儿最多待半年。这些日子里,我老了不少,也漂亮了不少(这一点你要仔细观察才有体会)。我感到颇为得意,老边和丁伟从丈夫变成了爸爸,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可我还是这么年轻貌美。至于职业上的进步,我认为还是少提为妙。有什么好提的呢?我只不过花了5年时间练就了一些职业基本功,比如对于写字的热爱,对于阅读的习惯,对于和陌生人交流的技巧,以及对于我感到好奇的事情的好奇心。除了本能的自尊心,不做丢人的事情的自尊心,我还开始有了一些职业自尊心。我相信自己不仅是在做一件不丢人的事情,还在做一件能够让我产生自我认同的事情。我活了这么些岁数,真正做成功的事情其实没几件。
在《中国企业家》做了5年记者,这让我免于“有可能什么也做不成功”的危机感。现在我时不常还是能够感觉到秃鹫在我头顶上盘旋,空气燥热,阳光炫目,远处是一览无余的平原。我要再探索一些什么,才会觉得更快活。美好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而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文/雷晓宇,《中国企业家》高级记者)
蔡钰:“中企哥”不是一个传说
在我厮混的一个小圈子里有个切口叫“悬崖边”。但凡碰到恋不恋分不分、离不离婚不婚、着不着盛装回国、晚饭点不点水煮鱼等难决之命,人类们都会嚷嚷一嗓子--好悬哪,又崖啦--供其他安居乐业的酱油客们批阅一番。换工当然也属此类。2008年春节后,我干净利落地发了一帖,道是:我又跳了。
这次在悬崖底下等我的是《中国企业家》。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企业家》自己也正在悬崖边。听说我要过去,每一个相熟的媒体圈朋友的反应都意味深长得出奇统一:啊,那个,听说《中国企业家》老牛要走?我也老老实实地回说,我知道。
原总编牛文文要走,去创新刊。当时我只是简单地觉得,纸媒网媒,哪一家不是来来去去,川流不息?多大点儿事。
2008年是戊子年,不知五黄临不临太岁。杜亮是我的编辑,他以前就是《中国企业家》旧部,这次也是被找回来的一滴血,担任主编助理。我加了他的MSN,看一眼名字,他叫归队。我热血沸腾地想,啊,这狗血到发帅的人生。
当时的老牛还没正式离职。我在刚加入第一天,就得见了一次他指点江山。他召集全编辑部人员在办公室楼下的随想咖啡厅开新年战略筹备会,挥着大手,激情四溢地说:“今年是金融危机之下的天人交战年!!”
比起人事地震,更令我恐惧又期待的是见识老牛的雷霆万钧。此前我也在传媒圈漂了五六年,觉得“中企哥”不但占着江湖,而且占着传说,耳边不断能听到谁在那待了长达两年都没能转正,谁在那当着老板的面撕了稿子,最著名的一则当属总编牛文文乃是个喜怒切换极快、性情大鸣大放之人,他手下没有一人没被他骂过,被骂哭者不计其数。
2008年是戊子年,不知五黄临不临太岁,但五福娃合体在即,我决意低调生存。这里水很深,我想。
但恐惧的没来,期待也落空了。老牛已经开始筹备《创业家》,在《中国企业家》编辑部里,他恨不得是最风和日丽的一个。他有时路过我和王春梅的办公桌,说,“哈,春梅很好,蔡钰也很好”。面试时我叫他牛老师,他乐而受之,鼓励我在工作上要拿出杀气来。后来才听谁说,编辑部里提倡扁平,是不准叫老师的。在他的送别宴上,他跟我们一桌新人坐在一起,挨个点着说,虹秀会是刘涛,春梅会是谁谁……点到我时,他兴高采烈地鼓励说,“你未来会是一个老边”!
在老牛对编辑部主任如何统筹内部的解释声中,我抬头望了一眼我的未来,老边正在隔壁桌含羞讲着“黄段子”。我默默喝了一口茶。
我挺喜欢这里。人事变动中,设计部缺了美编,我的旧友T小姐刚好也想换工作,我就把她也推荐给了编辑部。
T是一个大胸而又极有主见的美女。我曾陪她去挑内衣,亲睹她试穿了一通之后,拽着我甩头而去,扔下话说:“你们家的70C根本就不适合我!”导购在我俩的背影中扶住墙,伸出绝望的五指在空中抓啊抓,泣声说:“小姐,你真的是70D……”
最终T成了我的新同事。
我刚进来没几个月,就遭到李岷翻来覆去、语重心长的鄙视,说:“听你平时说话稀奇古怪,为什么写起稿子来这么硬邦邦、全是财经腔呢?你要写得松弛一点!”
我的写作风格带着典型理科生的逻辑窘迫。我是理科生,没受过什么写作训练,最早实习时在《财经》给前辈们打下手,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又是在《财经时报》关注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与财技分析。一直认为财式写作就是体裁标杆:简洁、利落,尽量用数字说话,不添加主观色彩。每句话、每段话之间一定要有鲜明的起承逻辑,但同时又要把作者自己深深地埋起来,不留任何把柄。我懵懂地意识到了这些,却采撷不到其精华,于是行文一直有枯涩感。在李岷说之前我一直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但却始终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