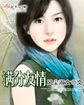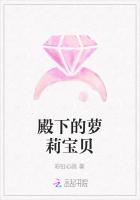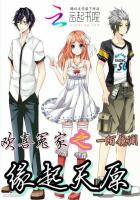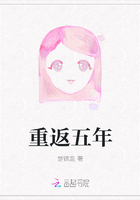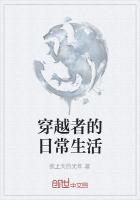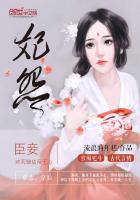一、原初激情与故土牵挂
与同时代的同龄作家相比,贾平凹的小说似乎一直保持着对乡土的热切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对商州“奇闻逸事”的“三录”,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初对高老庄、清风街芸芸众生的卑微生命与生活状态的浮世绘般的精雕细描,贾平凹始终将自己书写的焦点对准了他曾经生活过的中国的乡村世界。毋宁说在其30多年的创作生命中,故乡那片曾经稔熟的土地,近30年来故乡所发生的人事的沧桑变迁,故乡乡亲父老的生死悲歌,不仅成为作家笔下那个不断营建的虚构世界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支撑贾平凹走过30年文学辛苦路的“原初的激情”。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更多的是将一个乡土化的“中国”放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意识之中来审视和考察。这样的视角,一方面出自当时的知识分子对80年代的时代大主题的呼应,那无疑是整个民族、国家走向世界、追赶世界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身处在彼时彼地的中国知识者自身的局限所在。换言之,他们的思维乃至文化意识深深地被当下的时代所牵制,而那个时代是“改革开放”。“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实际上也深刻地折射出缠绕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梦魇”——一代又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性的集体焦虑,抑或是关于现代性的痴迷与想象。一个古老的中国或者是当下的中国成为“传统”的象征和指代,而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进步、政治制度民主、精神文化异彩纷呈的欧美世界则成为“现代”这一概念的最明晰而又直观的体现。于是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黄土地乃至黄河所隐喻的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遭到某种质疑、批判,而蓝色的海洋所指涉的一个现代化的西方成为“我们”追慕与艳羡的对象。在80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世界的想象中,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叙述,则被巧妙地转化为关于乡村与城市、文明与愚昧的讲述。在彼时彼地对中国现代化热切的全民企盼之中,乡村成为一个贫穷的、落后的、愚昧的“无望之地”。黄土地成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散地。它亘古不变的沉寂似乎又代表了一种封闭、滞后、沉闷和压抑。在乡村这面镜子的照耀下,城市则成为现代文明之光烛照之所在。它不仅仅是物质上比较发达,而且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方式,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化、更加自由而丰富的现代文明。
于是,8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对乡村和城市的书写实际上又更直接地呈现为对“文明与愚昧”主题的展现。于是在80年代的文学世界中,出现了“(离乡)进城”的故事模式。不仅仅陈焕生这样意识深处还残留着某种阿Q性格的农民带着自家的农产品进城出售换钱(高晓声的“陈焕生”系列小说),更多的出生在乡下,却已经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年轻的“乡土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黄土地,到城市里寻找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那一片空间。极为有意味的是,在80年代的小说中,当涉及年轻的“乡土知识分子”进城这一主题时,不同的作家几乎采取了相似的叙述策略。当那个虽然出生和成长在农村,却已经在现代教育的熏陶下而蜕化为一个“乡土知识分子”的年轻人,面对留守在乡土家园还是进城发展的人生抉择时,他们同时面临的也是关于情感或者是爱情的考验。毋宁说那是一次面对两个不同的女性的抉择:一个是纯净如水的乡村少女,一个是都市里的鲜活艳丽的摩登女郎。两个年轻的女性成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的隐喻和指代。换言之,对两个女性的选择也就变成了对两种不同文化的选择。犹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面对刘巧珍和黄亚萍时的矛盾(路遥《人生》),贾平凹笔下的金狗面对小水和英英时的痛苦抉择(贾平凹《浮躁》)。
贾平凹在8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一方面受制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意识。在《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等作品里,他设置了两组不同的文化观念的人物,而这些不同文化观念的人物实际上又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意识。一组是更本土化的传统的农民,他们还深深地沉浸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生活方式里,坚持着农民的“本分”;另一组农民则开始受时代风潮而动,开始慢慢地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之外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以这样的视角来看,《鸡窝洼的人家》讲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山野风情”的“****故事”。在两个家庭重新组合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类不同的农民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贾平凹的文本里,至少呈现出这样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当贾平凹处理“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时,并没有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道德式或者价值式的判断。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他更倾心于作品中禾禾所代表的新型农民。他们不再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农活上,开始寻求另一种介于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发展。那个复员返乡的金狗也并不安于做农民,而是“整夜地走动”,“三天两头的到白云寨,到州城里去”。他和乡亲们聊的也是“国家的事,联合国的事”。无疑作家本人对这样一种新型的农民是怀有某种期待的。有意味的是,当他处理那些依然坚持传统思想意识的农民时,却并未对其进行简单的否定。犹如《腊月·正月》里的那个以传统文化的坚守者自居的韩玄子,尽管思想深处有某种保守的因子,诸如他对待曾经是自己的学生而如今在农村办起了食品加工厂的王才的不满甚至是鄙夷。作家对其思想中“封建保守的部分嘲讽抨击”时,“又表现出深沉的感伤情绪”。毋宁说那是作家在触碰时代变革的“声浪”时,对以乡村世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新的审视和关照,以及对其沉寂不变而封闭循环的某种深深的隐忧。而这种潜藏在文本背后的隐忧在作家90年代的长篇创作中则直接呈现为一曲悲情的挽歌。
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中的夏天智实际上就是对80年代的《腊月·正月》里的韩玄子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在《秦腔》里,作家不再对夏天智所代表的民间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进行批判,反而对其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里的式微充满了浓郁的悲情和哀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秦腔》里,作家本人似乎更多的将同情和认同的目光投射到苦苦热爱秦腔的夏天智和依然坚持着80年代乃至更早时期的某种时代精神的老村主任夏天义身上。夏天智在夏氏家族乃至整个清风街的威严,与他所抱有的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小说中多次写到夏天义的儿媳妇与儿子之间发生纠纷与摩擦时,只要夏天智出现,他们马上从泼辣的吵骂中噤声,而悄悄地离去。清风街上哪一家兄弟分家也常常是请到夏天智,所起的作用比村干部的作用要更大,而小说中夏天义身上所代表的是80年代或者更早的一种时代精神。他的倔强和固执与他所坚守的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常常超越家族、家庭儿女私情的大公无私恰恰是清风街年轻一辈人身上所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欠缺才更显得弥足珍贵。尽管他早已从清风街领导干部的岗位上退下,却时刻关注着清风街的变化与发展。当清风街的稻田出现旱情而浇不上水时,又是他亲自出面带着君亭等人到水库软硬兼施的逼迫水库放水,从而缓解了田里的旱情。对于村子里许多人扔下田地,到城里打工致使许多庄稼地荒芜的情况,这位老人也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甚至还起草了关于农村土地情况的意见书向上级反映情况。清风街的支书君亭是他的亲侄子,可他并没有因为这份血缘上的亲情而放弃自己所坚守的立场和精神。当君亭等人想用村里的土地换取水库的鱼塘时,他则明确地表示反对。作为一个农民,他知道土地所代表的意义。在家人甚至村里人的不理解下,他依然身体力行地表达着对土地的那份无比的眷恋和热爱。于是,一个老人率领着一个“疯子”和一个哑巴在贫瘠的七里沟开始淤地。那是一个老愚公的形象,也是一个夸父的形象。直到小说的结尾,这个倔强的老人葬身在雨后山体滑坡的乱石之中。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挽歌。只是在小说当中,当夏氏家族的也是整个清风街的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先后辞世时,是不是也如同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秦腔的没落与衰颓,“我们的故乡”所代表的那种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也在席卷而来的城市化乃至全球化的大潮中正在一步步的消失?
从1998年的长篇小说《高老庄》开始,贾平凹在继续他的文学世界的乡村之旅时,不再将那个他想象的今日中国的“乡村”放大为一个大商州式的故乡,诸如80年代的长篇小说《浮躁》,而是直接将其微缩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与其说那是一个作家想象中的文学化的卑微而平凡的村庄,毋宁说那个小小的村落正是作家对自己生活了整整19年的故乡棣花街的凝重的回眸与深情的俯瞰。
从80年代在《商州》中对大故乡的山野风情与民风民俗的展示(《商州》《商州三录》),对浮躁的时代氛围下商州年轻的农民企图参与到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进程中的叙述(《浮躁》),到90年代后对以故乡棣花街为原型的高老庄、清风街如同浮世绘般的精雕细描,可以说在贾平凹的乡土创作中,对故乡的割舍不下的浓浓的牵挂,对乡村故土的父老生活的持续不断的深切关注,成为引发他绵绵不断的文学创作的“原初的激情”。
二、原乡人与返乡者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在贾平凹的乡土文学创作的背后是其对故乡的割舍不断的情感,而这份情意浓浓的乡情甚至是亲情成为其创作的“原初的激情”;那么,作家贾平凹似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之中的“原乡人”,犹如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小说《原乡人》中,那个在家国之间漂泊离散的男主人公——“原乡人”——正是作家钟理和自己一样。也如同钟理和先生的小说中所说的“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同样身为作家的贾平凹将自己对故乡的种种情感都给予在他的文学世界之中,寄予在他对故乡棣花街为原型的高老庄、清风街乃至是仙游川(《浮躁》)的叙述之中。
贾平凹多次谈到自己的故乡: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十九岁……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前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的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别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有意味的是,在上面这段长长的关于故乡的文字中,作家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并不仅仅是一往情深。其中既有对故乡悠久历史的自豪,对养育自己的那片故土的感恩与感激,还有因为它的贫瘠和蛮荒而产生的内心深处刻骨铭心的痛楚与酸涩。同时也包含了一个生长在乡村而后进城发展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的清晰而无奈的确认。“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于是,在贾平凹的意识中,当他选择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想象自己的故乡时,他是以一个身处在城里的农民的视角来观照故乡的山山水水。
贾平凹曾经一再宣称:“我是(个)农民。”也许正如赵园在谈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时所指出的,这种“地之子”般的自述,“是中国知识者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一种指认……更是他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一种回答。这回答绝无形而上意味,它毋宁说过于朴素、近于童稚,但包含其中的文化骄傲,是十足真诚的……(他们)由乡村中走出,在‘走出’之后并未割断了自体与(乡村)母体间的联系。”
实际上,对自我身份的明确指认,还隐含了知识者的一份深深的遗憾或者自卑。遗憾或者自卑的是当他们走进城市之后,依然发现自己骨子深处还保留着农民的根性。“我是农民”,一方面成为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已经进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并未完全转化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者的某种遗憾甚或是自卑。置身于都市之中,在那些本身就在都市里出生和成长的知识者面前,他们依然显得像个农民,尤其是他们处身在繁华而喧嚣的大都市,既充分地享受和领略了都市所蕴涵的五彩纷呈的现代文明之后,又同时敏锐地觉察到都市中丑陋的、阴暗的,乃至虚伪的“恶之花”。慢慢的,都市在他们的心中,不再是80年代那个充满了新鲜活力和充溢着憧憬和希望的“飞地”,却成为一个布满陷阱、缠绕着种种欲望、诱发着人性堕落的“废都”。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进城的故事或者经历,似乎成了一出童话,宛如那个英国的小姑娘追逐一只兔子,而跑进了一个无法分清真实与虚幻的“镜城”:镜中的一切如此的逼真却又如此的虚幻。即使那个镜中的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中的“自我”(英国数学家卡尔·刘易斯的童话《艾丽丝镜中奇遇记》)。在“废都”也是“镜城”之中,“乡土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和自我堕落成为不堪回首的梦魇。而当他们在“镜城”或“废都”里因为都市的“恶之花”而陷入人性抑或是人生的迷宫而无法自拔时,他们潜意识里与乡土的脐带却使他们重新找回了“灵魂和精神的坐标”,也是在充满“恶之花”的城市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他们突然发现在记忆中自己曾经生长的乡村故土显得如此的纯净和朴素,它是一座“静虚村”,恬淡而安逸。怀乡成为内心持续不断的一股股冲动。于是在90年代的《废都》里,当庄之蝶在西京逐渐迷失自我时,贾平凹却同时在小说中设置了一头来自终南山的牛。那头牛却显得异样的清醒。面对钢筋水泥的都市,它不断地怀念自己曾经生活的乡村,乡村的同伴。身处在一座不断“下陷”的城市里,它感到的是“孤独、寂寞和无可名状的浮躁”。与其说那是一头牛的喃喃自语,不如说那也是另一个清醒的庄之蝶的自我倾诉。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是与主人公有着相似经历的作家本人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流露。在小说的结尾,庄之蝶决定离开这座带给他无数梦魇的城市。从当初金狗拼命地往城里跑,到庄之蝶痛苦地离开城市,十年之间,贾平凹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充溢的是一个从底层成长起来的知识者的苦涩柔情。此时此刻,与乡村之间的并未割断的联系,也成为知识者或者作家本人超越自我乃至自我救赎的一根举轻若重的“稻草”。对罪恶的渊薮之地的城市的逃逸,使乡土或者故乡再次成为知识者梦想中温馨而温情的精神家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拥有的怀乡病的表征,在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怀乡——对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于乡村的情感回归。但是“知识分子以乡村为净土,以乡村为‘拯救’,却又集中表现着中国士大夫、知识者的弱者心态,他们的道德缺乏自信,他们精神的孱弱,心性的卑弱”。
但是另一方面,庄之蝶之类的知识者在城市里的困顿与迷茫、失落与失措,也同样与他们骨子里还保有的农民的根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在《废都》里,作者借庄之蝶的好朋友孟云房之口,一针见血地点出庄之蝶们的悲剧的根本之所在:“在这个城市几十年了,并没有现代城市思维,还是整个价的乡下人思维。”乡下人的思维成为庄之蝶迷失于西京的最主要的原因。当作家通过孟云房之口点出这一玄机时,那其中又掩藏了作家本人多少对自我身份确认的辛酸和苦涩。也许还夹杂着一份对自己还并未完全脱离农民的根性,蜕变为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哀伤和遗憾,甚或还有某种无法言明的自卑。在《浮躁》中那个已经进城成为记者的金狗在情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石华的眼中依然“还像一个农民”。就像一盆冷水一样,石华的话将那个充满了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从梦中浇醒。他被迫地承认:“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最无能的农民的儿子。”那既有刻骨铭心的伤痛,更有一份卑微的自我的体认。就如同在嘉年华上的盛装表演中,你身着王子的华贵的衣服,可别人却将那华美的衣服从你身上一层层的剥离,将你里面贴身的破衫褴褛一览无遗地展露在众人面前。有尴尬,更多的还有对某种宿命的无奈,甚至是深深的自卑。同时还会有某种“仇恨”。就如同我在上面引用的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里的那段文字中说的:“我恨故乡……”恨得要将自己身上那层故乡所赋予的“皮”剥掉!
于是在随后的《高老庄》中故事的一条线索是,大学教授高子路在父亲病逝三周年的祭日回到故乡祭父,但是回到故乡的高子路,却始终与故乡保持着某种疏离。毋宁说那也是小说背后的作家本人,对生养他的故乡棣花街所保持的不应有的疏离。而祭父事件与其说显示出身处在城中的知识者对自己血脉渊源的确认,毋宁说传达出的是知识者对自己精神谱系的无意识的追认,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怀乡。只是世纪末的故乡呈现出来的衰败早已打碎了怀乡情景中那个美好故乡的想象。故乡不再是一座“静虚村”而变得满地的荒凉与颓败。年老的在慢慢地衰老然后走向死亡,年轻力壮的男性大多离开故乡进城打工,有下煤窑的,有背金矿的,还有在省城拉煤、捡破烂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则有些神秘而暧昧地出去又回来,诸如苏红那样的变得花枝招展。基层政权的权力纠葛,家庭纠纷,宗族械斗,聚赌,偷情,借种,集体闹事……村办工厂并没有给村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却反而贪婪地消耗着农村本来就不多的资源。人性中的丑陋和猥琐在这“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身上展露无疑。当年血性的汉子雷大空转身成为带有江湖气的蔡老黑。乡村的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纽带似乎也变成了“利益”。在《秦腔》里这样的故事依然在上演。令人痛惜的是,高老庄的乡民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委顿与衰弱。连回到高老庄的大学教授高子路也逐渐恢复了高老庄人所特有的劣根性。从现实的层面而言,“……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有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从象征的层面上来说,返乡的知识者在对故乡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中,依然痛苦地发现了乡村所蕴涵的“文化传统”令其深恶痛绝的种种“弊害”。在《高老庄》的结尾,高子路在父亲的坟前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知识者的返乡之旅似乎成了充塞痛苦和酸楚的记忆。返乡的结果却成了一次与故乡的诀别!那背后掩藏的是知识者对乡村故土的深深失望。
无论是高老庄的高子路,还是清风街的夏风,甚或是高子路与夏风背后的作家贾平凹,他们内心深处积攒的“原乡人”的情怀却在逐渐的淡化。在父亲的三周年祭日之后,高子路似乎再也不想重回故乡,夏风在与妻子白雪离婚、父亲病逝之后又迅速地返回了省城;而对于作家本人而言,“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的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也许有一天,它对于“我将越来越陌生”,“但那都不再属于我”。于是书写故乡,与其说是为了一份责任和情感,为生养自己的故乡竖起一块碑,不如说成为一种忘却的回忆:在回忆中渐渐失去对故乡的记忆,抑或是在记忆的消磨中渐渐忘却故乡的风貌。
三、“不正常的人”的现代隐喻
在福柯的意义上,所谓的“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是由历史上三种人转变而来的:“畸形的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的儿童”。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所谓的“不正常的人”。比如《秦腔》中被人们称为“疯子”的“我”——张引生,《高老庄》中的“疯子”护林员迷糊叔,还有高子路和前妻菊娃的瘸腿儿子石头。但是贾平凹小说中出现的这类“不正常的人”并不完全等同于福柯意义上的“不正常的人”。因为“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不正常人中的)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做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畸形在法律之外,是法律所没有预见到的,因此这个自然的混乱引起了法律的混乱。”福柯关于“不正常人或者畸形人”的叙述实际上揭示的是法律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知识乃至权力对社会异己分子的“规训与惩戒”。
反观贾平凹小说中的那些“不正常的人”,诸如张引生,石头,迷糊叔,甚至是《废都》中那头像人一样会思考的牛,他们的不同于常人则显得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其中的部分人确实属于生理上或者是生物学乃至医学意义上的“畸形人”。比如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的石头,双腿无法像正常的同龄的孩子走路和奔跑。张引生挥刀自残生殖器,也成为一个生理上的“废人”,一个民间意义上的并不完整的男人。生理上的某种残疾确实使他们成为被科学或者社会所认可的“不正常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实际上有些近似于福柯所设定的“畸形人”。像张引生,生理上的残疾使他超越了“法律的极限”,“法律”无从评判他的真实身份的归属:男人抑或是女人?另一方面,诸如张引生和迷糊叔的被人称为“疯子”,使他们被大众所排斥为异己,视为是大众之外的异类,不是出于他们生理上的残缺,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某种常人或大众并不具有的超越庸常与现实的能力。具有特殊情况的是《废都》中的那头会思考的牛,宛如一个哲学家的它,在外在的形体上以“动物”的形式存在,却在精神、思想上以人的形式活着。与其说这是一头非正常的牛——动物,不如说那是一个以动物形式存在的不正常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头身处“废都”却思念故乡终南山、思想极为清醒的牛,正是另一个庄之蝶,或者是作家庄之蝶“内在精神的某一层面剥离其身体后的曲折变形的呈现”。宛如一出“变形记”一般,“会思考的牛和作家庄之蝶的关系再一次展示了喧闹中的精神分裂者的形象”。相对于那个困惑迷茫而逐渐迷失自我的庄之蝶,意识和思想极为清醒的牛显然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庄之蝶。
因此在此处,当我通过“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来分析贾平凹的小说时,并非完全将其等同于福柯意义上的“不正常的人”。但是,福柯关于“不正常的人”的知识考古学的分析与论述,所揭示的知识与权力在“不正常的人”的主体的构造中的运作关系却是我引以借鉴的。具体到贾平凹的小说中而言,我试图借助这样一个概念来考察,当作家以极为复杂的乡愁意识去书写他的故乡棣花街时,为什么会设置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非正常人的形象?他是怎样来叙述这些非正常人的故事的?这些故乡的非正常人与故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复杂的关联?而在这所有的背后我们能否窥探出,这样讲述故乡的方式又传达出作家贾平凹本人怎样的文学观点与人生态度,抑或是何种世界观?
无独有偶的是,在《废都》中也好,还是在《秦腔》和《高老庄》也好,那个不正常的人的出现总会跟知识者与故乡有关系。当牛对物欲横流的西京充满了失望之时,它却无比思念自己的故乡终南山,想念故乡的伙伴。而已经逐渐失去自我的大作家庄之蝶也在最后决定诀别西京而到远方去。远方成为彼岸,成为寻梦者要寻找的精神家园。那是精神或文化意义上的另一种乡愁。而石头和迷糊叔本身就生活在高老庄,但他们的出现实际上与高子路的返乡祭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当高子路返乡拜祭自己已经逝去的父亲时,他实际上又是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在儿子石头面前的。如果说就像上面我们一再分析的那样,回乡祭父实际上隐含了知识分子的某种乡愁,返乡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寻梦,那么,当知识者回到故乡,抑或是触碰到那个象征意义上的梦时,他却必须面对一个连他本人都界定为残疾的儿子。有研究者指出,在《秦腔》中,可能还掩藏着关涉到作家本人的不可觉察的隐私。那就是在自责中表达对前妻的追念和怀恋,表达一种懊悔和自责,以达到忏悔的作用。尽管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商榷,但是研究者对“自责和懊悔”的表达方式的敏锐地发现,却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关于张引生这个非正常人的问题。与其说作家要表达自责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无休无止的展示夏风对白雪的伤害,另一方面不厌其烦的用引生来表现对白雪的爱”,而“这两种看似悖谬的人物表现他(作家——笔者注)矛盾的心态”,毋宁说,在一定程度上,张引生和夏风是合二为一的一个人物。一个固守清风街的疯子张引生,一个进城成为作家的令清风街的人骄傲的夏风,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分裂体。
如果说,在隐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废都》中的牛和庄之蝶,《秦腔》中的张引生和夏风视作同一个个体的两个变形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变形记的设置中,牛和庄之蝶,张引生与夏风的合二为一与由一为二,实际上表征出的是一个精神分裂者的形象。那个被大众、社会认可为正常的人,规规矩矩地扮演着社会规范的角色,他更多的是主动的,或者是被迫的,甚至是随波逐流地认同着主流,认同着社会的变化,认同着大众的意见。当西京的三大名人纷纷俯身于金钱与两性时,另一位西京的大名人庄之蝶则也充满犹疑地步了他们的后尘。回到故乡的夏风似乎并未对故乡的人事纠纷发表什么看法,他更多的成为村人中的一员,而随波逐流。另一方面,那个所谓非正常人则成为一个僭越者,他超越大众的思想和意识,也僭越社会的种种规范。当西京的名人们迷失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时,牛却是清醒的。它不再认为城市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反而认为这座钢筋水泥铸成的城成为扼杀自己生命的无望之地。在清风街,张引生以疯子和不完整的男人的身份成为鹤立鸡群的一个异类。但是他却时常扮演着一个介入社会、勇于批判的角色。当村支书君亭决定用清风街七里沟的淤地换取水库的鱼塘时,他自己公开地贴了一张“大字报”,不仅仅对此表示反对,同时对当下的现实进行了某种微讽:“不要民主,只要权;为了将来成大款。不淤七里沟,吃瓦片,屙砖头,李鸿章是你祖;养鱼送领导,还想往上走;老百姓,皮包肉,生活够苦,麦糠里榨油……”甚至在结尾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以疯子的非理性实践的却是极为勇敢的理性之举。似乎疯子的身份极为巧妙地使他的“僭越”行为得到了大众甚至权力的原谅和赦免。用村支书君亭的话是:“他引生是疯子,疯子的话你能听得?”也是这样一个疯子,当众人都反对夏天义去七里沟淤地时,他却坚定地支持夏天义,而且还亲自跟着夏天义去淤地。
似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作家在故乡或者乡愁的故事中,设置这样的一种精神分裂者的形象时,他一方面借助那个非正常的人对社会现实表达出某种批判,另一方面却又以一个随波逐流者的形象传达出他对那种批判角色的质疑,即一个寻梦者也是知识者真的能够在对现实发言中实现自己的怀乡梦或改变现实吗?
贾平凹笔下的这些“不正常的人”断然不是鲁迅笔下不被庸众/被启蒙者所理解的孤独者/启蒙者,或者说他们本身就身处在大众之中,但是他们却具有某种大众并不具有的超现实的感觉力和想象力。双腿虽然不会走路,可小石头却经常用双手画出奇特的景象来。这个没有学过人体解剖的小男孩竟然画出了“一个人倒在地上,这人没皮没肉,全然是骨架”,而且“大小骨件没多一块,没少一块……也没有一块不是地方”,竟然跟人体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连高子路的城里妻子西夏也感到极为惊奇和困惑。更令西夏感到吃惊的是,有一天这个小男孩还无师自通地画出了一幅关于地狱的图画。而且经常还有一只大蝴蝶围绕在他的身边,似乎和这个小男孩有着常人难以觉察的沟通和交流。被高老庄的村民称为“疯子”的迷糊叔,则经常拉着悲凉的胡琴,哑着嗓子唱:黑山哟白云湫,/河水哟往西流,/人无三代的富哟,/清官的不到哟头。歌曲中充满了对人生的苍凉体悟,以及对现实的某种批判。还有歌曲中提到的白云湫,这个只有迷糊叔亲自到过的地方,在他的讲述中充满了神秘。那是一个高老庄之外的充满种种猜测和传闻的神秘莫测的世界。但同高老庄相比,那里却是一个更原生态化的大自然的王国。疯疯癫癫的迷糊叔也对这个原始的世界拥有着最鲜活的感官记忆。同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同类称为“疯子”的老人还是护林员,肩负着保护大自然的职责。正是这样一老一小——高老庄里的“非正常的人”,表现出与大自然的神秘的感应。难怪肖云儒在点评《高老庄》时,曾经多次说这老少两代人“都有和天地山林相应和的心力”,他们“从生民的两头接通喧腾巨变的现实和沉静恒定的天宇,天人感应着,也互证、对称着”。
张引生身上也同样具有这种清风街普通人所没有的感官反应。他常常和家里的老鼠、树上的鸟、飞着的蝴蝶说话,他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甚至他还能从动物身上看到他们是人的隐身。在七里沟和夏天义淤地时,从天上跌下来的那只大鸟,他竟然能够看出是自己的父亲的化身。在清风街的大众眼里,这当然属于疯人的胡言乱语。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同样表征出张引生与大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感应。
在贾平凹的笔下,这些故乡高老庄或者清风街的非正常人都表现出与大自然的亲密感。当他们被他们的同类所拒斥、漠视与嘲笑时,他们反而具有某种对大自然万物的亲近感,反而能够在自然万物中释放自己的心灵,获得应有的灵魂上的惬意。当故乡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关于利益的形形色色的纠纷时,那些被排斥的非正常的人却在人与自然的交流之中寻找到了另一种更和谐的人生形式。也许故乡这些“不正常的人”所践行的也正是心怀怀乡病的知识者心中理想的人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