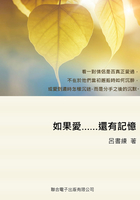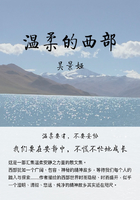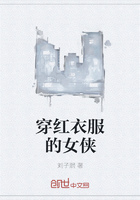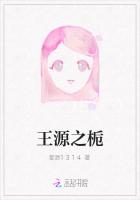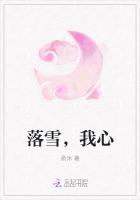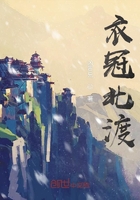一、创造“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本章以贾平凹的散文为对象,旨在探讨其社会生态主题的和谐构筑。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本身的关系。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盘旋上升、不断递进的过程。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人类认识相同步,从早期神话,到整个现实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现代性文学,都无不打上人类试图解释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关系问题的烙印。贾平凹是新********中较早触及生态审美问题的作家。在他皇皇数百万言的作品中,对“生态美”的呼唤和思考的作品比重很大。从70年代末期开始,贾平凹创作中就表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美思想,尤其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这种思想体现得较为明显。贾平凹以不同于他人的创作悟性,超常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思维品质,为读者描画出一幅幅富有情趣和诗意的生态画面。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使他成为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先锋派”散文家。他在散文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一种审美的生态思想。在微观上,他刻意描摹自然的原生态美,展示生态的生机与活力。贾平凹描摹自然生态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客体化(人的自然化),即将自己移入对象之中客观描写自然,展示对象的美,很少抒情;其二是客体主体化(自然的人化),即通过对客体结构形态的描摹抒发主体的诗思哲情。在宏观上,他努力创造“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表现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发展关系:生命和万物的同一是贾平凹“和谐”艺术世界的亮点。这种独特的和谐文化意识,主要源自作家人生过程中习惯的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生活的古朴淳厚的“商州”文化濡染,二是受中国人传统宇宙意识的制导。从现实超越性上,他批判“工业文明”的生态悖论,追寻人的生态本真:工业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丰美的物质享受,但无限膨胀的欲望又将人带入破坏和谐关系的悖论,使人陷入“自掘坟墓”的险境。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一贯追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文理想,是形成中国文人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贾平凹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在学习过程养成了良好的中国人文传统修养。这就促使他在创作中不断地、自觉地追寻和把握“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主张作家要重直觉感悟。而感应式思维促生的直觉体验使贾平凹的艺术世界表现出一种和谐。在这种“天人合一”审美观指导下,贾平凹笔下的人、事、景、物融通合构,无论是清茶、淡酒、明月、绿水,还是深山、老林、大漠、荒原,人、自然、社会达到了和谐交融、完美统一的艺术境界,表现出了作家独具一格的审美品质。
在《商州三录》里,作者给我们描画出的是一幅幅天人合一的人间美景,反映出其一贯的美学追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者笔下的商山人老实厚道,待人热诚。他们过着“洋芋糁子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包谷糊汤是命饭,搅团土豆离不开”。他们喝糊汤、吃柿子、喝烧酒,唱着“花鼓戏”,说着自编的“四溜话”。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安土重迁,“男耕女织”,自产自供,与世无争。“生存的需要,使他们结成血缘之网,生活之网。外地人不愿在此安家,他们却死也不肯离开这块热土。”(《莽岭一条沟》)人们并不苛求丰美的物质享受,更多看重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宜的这种关系。他们依山造屋,靠天吃饭,他们喜欢山、乐山、爱山,更注重与山的情缘。在贾平凹笔下,商州人都有着浓重的“山地情结”,或曰“黄土情结”。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贫而不困,怡然自乐。“一切都很安静”(《商州又录》之十一)。人、自然、社会和谐共处。人以地而生灵气,地因人而焕发生机。这是何等的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胜境呵!而且,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人身上,仍然不乏对生命的更新和进取精神。诸如,山里老婆子对自己孙子“越来越不像山里人了”的喟叹(《商州又录》之九);“黄家儿子”那超前的经商意识(《木碗世家》);还有商山人渴望挣脱人性枷锁,对真挚****的追寻(《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一对情人》)等,都已经说明,这是一方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热土,是作者永远的“人生根据地”、休养生息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虽然贫穷,但他们并不羡慕城市生活。他们能够在山里生存,依靠山,利用山,建设山。在这种源源不断的生机和希望的驱动下,整个商州不停地向前发展、进步,愈来愈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美态。
不仅写商州山地是如此,在写甘肃通渭人家时,作者同样抒发了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通渭地处西部缺水地区,水源不足使人畜备受煎熬,生态条件十分恶劣。但作者笔下的通渭,却是一个充满了乐观、和谐、向上生态精神的艺术世界。虽然作者也描写了通渭人吃水的困难:不能用净水洗衣,也不能擦澡,他们修水窖,靠“天”蓄水,洗过脸手的水,涮过锅洗过碗的水,过滤后再喂牲口和洗衣服。但在作者笔下,通渭人却善于利用水、节约水、再生水。不仅如此,缺水少彩的通渭人偏偏爱花惜木,追求和谐优美人生。缺水的通渭反倒成了战胜缺水生态的象征。通渭人缺水,但人们不缺道德,不缺精神追求。“正因为心里干净,通渭人处处表现出他们精神的高贵。”他们不仅重视教育,而且爱字成风。“日子再苦焦,墙上也要挂着字。”一般人家贴挂字是不讲究什么名家不名家的,但一定得要求写字人的德行和长相。崇尚耕读道德是通渭人本色。通渭人待人热诚、质朴,待客最豪华的仪式是杀鸡、烙油饼、熬地方茶。日子虽然清苦,但活得本真。知足常乐的通渭人不怨天尤人,他们靠天吃饭,偶然的“一场雨哗哗降临,村人也欢乐得如过年节”。在作者笔下,通渭人、通渭山水、通渭民风如诗似画,人、自然、社会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平衡、和谐。这“通渭”岂不活脱脱又是一个“新商州”!
生命和万物的同一是贾平凹“和谐”艺术世界的亮点。这种独特的和谐文化意识,不是谁赐予作家的,它主要源自作家人生过程中习染的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生活的古朴淳厚的“商州”文化濡染。贾平凹从睁眼看世界起,近20年都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商州”的山野乡村。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凝重,这里山水重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山民们保持着浓郁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然而正是这自然的山光水色和山民的单纯朴实,构成了一种和谐与淳朴的文化。贾平凹自己也说:“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我是比较注意的,它是构成我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文学,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曾经体味过陕北民歌与黄土高原的和谐统一,我曾经体味过陕南民歌与秦巴山峰的和谐统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可以说,商州和谐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从而奠定了其作品的基本色调。二是受中国人传统的宇宙意识制导。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人同构合一的观念。认为整个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富有生命的,都是气韵流荡、生机盎然的,物与人从根本上来讲,是相类相通的。“天人同构,天人一体,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人对于整个宇宙的总观点、总看法。中国人的这一宇宙意识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以潜移默化方式渗透流布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心理结构。”同为国人一员的贾平凹无法逃离这个“结”,他在文学创作的感应思维中形象地表现出亲和意识。
二、批判“工业文明”的生态悖论
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既提升了人们的生存质量,给人们带来丰美的物质享受,又在一定程度上异化、扭曲了人的本真个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生存悖论和爱欲失范情态。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人文生态以及艺术与审美生态屡被扼杀和破坏。人们不仅为了生存受着“基本压抑”,出卖劳力和自由,而且还为了某种理性算计领受着“额外压抑”,人为支付“文明”的重负的费用。这在城市人(市井阶层)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悖论现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工业文明背景下城市人的生存丑态。他是站在“农耕文明”立场上,对“现代文明”束缚下人们扭曲、变异、非本真的“生活相”进行挞伐的,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其精警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及其“生态美”思想。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在我国美学由“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以及由“内部研究转到外部研究”的美学转向的过程中,在后现代的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后现代”实质上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超越。这就意味着生态美理论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超越)。“这种价值立场和理论向度突出表现于生态美学是从一种新的存在观的高度,重新思考人与现实、人与自然、人与文化间的审美关系,是对美学现代性的深入思考和反省。”贾平凹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生态美”思想,创作出了《说房子》、《说女人》、《说美容》、《说打扮》、《说钱》、《说奉承》、《说孩子》等“说”类散文和《闲人》、《弈人》、《忙人》、《人病》、《看人》、《名人》等“人”类散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一反柔美幽远的美学风格,终止人与自然感应合一的思维方式,率诚地触剖分析了现代人生活中种种不堪重负的变异现象,更多地书写现代人生怪异荒诞的种种病态。
在作者眼中,这些“城市人”已经失去商山人与天地相合的自然本性,违背了自然规律,为“文明”所累,得了“现代病”。在他的笔下,城市被描写成充满怪异、荒诞、病态的世界。《笑口常开》典型地反映了城市病态的种种类型:人情薄,赠书即弃;难相爱,老来才有黄昏恋;居住挤,房事匆忙无欢乐;不坦诚,阿谀逢迎才为真。而且在这类文章写作中,充满着一种“黑色幽默”和冷色基调,作者正话反说,有时甚至不见“作者”,话语描述之中,却仍然充满“杀伤力”。在《弈人》中,作家对中国人在棋盘上厮杀、斗狠,互不相让,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的形象刻画,和希望变相统治别人、实现征服欲,或者表面痴迷于棋,实际上却以棋作为晋身之阶的心理分析可谓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本来就崇尚“本真”的作家认为,女人的化妆“违背了自然规律,轻贱了自己”。如同大自然一样,人体也有风水,随便去改造,就失去了和谐,也失去了特点和标志。(《说美容》)这和谐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标志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其中暗含着与山、石、月、花一样的“自然”美好的生活原型,一种与自然本性相合的人格境界——生命本真。
生物之间是一个链环关系,人也是这个生物链中的一员。一旦生物链受损、破坏,人作为生物亦将受害其中甚至不复存在。工业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丰美的物质享受,但无限膨胀的欲望又将人带入破坏和谐关系的悖论,使人陷入“自掘坟墓”的险境。这一点,不仅在“城市人”身上大量存在,“农村人”身上也有表现。贾平凹在描摹受现代商业文明潜浸而异化的农村生活时,也对扭曲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悖论”作了批判。狼是贾平凹笔下常见的意象,“人与狼”的关系是作者经常思考的问题。在狼(群)很多时,人与狼之间呈敌对关系。狼吃牲畜,人要宰杀狼,狼又在人的逼迫下,学会了生存能力,变得日益凶残。人和狼处在矛盾和斗争状态之中。作者以辛辣之笔写出了生态的悖论:一个孩子在狼群里能够生存,回到人间却得不到亲情,被抛弃乃至死去;(《金洞》)当狼生病时,它会找上门来求医。病好后还会衔来小孩的银项圈、铜宝锁报答治病之恩。(《莽岭一条沟》)在这里,狼身上浓郁的“人情味”已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残暴气。“狼”不再是一种代表“凶残”和“恶”的意象,它已经作为一种普通的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地共同生息于自然界中。人和狼互相依存,呈现平衡状态;而当狼群被打散、赶走、甚至狼被消灭之时,生物链条一个环节又被打断,生态平衡又被破坏,人们又一次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野羊野兔经常糟蹋庄稼,扰乱村人,还将淘金人的被褥干粮袋咬破”(《金洞》)。这里又有一个悖论出现:人夺了狼洞,断了狼的后路,狼却为人留下了巨大财富“黄金”。人靠狼而致富。人们又开始怀念狼、呼唤狼。“狼”可以说是作者反思现代文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形象。这里的“狼”不仅包含“狼”本身意象,还扩而大之衍演到狼以外其他生物。人宰杀狼其实就是砍砸自己的食物链。贾平凹通过反思狼的被宰杀和数量的减少,以及对人与狼关系悖论的描写,批判人的凶恶,抨击斩断人自身生存链条的愚钝现象,呼唤人和狼(自然、世界)的和谐生态。
在很多人眼中,贾平凹是一个“农乡土著”,他珍爱农业文明,贬抑城市生活,有着牢不可夺的“黄土情结”和“向农背城”情绪。艺术尺度在他笔下似乎是一种分裂状态。但我们从生态美的角度切入,发现贾平凹对“城市人”(工业文明)的嘲讽性描写,反映了他对人的生态本真的执著和追求。在他看来,农业文明离自然生态更近,人生存的相对自由、亲和、平衡发展,不失本真之美,而工业文明将人更拉入扭曲、变异的泥淖,远离本真之美。化装、面具、伪造,不仅在外观上让人与本真相暌离,更从本真上腐蚀人的灵魂,这种思想今天看来不无道理。
三、描摹“人化自然”的原生情态
与其他作家相比,贾平凹较早意识到自然生态的美。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自然生态平衡、发展的美态。在他的笔下,山、林、河、石等物象充满了生命的灵光,显示出与人相应的审美价值。他的创作,与近几年兴起的“生态美”的相关理论相吻合。美学家曾繁仁指出:“新兴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也坚持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乃至于山脉、大河、岩石等无生命的物体,统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自身的‘审美价值’。自然界本身也有美感。”贾平凹描摹自然生态的散文大多都抓住了审美对象的“内在价值”,从中抒写出自然界本身的美感。
自然生态美的特征是绿色,生态美的本质是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牛山之木尝美矣”,为什么孟子认为它美?它是因为牛山有茂密的森林和绿色植被,那一片浓浓的生机盎然的绿色给人们以赏心悦目之感。它蕴涵着生命,显示出勃勃生机,给人以希望和活力。自然中富含山、石、月、树等人文意象,作为人的个体生命的外延,它可以起到丰富生命、深刻识见的作用。而且,“山、川、日、月、鸟、兽、虫、鱼、林、泉、花、草都必须在其自身保持住自在生态时,才有可能灿然开放为美的存在。”就自然环境美来说,充足而又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丰富的绿色植物是生态美外在形象显示的三大要素。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存亡绝续的制导作用呢?可见,无论从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角度审视,自然的本原是美的。诚如李西建教授所说:“对生命存在的尊重和热爱,这既是生态学,也是生态美学最重要与最基本的精神。”那么,描摹这种美,传达这种美成为作家的主要责任。贾平凹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一再提倡,“散文本质是美文”,我们的散文作品必须能发现出这种美来(它包括自然美、人情美、对社会批判的美等)。贾平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描写了自然环境生态美,反映了自然环境生态美。他在《平凹携妇人游石林》中就认为石林是无法用文字写出的,“大美不能言”。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是酒,就表现它的醇香;是茶,就表现它的清淡;即便是水吧,也只能表现它的无色无味。”因此,他总是贴着事物的本来面目写。写月色中的皇甫峪的水,是“两山之间夹出的一条细水”;写深山里挑着担子的山民,是“光光的脊梁上滚着有油质的汗珠”。
从创作方法上,贾平凹描摹自然生态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客体化(人的自然化)。即将自己移入对象之中客观描写自然,展示对象的美,很少表情。像《文竹》、《含羞草》、《秦地游踪》(11篇)、《河西小品》(5篇)、南国笔记(5篇)等篇什即是如此。在作者笔下,商州山民的生活,是“火上的吊罐里,咕嘟嘟煮着熏肉,热灰里的洋芋也熟得冒起白气”;冬天的山是“清清奇奇的瘦”,雪中洼后的山是“浑圆圆”的白,作者竭力去掉人为痕迹,去描摹一种“无笔而妙趣天成”的画面。贾平凹的语言朴素清新,着力雕刻对象的个性特征,将事物的本来面目直截呈现在读者面前。正由于对自然的衷情,对人生的热爱和心中永葆的诗情,作者笔下的人和事才会充满风情,一派原始生态般的纯净:“走遍了十八县,一样的地形,一样的颜色……女人都白脸子,细腰身,穿窄窄的小袄,蓄长长的辫,多情多意,给你纯净的笑,男的却边塞将士一般的强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上的酒席,又有人醉倒方止。”(《黄土高原》)“男人都长得白白净净,武而不粗,文而不酸。女人皆有水色,要么雍容丰满,要么素净苗条,绝无粗短黑红和枯瘦干瘪之相。”(《商州初录·棣花》)读到这些文字,谁还能再去想穷山恶水,黄埃漫漫,那沟壑纵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大西北?之所以会有这种独特的审美感受,是因为作者始终以古朴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生态。而生态美很大程度上就美在生命的本真和发展上。正是在这种人的自然化的选择中,作者笔下的“戈壁大漠”有了价值,万物有了灵性,两性合构的世界也都滤化为和谐相宜的生存美景。
其二是客体主体化(自然的人化)。作者虽然赞美讴歌自然生态,但目的却是通过对客体结构形态的描摹抒发主体的诗思哲情。这集中体现在贾平凹逐年渐多地创作出来的大量的山水游记、生活感悟类散文中。这些散文寓意并不在山水形态和生活琐事,作者在细细叙写中蕴藉文中的是主客体感应交融的境界,主体专注于一境心灵静虚时的思想。如在《一棵小桃树》、《丑石》、《月迹》、《月鉴》、《静虚村记》、《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等七八十年代创作的散文篇目中,贾平凹作品的况味更多地体现在客体所具有的启唤主体感应的情感结构上,着力营造一种物我交融的意境。譬如,大戈壁本应是荒凉寂寞之所,但在作者眼中,它却是一块“难得糊涂的,大智若愚的地方”,因为它经历了洪荒,走入了单纯。广袤的大戈壁因此而成为一幅“现代艺术”的画,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变异,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生命中的灿烂。(《戈壁滩》)在作者的思想中,戈壁荒漠也是一种生物,一种生命不断更新发展的产物,正是这种有生有息、生生不息的生态平衡再生的宜人性,寄寓了主体的人生体验和历史价值观,才使作者眼中的戈壁滩成为审美抒写的对象,成为“现代艺术”的画。在贾平凹90年代的禅思美文中,人生体悟和学养的不断累积和提升,此时作者通过客体所抒写的已是寂静心境对自然的投射与倾泻。此时抒发的禅思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的禅宗自度顿悟的境界。《三目石》、《树佛》、《坐佛》等均有这个特点。面对顽石,人为何竟会“夜不成寐”,为何会出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看山不是山,又看水不是水,再看山还是山,再看水还是水”的情形?(《三目石》)当然是主体移情中玄想认知所致。以上两种对自然生态原生情态美的描摹,归总起来前者体现了贾平凹归复自然,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观,表现为人的自然化特征。后者则心境扩拓,容纳万物于心,表现了自然的人化状态。
在贾平凹的笔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并非二分对立,而是融通互汇,共生共荣,二者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环,没有绝对的主客体之分。贾平凹之所以能够在20多年的散文创作中不绝诗感才情,就在于他不断地借鉴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在不断积累学养锤炼人格净化心灵的同时,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寄情自然,顺应同化自然,从而才不断地创造人与自然恒新的关系和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