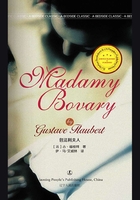我的牙比别人特殊,两个门牙之间多长了个小牙,小牙尖尖的,母亲叫它锥子牙。
这颗小牙跟了我好多年,它使我自卑,使我自惭形秽,使我在众人面前不敢开口大笑,偶尔忘情大笑,会立刻下意识地捂住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颗乳齿,是小时候乳牙没退净留下的,如果小时候家长留点心,在我退完乳牙后立即找牙医把它拔掉,就不会让它一直跟到我长大成人。
但在当年,在医学极不发达的偏僻乡间,这颗因父母疏忽而留下的小牙却成了我是全家灾星的依据,我家周围的邻居这样认为,我的母亲也这样认为。母亲说,自打她怀上我,家里就没得过好,灾难一冲跟着一冲。现在又多出这么个特殊的小牙,我不是主丧的扫帚星还能是什么?
母亲说他们第一次受到惊吓就在怀上我不久,那是1945年的4月,日本投降的前夕。一天晚上,衙门里的日本小官公藤带着巡捕下屯查夜,重点查一些他们认为头脑复杂的,对“大日本帝国”好像总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家,看这些人家是不是窝藏反满抗日分子。公藤带着巡捕查夜查到我们家时,差点把十六岁的大哥当成抗日分子带走。
父亲说时光还没有进入1945年,小日本就已经处处显露出败亡之气,供应紧张,兵员不足,士气低落……开始小日本还挺牛气,征兵不要近视眼,那些不愿意上前线打仗送死的日本青年就想方设法把眼睛弄近视,方法很简单,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拼命看书,一个礼拜下来,鼻梁上就挎上了近视眼镜。那时凡去有日本学生读书的学校看看,十多岁的日本男孩大都戴着近视眼镜,仿佛爱吃鱼的日本人在眼睛上反到先天不足,像传染瘟疫一样传染近视眼。而战争进行到1944年,日本国家已顾不上眼睛近视不近视了,把一些戴着眼镜的十三四岁的男学生都拉上了战场,作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越接近末日,日本在辽南地区的统治越疯狂。以往辽南地区各个划分片只有一个日本小官,这个小官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或镇长,掌管他管辖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大权,负责管理这个地区的治安和民事纠纷。战争进行到1945年,辽南地方也开始驻扎日本兵,也修开了准备打仗的战壕和工事,并三天两头地巡逻、查夜,骑着电驴子(摩托)的日本士兵在乡间的土路上突、突、突地横冲直撞,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乡里人就悄悄议论:小日本看样子蜡头不高了(辽南话日子不长了的意思)没看像条疯狗吗?踢腾不了几天了。
那天晚上,日本小官公藤和中国的巡捕耀武扬威地查到我们家时,我家养的小花狗可不买这个异国侵略者的账,对着公藤毫不客气地汪汪咬起来,一惯专横跋扈的的公藤遭到了狗的蔑视,立即起了火,拔出枪就朝狗打,一枪打断了小花狗的腿,小花狗拖着断腿惨叫着跑回屋里钻进锅洞,公藤还不解气,又追着朝锅洞里连打了几枪,直到小花狗咽气。
这条花狗还是大哥八岁那年从同学家抱回来的,养了这么些年,早已成为家中一员。狗的寿命一般也就是十多年,眼睁睁看着已经步入老年的花狗遭此恶运,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跟小花狗感情最深的大哥当时在旅顺师范读书,那天晚上恰好在家,见小花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下就哭了,小声嘟哝:跑人家地盘来横行霸道,真是欺人太甚!
大哥的嘟囔公藤没听见巡捕听见了,巡捕把大哥的话翻译给公藤,公藤的脸顿时气成了茄子色,大骂“八格牙鲁”并用枪指住了大哥,说大哥是“反满抗日分子”要把大哥抓起来送往北满当劳工。
旅大辽南地区自从四十年前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就把这里当成大和民族的一部分了,而大哥居然敢说这些法西斯分子是跑到别人的地盘横行霸道,无疑触犯了日本人的“天条”,在辽南地区说一不二的日本人当然要恼怒了。
日本人要把大哥带走,可把父母吓傻了,送往北满就等于去了人间地狱,凡送往那里的人可以说有去无回。父母苦苦央求日本人饶了大哥,说大哥年纪小不懂事,说大哥在旅顺师范(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哪里是什么反满抗日分子!
那一次,还亏得父亲是当地的小学校长,在地方有点名望,日本人才手下留情,放了大哥。公藤和巡捕耀武扬威地走后,父亲出了一头汗,母亲则瘫倒在地上……
在公元1904年之前,全国赫赫有名的沿海城市大连和旅顺,曾经是沙皇俄国的地盘,从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后,旅大地区又被日本列强占领,成为日本人的地盘,比“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全部沦陷还要早27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有一首,就是为旅顺大连沦为两个列强殖民地而写的: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地比拟?两个强邻将我们来回地蹴蹋,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当时的旅大地区人,确实像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国家不能给他们做主,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俄两家在自己的家门口发了疯地打,老老实实等待谁打赢了就做谁的奴隶。
现在的大连市,仍遗留着好多那一时期俄国和日本的建筑,时时向人们提醒着那一段民族耻辱史。
而日本人所占领的旅顺大连到皮口一带地区,被日本殖民者划为日本的关东州,称这一地区的人为“大日本的关东州顺民”,关东州地区改用日本的年号,关东州的孩子被施以奴化教育,一上学就得学习日本话,把日本话作为国语。
我出生时日本已经投降,异国占领者或死或逃,很快就从辽南地区销声匿迹,但日本话的影响却持续了好长时间。小时候,我和同龄孩子在街上拍球,拍那种用线缠成的球,一边拍,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要西麻米三便高,要几内,要西麻米三便高,要几内,上盖小……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殖民者留给辽南孩子的最后遗物了。
日本占领者除了让辽南地区的孩子都学日本话,还不准这一地区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让这一地区人管关内叫中国,要叫“支那”,管关内人叫“支那人”。他们在辽南这片肥美富饶的土地上每十里八村就修建一所富有异国风味的小衙门,里面住个日本小官和他的家眷,再配上一个中国巡捕和一两个打杂的差役。就那么几间房,一个日本官员,就构成日本奴役压迫当地中国人的最高首府。
我家附近就有这样一所小衙门,建在村外的高坡上,是几处日本式的大檐洋房,洋房四周是一尺多宽的围墙,因为偏坡式的地势加上地基垫高,围墙从外边看有十几米高,在院内,则不足一米。站在院内围墙边,有一种站在古代高高城墙上的感觉。
围墙外是一条简易公路,架一条通电话拉警笛的电线。围墙内还修了一座类似电影《地道战》中的那种炮楼,日本人不叫炮楼叫了望塔,了望塔上安了一个声音能传出几里远的大喇叭,终年飘着一面白底镶红的让中国人看着刺眼的膏药旗。
还在童年时期,我就知道了日本侵华史,知道了中国的八年抗战,那是因为我读了好多有关抗日战争的小书大书,像《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吕梁英雄传》、《苦菜花》等等,小学中学的语文和历史课本里也选择了好些有关抗日战争和抗日英雄的故事。
但书里所说的抗日故事和抗日英雄大都发生在山东华北山西一带,东北地区也有,像抗日联军、八女投江、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可这些故事没有一个发生在辽南,抗日英雄也没有一个是辽南人。我感到奇怪,就问父亲,说咱辽南地区也有日本人,怎么辽南地区就没有抗日英雄?父亲苦笑着说:怎么跟你说呢?咱这地方跟山东华北山西不一样,同是东北地区,跟东北其他地区也不一样,那些地区是日本用武力抢占的,咱这地方,是国家无能,不得不拱手送给日本的,就像亲爹亲娘没本事,只好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一样。孩子送给谁,就得听谁的话,老实巴交的辽南人可能都这样认为。再说,从1904年日本打败俄国占领辽南,在这块地盘上一统治就是40年,40年啊,再有锐气的老虎,长期被关在笼子里也打蔫了,更别说这些上不了天也入不了地的老实人了。
父亲还告诉我们:在日本人手下,日子是不好过的,中国人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都得听日本人的,日本人叫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父亲说我的哥哥们学习都好,可身为辽南人就别想上大学,只能上日本人办的师范学校。在日本人眼里,亡国奴是没有资格上大学的,亡国奴只能做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亡国奴的素质决不能超过他们的大和民族。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你不知道儿们如何地想念你!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这是《七子之歌·旅顺大连》中最后的几句,它们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殖民地人们的心情。“八·一五”日本投降,一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还没转过劲来,父亲已热泪滂沱,告诉哥哥们,咱们这下可有家有父母了,记住,咱们的父母是中国,咱们是中国人。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再也不当亡国奴,再也不会受日本人的歧视了。
父亲说,八月十五日那天上午,踞守在辽南一带的日本人还逼着当地的中国人为他们修工事,挖地道,做着长期坚守的准备。没过一会儿,衙门里的喇叭响了,播放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听了几句,那些刚刚还耀武扬威的日本兵顿时像被打断了脊梁骨一样,都耷拉了头,慢慢放下了枪,衙门里高高飘扬的膏药旗也降下来了,父亲说,在那一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真是又开心又激动,那种心情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那个晚上,我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感觉,但我想我的感觉决不会有父亲当年那么强烈,一是辽南距离香港太远,对遥远的香港没有太多的印象和感情,自身也没有体验过身为亡国奴的滋味;二是经受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我已不具有父亲当年的那股热情那股激情了,我觉得我及我的兄长们在多年的风风雨雨中都磨练得比当年的父亲要圆滑多了,都缺少了一点父亲一生中的那种认真、执著,也可以说是死心眼。
父亲说,日本一投降,衙门里最后一任小官公藤,立刻变成了一条丧家犬,在大街上跪着给中国人挨个磕头,求中国人饶他一命。父亲说,这个公藤平日傲慢得不可一世,常常嘲笑中国人命贱:吃饭猪的一样,干活牛的一样;嘲笑中国人不卫生:刷牙的不干,洗澡的不干,女人缠小脚的有……他偶尔去趟百姓家,得戴着口罩和白手套,就像中国人家里到处都是病菌,随时都会传染给他一样。当他做了丧家犬那几天,他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了,晚上也不知睡在哪个狗窝里,白天悄悄上这家讨口吃的,上那家要碗水喝,要到了吃的他就躲在哪个角落,也不管卫不卫生了,狼吞虎咽地几口就吃下去。乡里百姓还是厚道,没有置他于死地,去谁家要吃的也给他。那时谁要弄死他,比弄死一只猫狗还容易,但当地人都没有那样做,也不知当地人思想觉悟低,还是不愿意跟一条可怜的丧家犬计较,反正放过了这个霸道的异国占领者。这个公藤后来据说回了国。
母亲不像父亲,她目不识丁,虽然有当教员的丈夫不时地灌输一些文明字眼,讲一些家门之外的新鲜事情,但对什么是外国列强,什么是日俄战争等等仍然是稀里糊涂,她不想也不去过问中国的地盘为什么要日本人来当家,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受日本人的气,要日本人来管。如果说父亲当年当亡国奴当得清醒当得痛苦,那么母亲当亡国奴则当得糊涂当得心安。在土改之前,她的生活圈子只在自己的小家庭,在丈夫孩子身上。外边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不懂也不想去了解。她只凭个人的感觉去理解世上的是是非非。她说:日本人走了老毛子(1945年8月进军东北的苏联人)来了,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的老毛子比日本人还凶,到了辽南就抢东西,到我家后抢走了爷爷侍养的30多箱蜜蜂,足足装了一卡车,还抢走了为生我而准备的一葫芦兜鸡蛋。后来蜂子对他们没有用就又扔到路上不要了。
抢走蜂子抢走鸡蛋,这算是我带给家中的第二次惊吓,也算一次灾难吧。
我出生于1946年的一月,降生在数九寒冬的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应该说我的出生不占天时不占地利更不占人和。当时辽南地区的情况是日本人走了苏联红军来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的军队来了,国民党军队还没走共产党的部队也来了。以后是国共两党来来去去,双方形成拉锯战,枪声炮声成天响个不停。被日本人统治了四十年封锁了四十年的辽南百姓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共产党,也没接触过国民党,对国共两党的概念一无所知,所以觉悟就没有解放区根据地的人高,不像解放区根据地的人能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不像解放区人能自发做军鞋,抬担架,车轮滚滚去支援前方,辽南人还从没见过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他们是一听枪响都吓得躲在家里,担心不长眼睛的子弹会揭了自己的脑壳,担心被南来北往也不知是哪家的队伍抓兵或抓差送道。
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不要说生孩子,家里出现任何一点意外都是灾难,而我偏偏就选在这样一个不该出生的时候不识趣地降生了。
在我的上边,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哥哥,四个哥哥身后又是两个姐姐。虽然大姐生下后没活几天,但饱受儿女之累的母亲对养育孩子已从心里发憷,所以我还没出世就已遭到母亲的厌恶,何况我又生不逢时。
我出生时,母亲连接生婆都懒得找(也许想找也不方便),我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半夜子时瓜熟蒂落,我好像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一落地不像我的哥哥姐姐那样放声大哭,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存在,而是一声不吭像是死了。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看又是个丫头,就对父亲说:没气了,找个筐拐出去吧,等天亮再找人送到山外烧了。
那时,三岁以下的孩子死了没有埋的,都是用谷草裹巴裹巴然后夹到山外点把火烧了了事,烧过的死孩子就成了野狗的美味佳肴。烧死孩子时,往往点火的人还没走,周围已围满了等待美餐的野狗,那情景就像天葬场,野狗就像那些专门吃死人的秃鹫。人们说那时孩子生一千能死八百,这说法可能夸张了点,但孩子生得多死得也多的确是事实,山上几乎天天能看到烧死孩子的烟火,村里的狗儿们一看见哪个山上冒起烟火,就像古战场上的士兵看见烽火台上发出狼烟一样争先恐后往那儿跑,为争抢美味佳肴而相互火并……当时的农村,谁家死个孩子根本不当回事,所以母亲在处理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小生命时,就像处理一只死猫死狗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