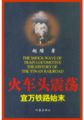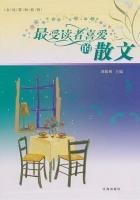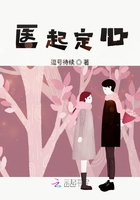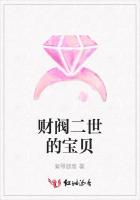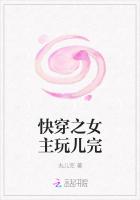迁徙,是生物为了适应自然而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早期人类为了种群的繁衍和生存需要,迫于自然或战争的原因进行过大规模的迁徙。许多古老的民族历史或英雄史诗中留存了大量的记录,并一再地咏叹古老民族长途跋涉的沧桑历史,如《荷马史诗》、《圣经》和《格萨尔》等经典中都记录了大量的民族群迁的苦难史。随着农耕生产方式的流行,人类获得土地后,群体迁徙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放弃。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体流浪成为特立独行的精神表达,成为脱离群体生活、背离规范的反抗姿态。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在规范和严整的社会秩序中经常被视为不安分的因素而备受贬损和打击,无法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同,但它往往成为思想先锋者的一种实践方式。在规范和僵化的社会机制中,流浪者成了社会变革的先驱分子。
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西方启蒙思潮的涌入带来文化的裂变,然而在现实中知识精英们所面对的仍是强大的一元化的精神文化图景,在承受禁锢和束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大量的、静态的生命形态因压抑、苦难而感觉迟钝甚至麻木,于是,流浪成为激活生命力、追寻理性精神、表现精神独立的人生选择。在新旧文化交替间,承担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在失落和再度追寻间徘徊、迷惘,变成流离失所和无所归依的精神浪子。现代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同于传统侠客、游僧和隐士之类的新型流浪者形象:郁达夫笔下的异国游子、田汉剧作中的浪子文人和鲁迅作品中的过客形象……他们那种痛苦又辛酸的流浪既是对旧有秩序的逃离和抗拒,也是对未来世界的追寻和探索。这些精神流浪者形象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流浪行为的产生大多源于精神的迷惘和灵魂的困惑,而不是生存的困窘(即使他们确实存在着生活困窘,也不会成为作者关注的中心)。流浪者的目的是在几乎僵死、凝固的社会中获得身心自由,获得独立意志,因此,现代文学中的“精神流浪者”并非充满诗意地漫游,而是体现为焦灼地追寻。在流浪中追寻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行为模式。
在经历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化转向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渐规范统一,流浪日渐固化,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使任何形式的精神和肉体的流浪的企图都受到严厉的排斥、限制和打击。即使在文本中嵌入一个具有流浪倾向的现象或人物,往往也是作为被否定或贬斥的对象而出现的,流浪者总是得到可悲可叹的下场。当时唱红大江南北的《流浪者》电影中的《拉兹之歌》也不是正面宣扬流浪,而是为阐释贫富不公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流浪作为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作为人性的一种表现形态,长期被抑制和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呆板僵硬的文化生活板块逐渐松动,同一、静止和均质的生活方式开始分化,人们感知世界、体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类潜在的流浪情结逐渐被唤起。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带来文化模式和思维特征的多样化。社会变革和文化交融也造成价值标准失范和社会心理失衡。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尚未确定,行为的茫然无措、心态的无所凭依,这一切都反映在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一方面人们在不断出现的各种风险面前,不再感到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在充满动感的社会新气象中,充满了变化的契机,诱发了人们探险的欲望。新时期文学中的流浪者和流浪现象逐渐呈现于文本,释放了被遮蔽的人性状态。作家开始关注流浪者怀着希望和惆怅的路上状态,追逐他们精神演变的踪迹,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生命形态。《人啊,人》中作为狂乱世界中少见的清醒者就是一个在“文革”中四处流浪、体验民生疾苦,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真理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对非理性世界进行了严肃的理性思索。《古船》中的叔叔是一个有过流浪经历并始终惦念和向往流浪的流浪者。作者肯定了他自由不羁的人生历程,最终还在大是大非面前给他安排了一个惨烈的勇者结局。
流浪一方面瓦解了旧有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自我确证的可能。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大多是“精神流浪”现象,这些知识流浪者充满了追寻的痛苦和焦灼。他们对原来的生活方式既拒斥又留恋,对新的价值观念既认同又怀疑。新时期文学中,敏感于时代变迁的知识者的流浪情结最为突出。《春之声》中的岳之峰乘闷罐子车的路途上感受到生命的新律动,《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在游历北方大河的过程中思考和探求古老民族的精神命脉。对于人类而言,现实是可靠和确定的,但现实也永远充满缺憾,尤其在价值理想需要重新确立的文化转型期。开始“解冻”的文化土壤产生了摆脱束缚的可能,打破禁锢的急切和无法安于现状的焦躁促成了人们内心的涌动。
一、群体迁移与城乡徘徊
知青是当代中国特定政策下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中抹不去的一道风景。虽然他们的群迁方式并非完全出于个体意愿,但他们却因不固定的方式理性而清醒地获得真知,成为新时期初一批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先锋者。知青的群体迁移经历和因此而产生的文化流浪心态则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题材。知青的流浪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体迁移活动,这段自愿或是不自愿的特殊生活经历,在他们这一代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知青有着明显的时段界限和身份标志,他们曾经有过相对独立的群聚世界,有着共同被放逐并不断寻找归属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城市的梭子式的固定的流浪路线,使他们的身份颇为尴尬,同时造成了他们灵魂的徘徊。
知青的成长环境在市镇,但步入成年人行列时,却需要到农村去追寻人生价值。起初他们以拯救者和拓荒者的人生定位介入农村生活,甚至满怀改造农村的青春激情,但农村社群不仅不认可他们的价值,甚至排斥和拒绝他们进入农村社会,因而,知青们深入农村环境后,明显地感到自我价值的失落。他们始终在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文化环境之间徘徊,成为“在路上”的一群人。“艰难的现实生活迫使插队知青形成一定的互助组织,并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价值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知青亚社会圈。在1970年前后,全国各地乡村出现了一些游离‘文革’社会的知青‘文化村落’。”
知青群体从怀着豪情壮志去追寻自我到被现实无情拒斥所造成人生错位,在精神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空缺和不安定感以及强烈的无家可归感。这些因素使他们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精神世界中都无法确证自己。叶辛的《蹉跎岁月》以山寨姑娘邵玉蓉的形象显示了知青对乡村的一种矛盾心理,她勇敢地接受了历尽生活沧桑和情感磨难的柯碧舟,以善良和纯真抚慰了柯的心灵创伤,但是她在柯的生命过程中仅仅是一个过客,她的死亡表明乡村的美好只能作为回忆存在于知青的记忆中。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知青的视角来审视马桥人。对马桥而言,知青以他者的身份来观察马桥,无法真正介入马桥的生活。他们处于“在”而不“属于”的尴尬状态。
知青的尴尬在于生活环境与其出身的脱节,市镇和农村的文化差异取消了知青精神世界的统一和完整。在知青眼中,农民的精神世界是愚昧的,却是完整和统一的,即使环境改变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精神特质。与之相较,知青的精神世界却是分裂的,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考察农村经验时,他们无法拆除自身与农村世界的隔膜。知青始终关注自身与农民的区分,显示自己的独立。在对农民进行文化现象的价值判断时,知青突显自身的是非观念和价值立场,农民则成为他们俯视的对象。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使他们的思想显得僵化,无法真正融入农村。特定的时代铸就了知青们特殊的生活境遇,造成了他们永远无法弥合的分裂身份。韩少功《暗示》中的不少篇章,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描摹了知青一代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无所适从和迷离徘徊的精神状态。
当知青们意识到,中国农村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时,就表达出别离乡村的渴望,但是,当永别乡村成为现实时,他们的内心却被一份魂牵梦萦的情感所缠绕。离开乡村后,有着知青生活经历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留恋乡村乡土,认同乡村价值观,并沾满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被称为知青文学。“乡村生活作为一种精神已存留于诗歌世界的深处。因此,到乡下去‘看看’,已必然地成为一种精神之旅,成为一种寻找灵魂停泊地的‘仪式’。”日后滤去了沉重时代的尘埃、苦难和怨恨沉淀下来后,被想象成澄净和透明的乡村世界成为他们反抗城市的精神参照系,“对乡村的神话想象更多的是出于已经再做‘城里人’的知青对自己进行重构的需要”。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表达了别离农村的返城知青的尴尬心态。曾经经历了10年沧桑的知青生活的陈信,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上海,在短暂的心理平衡之后,他发现记忆中的城市与眼前的现实完全不同,在熟悉的家园前他依然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中,知青“我”回城后,对纯净的清平湾和淳朴的农民不仅充满了感恩而且进行了诗性的述说。
对于知青而言,城市与农村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分,而且存在着价值观念的明显分野。虽然,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同现实农村的愚昧和落后,但与纷扰喧闹的都市相比较,农村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更能给他们疲惫的心灵带来抚慰,古典理想主义仍然是他们的精神依归。当知青把精神乌托邦定位在他们曾经力图挣脱的农村世界,注定了他们无法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到平衡的支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南方的岸》等作品一方面如实地记录了知青生活的艰苦,另一方面又用充满浪漫的笔调升华美化了这段艰难的生活经历,遮蔽了被放逐的辛酸和苦难,表现了被虚化的诗意和浪漫。这类作品大多存在着这样的述说:知青在农村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形成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而回归都市生活,物质上满足了,却无法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甚至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空洞。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把知青塑造成充满了浪漫情怀的献身者和筚路蓝缕无怨无悔的开创者。但这种人生定位伴随着一个被否定的时代价值,浪漫的色彩仅存在于文学的修饰和艺术的夸张中。
“文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传统家庭观念的松动,知青们以切身的体验强化了这种流浪的机制,从家庭成员的身份开始进入到集体户员的角色。知青点的集体户造成的感觉永远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存在的生活形态,在行为上他们从属于一定的组织形式,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悬挂在空中,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他们永远处在一个无法停下的恒动状态。“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呵,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纬度相遇”(舒婷《双桅船》)。对于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于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已经成熟的大人,知青们都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他们是被城市抛离的人群,而农村也视他们为他者。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中朴实的农民们对知青的评价是:“总听见垸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轻人带着学坏。”农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既没有抚慰知青们孤独的心灵,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委屈。文化上的鸿沟造成了沟通上的障碍,甚至还带来了彼此的冲突和伤害。
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荒原与人》以知青们在自然荒原上的情感失落为切入点,展开对人性的反思。主人公之一的马兆新曾在他灵魂和爱情的栖息地——落马湖经历过惨烈的世事;尔后他离开落马湖开始了15年的人生流浪,任何具体的空间概念都不能让他停下流浪的步伐。“15年来,我走遍了人间的草野、山川、大漠和湖泽……很多人问我,你在找什么?(一丝苦笑漾上嘴角)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找什么……”(《荒原与人·一》)落马湖是他曾经的灵魂寄居处,但它却无法成为他精神的安身地。徜徉在人生的荒原,强烈地追寻平衡的欲望和永恒的失落感构成了人性的张力,撕扯着人类的灵魂,已经开始的流浪成为一种精神体验,驻足在人们的心头。
知青作为一个群体,曾经普遍地有过流浪的生活经历。而迁徙式的流浪,早在人类与自然搏击和拥抱中就早已存在。在历史进程中,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获得了普遍而广泛的意义。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在他乡流浪时,总是把草原上的经历作为自己甜美的回忆,但是,当成人后的白音宝力格回到草原时,才发现他与草原有着深深的隔阂,他只得再一次踏上了旅途。对于流浪者而言,他的生命的动力在路上,他的魅力也在路上,他与现实世界的沟壑造成了他的忧伤和孤独,也形成了他永不停息的生命驱动力,一旦流浪者找到了精神家园,他的流浪就停止了。张承志从《北方的河》、《黑骏马》到《心灵史》一直执著地在流浪中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流浪中寻找个体、群体的灵魂归宿。这些作品以雄健的笔调,恢弘的叙事,塑造了许多永不停息的流浪者形象。
知青的流浪行为虽然是由历史和时代所造成的,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图式带来的文明冲突,使得他们能以次一级的社会群体对世界、对人性作别样的观照。当他们力图以自身的文化观念对所谓的愚昧和落后进行“启蒙”的时候,却发现落入了更大的尴尬,因为他们自身也只是没有恒定目标的流浪者。
二、青春流浪与都市表达
如果说知青的流浪意识是由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历史情境造就的,知青们出于外在体制的压力,在寻找自我、进行自我价值认证的时候还怀着英雄主义的集体情结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中大量的对个体流浪的描摹则更多地出于具有现代意识的个性驱动。它以别离社会的惯常生活方式呈现其生存状态。这种形式的流浪显示了一种独立不依的姿态,一种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反抗。从表现集体(知青)的流浪到描绘个体的流浪,流浪在新时期文学中从被动地承受演变为主动的选择。这种有意识的选择姿态表现出对主体精神的关注,显示了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因为个体在被社会抛弃的同时也存在减少被社会异化的可能,使其具有更多的人身独立的机会。
个体的青春流浪的出现与生活或体制的压力关系不大,多半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他们不是寻找出世的归隐之所,而是寻求能够适意心灵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旅途中排遣俗世的干扰,才能袒露自己的灵魂,获得心的沟通和需求。这样的流浪重视的不是目标和结果,而是体验和情绪。流浪者对流浪的迷恋是因为他们重视主观心境,希望透过主观心境来认知世界、感受世界。流浪者别离了家园,摒弃了体制和组织,也就意味着放弃固定的生活状态,放弃寄托他们的形影和躯体的尘世。他们喜欢让生命处于不停的游荡状态,喜欢过居无定所、游无定处的生活。他们这种自我放逐的行为,打破了固定的生活模式,挣脱了固有的社会束缚和限制,于长途跋涉中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乐趣和新奇,获得新的人生体验。
青春流浪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直接的关联。知青文学大多把流浪的精神寄托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他们的青春脉动和浪漫情怀融合在与大自然生息相关的农村生活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流浪现象则是应和了城市的特征。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变动的,而且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变动。城市是资本社会发展的产物,充盈的物质扩展了人的欲望,现代生活充满了躁动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充满了不安和动荡的感觉。这些在都市社会中漂泊的人脱离了固定的体制生活,在城市文化中寻找独特的表达自我和展现个性的方式。因此,流浪者不再行走在乡村田野间,而是在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中放浪形骸。这些不羁的行为直接表达了现代人的流浪心态。刘毅然笔下的摇滚青年和年轻的音乐迷恋者强烈地表达了青春冲动。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通过在不同城市间的流浪,探寻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心理,把生活空间看成是戏剧展现的可移动的舞台。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固定的文化模块逐渐松动,流浪的路线日渐丰富,流浪者不再只是通过路上的静观来认知宇宙和感受生命,还选择在变动中洞透人生价值。这些都市流浪者在流浪路上不再苦思冥想,不再在自然和历史的感悟中获得一种恒定的人文精神;他们的流浪源于生命的冲动,源于对现代理性和文明社会的投奔。
新时期文学中描述的青春流浪现象受到现代文明的滋养,并由此而表现出对僵化的文化模式的反抗姿态。中国这个后发展国家既寄托着要求尽快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的期待,又因为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文化环境,任何一种文化行为都受到不同立场(包括传统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批评,因此,青春流浪的先锋性和反抗性很容易销蚀。流浪以逃离各种环境的方式表达流浪者的特立独行,然而一旦落到都市这一世俗环境中,就被实用和功利的目的所消解,流浪原有的精神实质隐遁了,而作为一种时髦的形式在生活中延伸。市民文学的代表王朔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把流浪视为摆酷的一种手段。当流浪被作为把玩情调的方式时,流浪与社会之间的真正的不合时宜不存在了,流浪只剩下了形式的躯壳。《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的流浪汉的形象承袭了流浪者的玩世不恭,彻底放弃了对精神家园的追寻。80年代新兴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借助于都市中的流浪现象形成了对被传统社会、僵化体制剥夺和遏制的人性的强大反拨。这时的青春流浪文学射出一束耀眼的光芒。但是,当现代文明产生的青春流浪现象由边缘的抵抗姿态变成了从众和时髦后,其批判的锋芒不仅钝化了,而且最终消弭了。
刘毅然的《摇滚青年》、《流浪的爵士鼓》和《孤独的萨克斯》、《奔逃》等作品以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以青春激情进行反抗的叛逆青年形象。这些青年人不肯向世俗的生活和僵化的体制妥协,放荡不羁、愤世嫉俗和自由任性,流浪成为他们保持个性独立和灵魂尊严的最佳选择。在流浪中,这些充满动感的生命与天籁相应和,于艺术创作中展现他们的天赋,无拘无束地跟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摇滚青年》中的“我”追求的就是自由自在,就是生命自由发展的价值。这位“我”因为不能满足展现自我的欲望,放弃了艺术节表演上令人羡慕的独舞位置,毅然地递交了辞呈,过起脱离体制的流浪生活来。作品对“我”此时的心情,有如下一段描写:“我心里实在太兴奋,终于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了,虽然前面的路很凄迷,可我还是激动得发抖”(刘毅然《摇滚青年》)。人物的反抗是可喜的,作者的表述是漂亮的——“我从来不需要真实生活的依据,我只执著于精神家园和感情世界的流浪。”但其局限却是明显的。幻想的流浪文本中所演绎的现代的骑士传奇,其出路毕竟有限。作品中叛逆者的形象虽是现代的,却被古典的情怀所牵绊,因此,这类人物最终势必无法成就真正的现代人格。
青春流浪汉饱满的激情跌落后的痛苦和迷惘是因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反差。青春流浪汉在饱满激情的驱动下,开始放飞自己的理想,甚至幻想自己成为古典时代的勇敢骑士,演绎着骑士时代的浪漫传奇。但是,现实往往摧毁他们的理想,使青春流浪者承受迷惘和痛苦的煎熬。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主人公兴致勃勃地出远门,但最后获得的是什么?流浪意味着对一个栖息地的逃离,也意味着对下一个安身地的寻找。它是人类的一种抵抗姿态,同时也蕴藏着新的构建的期望。在日渐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流浪通过游离于规整体制外、碎片化的行为方式,拒绝体制和组织的“询唤”,实现对各种压抑和强制的抵抗。流浪同时也是以空间上的隔绝保持着边缘的位置,从而实现对“中心”的审视和反省。青春的狂野气息,青春的浪漫情怀,青春的无畏表达更显出青春流浪中袒露的人性和张扬的生命力。然而,激情毕竟难以持久,青春流浪满怀期望踏上流浪之途,但流浪的艰难和困顿消磨了流浪者的激情,追寻的焦灼代替了“出门”时的美好憧憬。《十八岁出门远行》、《野人》和《桑树坪纪事》中出现的观看者,都以游离的姿态、不羁的行为显示出与主流社会、规范体系的不合流、不妥协,铭刻着批判者和反抗者的印记,但他们却在茫然的寻找中煎熬,无法提供明确的目标和实践路线。
青春流浪充满了浪漫和激情,带着青春的果敢和坚决,义无反顾地背离家园和亲人,寻找新世界。青春流浪充满了新奇,也充满了盲动。当青春不再,当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牛奶与面包,而且还有苦涩与辛酸时,青春流浪便失去了轻灵,甚至被缚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时流浪的步伐也就停止了。
三、文化流浪与家园追寻
与传统文化形态相比较,现代文化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体独立意志和精神自由。现代社会中,个人对群体和他者的生存依赖减少了,但空间、时间、宗教、法律或各种潜在和显在的规则惯例设置了各种圈子,限定了个人的存在,而人只有突破各种限制,才能拒绝各种人身依附,不断地获得自由和自主。流浪作为固定生活状态和固定观念模式的反动,能在行动过程中打破禁锢,突破“只在此山中”的视域局限,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流浪,从中心游离,滑向边缘的时候,显示了流浪者独立的精神姿态。
“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层地反映了逐渐松动后的社会思潮中的文化心理需求。评论家李庆西在归纳“寻根文学”的缘起时总结了三点:“(一)新时期文学走向风格化之初,作家们首先获得了一种‘寻找’意识。寻找新的艺术形式,也寻找自我。(二)‘寻找’意识的产生,与通常所说的‘价值危机’有关,也与文坛的‘现实主义’的危机相联系。因而许多作家从艺术思维方法和感觉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三)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拓了艺术眼界,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也就是说,艺术思维的自由并不等于存在的意义。”
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变更使恒定的精神价值体系产生了松动,新时期文学以敏感而纤弱的神经触及了这种变化,开始了“出门”流浪。这些“文化流浪者”最初把目标设定在西方现代主义上,但西方现代主义尽管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了形式变更的契机,最终却未能达成灵魂解救的目标。“寻根文学”提供的精神参考体系是“新时期文学”流浪中的又一驿站。当然,“寻根文学”的鼓吹者们迫切希望文学能停下流浪的步伐,以便顺利地找到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家园,逃离和寻找构成的张力正是不断地流浪的内在驱动力。然而,流浪并非集体行为,流浪状态从来少有群体的呈现,更多的却是个体的呈现。对于流浪者来说,只有出发的原点是相同的,至于要去哪里、流浪的方式和路线从来都是无法统一和明确的。因此,流浪者明确地知道要拒绝什么,却始终无法确定得到什么,他们选择的流浪从来都是充满变动的无限的过程。韩少功提出“寻根文学”是“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的主张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奢求。这是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当代作家企图担当文化使命的一种心理折射。
流浪意味着逃离,首先就是逃离家园,同时也是对新的精神家园的追寻。流浪行为本身蕴含着对目标积极主动的追寻。传统社会以家族制度为中介调控个体存在方式和个体生存空间。离家出走的流浪者在路上对家园总是怀着一种试图逃离又难以割舍的矛盾心理,因为依靠血缘关系和感情纽带维系着的家庭,牵动着个体最为自然本能的脆弱又敏感的神经。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松懈了,家庭观念也逐渐泛化,出走和回家不再成为流浪者始终无法排遣的心结。更大的“家”的概念,如家族、国家替代家庭成为文化流浪的出发地。
对于再度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直线演进,也意味着与传统发生的冲突;同时当现代性面对着全球化的时代语境时,也意味着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话和碰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现实受到多方位的挤压,民族“根性”的失落导致了强烈的文化流浪感,“寻根文学”思潮的掀起代表了转型期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一种反向运动轨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流浪汉。许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描绘了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惶惑。张炜《古船》中古镇上传说中的古船,《九月寓言》中因工业化而不断需要迁移的小村,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中逐渐被抛弃的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韩少功《爸爸爸》中不断地受到生存威胁的古老的鸡头寨,贾平凹《废都》中失落社会文化价值中心的西京,这些古老文明的象征不断地被侵蚀、被湮没的现象提醒着人们恒常的文化板块正在松动,传统的价值信念正受到叩问,一种不定感和漂泊感正弥漫在都市的生活中。
古老民族的文化断裂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明的构造和阐释中,同时也体现在当下现实社会的文化信念中。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叔叔”的灵魂始终都处在漂泊和错位中,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找到精神归宿,不知哪里是他的精神家园。年轻时“叔叔”因为被错划为右派与社会疏离了,因此,他的婚姻和爱情一直处于游离状态,无论妻子、编辑部的大姐,还是打字员小米,都无法给他营造一种家的平静和宁谧。动荡的岁月里,叔叔被放逐了,平静的年头,叔叔再也无法安歇下流浪的步伐。叔叔的精神世界非常孤独,他分裂的人格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法整合,“他苦就苦在,他不能将这些对人说,即使是大姐,也不行。这不是他对大姐的理解有所怀疑,而是因为他不能让大姐和过去40年里的那个叔叔认识,他不能让任何人和那个叔叔认识,和那个叔叔认识的任何人他都要消灭,杀人灭口似的,连他自己也要消灭”。40岁前后的生活不仅仅是时间和社会的变动,而且在人性中也形成了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沟壑。这种由时代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文化裂痕使“叔叔”的心灵一直处在漂泊与流浪焦虑中。当代文学所表现的精神家园的失落,是有其现实价值和普遍意义的。
新时期文学中大量对僵化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质疑和反省,显示了被掩蔽了差异性的体制文化的逐渐松解,削弱了体制的权威性。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对人物的设置都用代号,不再标志为个性化或带有明显的褒贬意味的名字。个体的精神内核无法通过外在的姓名符号直接传达,角色倾向越来越明显,面具感越来越强。在数字化的年代,语言、身体都仅仅具有符号的意义,而不代表任何心灵的真实。刘醒龙的《秋风醉了》表现了对单调的体制生活的反讽,而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则表现了对农村模式的揶揄,塑造了体制中佝偻的形象和卑屈的人格。
延续着80年代初的现代性目标,许多作品把灵魂的探险经历设定在西方社会,因此出现了大量的留学生文学和海外游子文学,其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把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浪子形象放到西方社会中,让他们感受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思考自身的价值定位和人生取向,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女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曾在天涯》。这些作品共同体现了在西方社会中有着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的文化无根感。传统观念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而且延续了几千年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可谓根深蒂固。新的社会环境对于迈出国门的浪子们,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因此,他们自然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标准进行比照和衡量。离乡别井的现实生存环境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才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故而游子们在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上始终处于悬浮状态,深感自己精神价值的无所依托,他们在认知世界和为人处世时容易产生双重标准。在文化流浪者的内心深处,总是难以排遣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习惯于把异国的文化价值观念视为异质文化本能地予以排斥,因而事实上的文化精神家园的失落和情感上的不甘心失落带来了心灵的激烈冲突,构成了这些文化流浪人深刻的精神痛苦。
双重标准存在的取舍自然容易在两种价值观念的比照中互为对立,从而在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情感和理智上产生冲突。这使得那些离开家园的海外游子不管落脚在何处,都有一种流离失所的感觉。在生存现实面前,海外游子们最终不得不放弃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精神世界中的文化价值理念,按异国的价值观念来处世行事,来谋取生存的权利。就是说,在陌生而又缺乏安全感的现实世界中,他们面临着精神被强制改造的痛苦,这种生活境遇使他们倍感残酷和失落。
文化的断裂感产生的流浪隐含着对文化家园的追寻,这种追寻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而且存在于处在文明冲突中的人与自然之间。高行健的戏剧《野人》塑造的便是后一类流浪者形象。生态学家离开高楼林立的城市,来到被现代人视为边缘的原始森林,寻找人类和鸟类的生活家园,他内心的隐痛在大自然和淳朴的大山妹子的抚慰下得以缓解。但是,大山中的人和物虽然可以给予他暂时的安慰,却不能使他停下流浪的步伐,他在大山和城市中穿梭,他的灵魂也在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间挣扎,最后,他只得开始了新的寻找和流浪,在流浪中探询人类存在的意义。
寻求意义的流浪者在文明的冲突中永远无法安息自己躁动的灵魂,流浪主体内心深处遍布着矛盾和痛苦。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以象征和变形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在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传统文化间左右突围,却无所适从的文化流浪者形象。这种丧失精神家园的流浪者形象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概括,它昭示了知识分子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现实困境。流浪不只是一种形态,更是内化在心灵的精神气质。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精神传统上的无家可归感成了知识分子世界性的命运。”高行健、马建等作家的文学流浪话语最终在国门外获得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但却丢失了进入自己家门的钥匙。
文化的流浪感带来了精神的痛苦,换来了文学中个性和个体意识的逐渐形成。别离中心减轻了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降低了意识形态的正面冲击,确保了独立的姿态。人类早期的流浪是因为服膺于自然规律的要求和生存的规则,而文化上的寻找则是因感受到文化规律的失调的焦虑所致。流浪旅途中显现的自由的生命状态与启蒙者的精神诉求是一致的,虽然流浪不是生命的终极的理想状态,但它提供了新的参照体系。在流浪中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和叩问更能激发人类对精神价值的永恒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