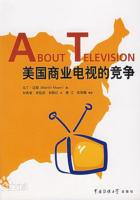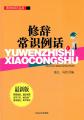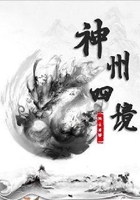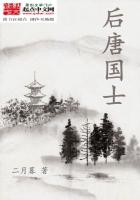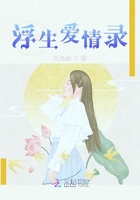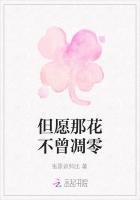名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学派。它讲求的是名实关系,所以也被称作形名学派。他们的论辩方式是以形名的方式,也就是循名责实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主要是政治主张。他们的论证过程和方式,创造性地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奠定了基础,所以有的学者在论述名学时,从哲学史的角度,进述名学的逻辑方法,或指出名学即逻辑学。虽然战国诸子均提出过正名问题,但有系统地提出名及论证方法的仍是名家的几位学者。名家在战国受到有些学者的赏识和批判,在秦亦不被重视,但是,他们的方法论却被应用着。秦始皇帝也在处处正名,即其例也。
(一)诸子论名
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孕育着新的王朝的诞生。新王朝是个什么王朝呢?诸子竞说,百花齐放,争鸣不休。在这样的形势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命题。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游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要正名,是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混乱和思想混乱,使“天下无道”变成天下有道。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要通过正名,建立天子的权威。同时,建立有序的政治权威和社会道德规范。他说:“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正名就是要拨乱反正,理顺这些关系,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正常轨道。这是孔子正名的理念。
荀子是主张“君子必辩”的。他接着孔子的正名命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正名》。这是在公孙龙、惠施以后,荀子为乱名而专门写的,也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混乱而写的。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将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为奇辞以敌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涌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说来说去,就是要说明为什么要正名。要让名与实归,名实相符。从政治上来说,还是要明明白白地分清贵贱,区别等级,避免名实交叉形成打不开的结,影响决策。对于一些辩者为了取得辩论的胜利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如庄子提出的“山与泽平”,宋子提出的“人之情欲寡也”,墨子提出的“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等命题,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于是,他开始更严厉地批判名家的一些学者了。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繷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他不仅批判了名家的惠施、邓析,同时也批判了儒家的孟子、子思以及墨翟、宋繸、慎到、田骈、陈仲等十二子。
墨子是实践家,他的论辩逻辑是抓住应用来说的。正如他说的“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所以,他认为:“今瞽曰,巨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能知黑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亦以其取也”。虽然如此,墨子主张,“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这便是墨子提出的三表法,用以衡量论辩的意义。他对三表法的解释是: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这就是说依据(本之)于历史的事实,观察(原察)实践的事实,应用(用之)于现实生活是否有利。对于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的贡献,胡适先生提出了演绎法、归纳法,而不同意章太炎提出的三段论,可见于其《先秦名学史》。
道家对名,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说虚无也不太准确。他还认为“有名”的,而且还是“万物之母”呢。但是,它是很玄妙的。有不可知论的意思,玄到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说的名,是不是名家所说的名的意思呢?我以为还是有名家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所提出名的意义才合适。那时许多人都提名的问题,作为一位思想家,对当时的热点问题,应该在他的思想言论上有所反映。“名可名,非常名”之类便是他的态度了。庄子对名辩的态度则更直截了当。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
他从齐物的观念出发,认为天下事物皆可齐一视之,不必分什么是非。他对待名家的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指非指的命题,以一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他并用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来说明要分是非,就像狙公一样愚蠢。看来是诡辩,实则是守其两端而摄其中。他将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而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以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等等。无贵贱,无美丑,无大小,无是非,无善恶,因为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们不必去计较这些,要物我两忘。看来无是非,其实也是对名的否定。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奈和回避。尹文子曰:“有势,使群下得为”。有权才有势,庄子不愿做官,自然无权,无权则无势,他也不想有势,于是,他的无奈和避世便是他自我保护的手段。
受到重用的法家,既有权,也有势,自然有一种进取之心,商君除了讲法、讲农战而外,对其他学派一概排斥,名家的学说自在排斥之列。韩非、李斯之徒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排斥异说是为了正君主的名分,同时,他们的论述也具有强烈的逻辑。
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诸子们无论谈名或不谈名,他们心中自有名在。他们的言谈和著述都在为名而说而著,他们的文字都有严密的逻辑在。
(二)周秦名家
战国时期以名家称的有惠施、邓析、公孙龙、尹文子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繺者为之,则苟钩繹析乱而已。
晋灼曰:繺,讦也。意思是攻讦。师古曰:繹,破也。他认为名家的缺点是如果用来互相攻讦,则具有破坏性,容易制造思想混乱。《志》中列出的名家有七家,三十六篇。这七家是:《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邓析》九篇。
邓析(?-前501年),郑国大夫。鲁昭六年(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鼎。这是中国最早的法律。邓析后来专门与子产作对,子产的法律中针对郑国人喜欢悬书(就是将自己的意见写在竹简上挂在街道中,就像大字报),专门写了禁止悬书的法令。邓析则将意见让人送去(就像送匿名信)。子产又立法禁止写这样的匿名信。邓析便将意见夹在物品中送去。他用法律中没有写明的方法来钻法律的空子。子产的法令无穷,他的应对方法也无穷。他还包打官司,并教人怎么反驳法律。他的价格是,大狱是一件衣服,小狱是一件襦繻(短衣裤)。于是跟邓析学的人不少。“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繼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列子·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杀之。”看起来,邓析是子产的一位政治对手。子产铸鼎,邓析则作《竹刑》。他的方法是钻子产的法律空子。他的辩论方式是“两可之说”。但是,子产并未杀邓析,是二十多年以后,即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子产死。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繽为政,第二年杀邓析。邓析死时应在五十岁以后,距子产死已二十年。邓析之所以能钻子产的法律空子,总是子产的法律条文太过疏阔,有可乘之机。以后《竹刑》为郑国所用,说明其较子产之法律文书要严密一些了。他教民争讼,也说明子产的条文保护贵族的倾向过重,民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替人有偿打官司,有点似今之律师。所以邓析的思想有他进步可取之处。
邓析的著作留下来的有《无原篇》和《转辞篇》。从现在的文辞看,似乎还是语录的集合。《无原篇》中认为: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陈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转辞篇》中云:
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安;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
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
从他的言论看,倾向于道家,主张无为安静。他认为,“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繿腕,手据鞭朴,而后为沾欤?”(《无厚篇》)。《转辞篇》中,杂入了老子、庄子一些言论,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何以知其然?为之斗斛而量之,为之权衡以平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仁义而穷之”。所以,“圣人以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故也。”他教人如何辩论,也就是“言之术”,又在文中谈法、谈兵。但总的趋向是道家,而表现出的是名辩家。从他的行事来看,他代表下层人民对抗子产之法,甚至充当了法律史上最早的律师,同时,他又是法家。
尹文子(公元前350-前285年),齐人,与宋繸、鼓蒙、田骈等为稷下学派,游学不仕。他的著作今存《尹文子》上下二卷,学者疑其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中云《尹文子》“其言出于黄老申韩之间。周氏《涉笔》,谓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盖得其真”。“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自老庄以下,各自为一家之言。读其文者,取其博辩闳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关于尹文的思想,《庄子·天下篇》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从这句来看,表现形式是墨家,而思想本质是道家。又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悖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举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繸、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纁合纃,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压?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纄(鄙)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这真是一种为众人而忘我的精神境界。这是他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禁攻寝兵,情欲寡浅,适可而止,宽人严己,奉献于人多而自己索取少。
在现行的他的著作中,先抄关于名的几点: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也者。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名不可不辩也。名称者,何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语曰:好牛。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纅言好,则复连于马矣。
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
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
可以看出,这里的名是名分,道便是各安名分。贫贱富贵美丑智愚各安其分,便是得道。所以,“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国乱的原因有三:“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以上见卷上)。名与法的关系是名为虚法为实,法以名而定。他还是讲法的。
在正名分的基础上,他分析了国之存亡的六征,有衰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有乱国。而乱政之本不是盗,不是奸,而是“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违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还是不守名分的事情。对正名分,文中举了两个例子。
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使,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殪。康衢长子,字僮曰善搏(依王启湘校改),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于是改之,宾客纅往。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之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文中用了三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名之重要。在佚文中又有狐假虎威的故事,录于《太平御览》。此故事亦见于《战国策·楚策》二。孰先孰后,已难考究了。自然,让人安于名分,仅是作者之理想,贫之求生存,是人生之欲,处理不好,名分也正不了,必然出现乱世。所以,作为人君,应该“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以上见卷下)。这些论点,同庄子所述的尹文的观点,还是可以接上轨的,并无太大差异。
惠施,曾作过梁惠王的相,其生卒年,依钱穆先生论,约生于周烈王时(公元前375-前369年),卒于魏襄王五年至九年(公元前318-前310年)。他也是名辩家。《庄子·天下篇》有他的一些材料。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太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为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惠施的命题是富有辩证的观点,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而辩者的某些命题,则陷入了诡辩的范畴。惠施以“善辩为名”,所以被归于名家之流。他的著作也散佚了。
公孙龙(公元前320-前250年),赵人,曾游于平原君门下。他的作品至唐时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六篇,与今本同。如果将名家认定是讲逻辑学的话,公孙龙可以被视为其代表。王启湘先生在《公孙龙子校铨叙》中说:“周秦人之以名学著者七人,今惟存邓析、尹文、公孙龙三家。而以为最卓绝。其名学要旨盖不出合同异四言之外。尝试论之,合同异者,名学所谓归纳也;离坚白者,名学所谓演绎也。”“演绎归纳为名学之方式,能立能破为名学之效果。以演绎归纳之方式,求能立能破之效果,而名家之能事毕矣。”这些集中地显示在《公孙龙子》书中。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白马论》
“白马非马”是他的一个命题。对于反诘者,他将白与马分为两个概念,讲白马有异于马的总称。然后,随着反诘者的问话,层层予以推理,仍然证明白马有异于马。符合于形式逻辑推理。
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坚白论》第五
他的概念是人眼看到的石和白,是两种;人手触石,知道石的坚,坚与石是两种概念,所以说是二不是三。然后又以问答的形式,进行逻辑推理。其他篇中亦与此同例。如《通变论》中:“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左。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右。”他认为,左右合为一位,不可合二以为右,也不可合二以为左,这便是二无一之道。他在证明他的命题中,运用了演绎、归纳等逻辑推理。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逻辑学。
他的逻辑推理是为他的名实观点服务的。他的名实观点便是名实与位的关系。他说: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这里说的名实位三者的关系是由物而实,由实而位,由位而名,名实相当才是正。因此,“出其所位”,便是“非位”。管的事超过了职权范围,便是越位,越位自然是“非位”了。他非常欣赏地说:“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一咏而三叹,显示出他对名实相当是甚为重视的。他在推论中展示的逻辑学思想是颇为睿智的,虽然他有时偷换命题,近似诡辩,也是一种智慧。
春秋以后,以下犯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呼唤着新的政治统治模式。政治上郡县制的脱生,经济上一度量的提出,体制上的君主专权,都是顺应当时的要求而出现的。孔子提出正名,正是为新制度进行酝酿理论的准备,名家的逻辑思维活动也正是对正名的回应。
(三)名学在秦
战国时期,各家争霸,政治家们在争取自己的政治主张能为国君们接受的情况下,也在研究如何在辩论技巧上能够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名实命题的提出是一个方面。循名责实则使逻辑学成了辩者要加以修习的问题。各家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主张更富逻辑性,强化话语的说服力。这便是名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秦王政时,《吕氏春秋》聚各家学说的精华,名学也在其中。《吕氏春秋》对名家的逻辑学作了整理和发展。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便对名家人物提出了批判。他首先提出“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文中首先将语言和思想统起来进行考虑,指出当时的说者言意相离的危害。文中举出的例子便是邓析。并说,邓析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标准,而可与不可日变,造成郑国大乱。后来杀了邓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从这里,作者提出了言、意的统一,言与心、行的统一。
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正,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于是,作者提出了审分与正名。
《审分览》中有: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壅也。
在《正名》中,作者明确提出: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在《审分览》中,作者不满于公孙龙,在《正名》中也不属意于尹文。作者并不反对辩。作者认为,“辩议不可不为。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即大义也——引者据高亨《诸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齐鲁1980版248页)”。但是辩论要有理,即辩必中理,“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议然后议”。“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这便是为说辩提出的原则,要中理,即充足理由。在推理中,作者提出了以类相别的推理方法。“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小方、大方是同一类,小马、大马都是马,可为一类。小智、大智则不是同一类了。他举了一个例: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可以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他指出这也不是一个类型(死和偏枯有质的不同)。他指出:“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原因就在于质的不同。死人和半身不遂便是质的变化了。物有多类,然而不然。如草有莘有纇,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也是质发生了变化。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中所讲的类,是以性质来区别它的质的规定性的。
名学到了秦始皇帝以后,则变异成为一种实用的代名词,既不需要正名,也不需要逻辑。它成了帝王意志,也成为群下欺上的工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全国一统。始皇帝也要正名,于是让群臣“议帝号”。这便是正名。王绾、冯韧、李斯为了正名,认为“泰皇最贵”,请为“泰皇”。秦王正认为还不够,“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这才算正名了。其他如:命曰制,令为诏,自称朕,群臣上书曰昧死,皇帝母曰太后,皇帝祖母曰皇太后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正名活动。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向大臣们述说六国君主的罪恶,也是一种正名活动。他东巡郡县,“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径”,“群臣颂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短”,“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当然更是正名之举。秦二世也东行巡游刻石,以正其名。以后更荒诞到赵高指鹿为马,二世死后为黔首之名葬于杜南宜春苑,子婴执政却是以秦王的名义来掌权的。正名之举,愈演愈荒唐,愈演愈不符合逻辑。正名耶,逻辑耶,到了此时,完全成了权势者手中的玩物,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以后,李斯在狱中,为了活命,第一次上书献“督责”之术,使二世“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能吏”。第二次上书居然违反逻辑地将自己为秦统一及立国后的七大功劳,列为七件大罪。所有这些,于正名,于逻辑,均不涉及,只能是名学的倒退,逻辑学的混乱。名学在秦王政的初期,以《吕氏春秋》而加以发展和完善,在秦始皇帝时期则成了御用的工具,到二世以后则是名学的混乱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