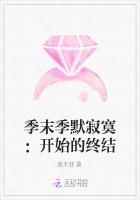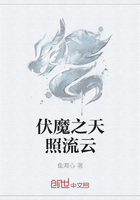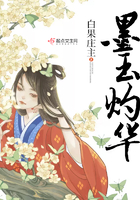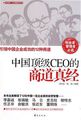攀登山峰:玛纳斯鲁Manaslu
攀登记录:2009年9月27日9:00(尼泊尔时间)登顶
突然飞来一只小鸟,停落在我身后的木梁上。我轻轻地起身,伸出手小心地把它捧到手掌心里,用手轻抚着它的羽毛。它快速转头看着我,眼里看不到一丝惊恐。这样靠心灵感应的神交让我舍不得放手。抚摸了它好一会儿,才打开手掌把它重新放回了天空。看着它从我的视线中越飞越远,我发了半天呆。人与小鸟能如此亲密相处,这是我从来无法想象的。我第一次感到,原来人与自然可以如此亲密和谐。查看原图。
为了保持攀登珠峰前的良好状态,2009年9月,我决定攀登海拔8156米的玛纳斯鲁。
在攀登玛纳斯鲁1个多月前,我随北京大学山鹰社一起前往青海攀登玉珠峰。北大山鹰社是国内最活跃的大学民间登山社团,在他们这群队员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青春激情、勇于攀登的精神。山鹰社成功攀登过很多雪山,特别是1998年登顶卓奥友,更是填补了国内大学登山组织攀登8000米级雪山的空白。但也因为缺乏足够的高海拔经验和对攀登8000米级雪山的综合判断能力,2008年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5名优秀学子因遭遇雪崩遇难。从他们对失败的诚恳总结和攀登经历上,能看到一群青年成熟和不服输的精神,但这些都付出了血的经验教训。
即便是6178米的玉珠峰,也一样不能轻视,2000年5月,玉珠峰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山难,两天内5位登山爱好者遇难。查看原图
这次山鹰社大队伍的攀登路线是北坡登顶再原路返回,王石、大刘和我3人却从南坡下山完成了一次玉珠峰由北到南的跨越。玉珠峰北坡的路线比较复杂,如果准备跨越一座山峰,需要具备更多的攀登经验和对上下不同的两条攀登路线的了解。当然,还需要具备很好的攀登技能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下山的路线是自己从未走过的,这更需要勇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崭新的体验。
在C1出发的那天早上,我们非常幸运地看到了百年不遇的日全食,我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也是我第一次担任“高山摄像”,记录了从C1到冲顶和跨越玉珠峰从南坡下撤的过程。从北向南的这次跨越,为我打下在今后登山中喜爱拍摄的基础。这也可以算是攀登玛纳斯鲁之前的一次为期一周的适应锻炼。
玛纳斯鲁是世界第八高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尼泊尔境内。自1956年5月9日日本登山队的两名队员和两名尼泊尔向导沿北坡首次登顶以来,截至2009年春季,登顶此山的只有435人次,另外有57人遇难。玛纳斯鲁成了继安纳普尔那、南迦帕巴特和K2之后,又一座登顶死亡率非常高的8000米级雪山。
近些年,随着攀登玛纳斯鲁的队伍的快速增加,路线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人登上了玛纳斯鲁。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做了短暂停留后,我们就准备向山里进发。我知道一进山就没有移动通讯信号了,赶紧给家人发出了几条短信,感觉有说不完的话要倾吐,但想表达的内容又不知所云。
发强回复信息安慰我说:“你量力而行,知难就退,平安最重要。”
我心里当然明白,安全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晚上收拾行李,突然在行李包里发现了离家时妈妈塞给我的一个苹果。它陪着我飞越高空、跨越国境,已经被各种装备挤压得伤痕累累。我拿出来抚摸着它,眼睛里不觉充满了泪水。
苹果——平安。分别时妈妈什么都没说,但是她的期待和祝福都藏在这个小小的苹果当中了。
我擦着眼泪,对自己说:“一定要活着回来。”
终于出发了。
2009年9月4日,我和王石、张梁、葛振芳等8名队员,随这次攀登的组织者杨春风,还有一位尼泊尔的登山负责人达瓦和他的夏尔巴们一起,先乘车到达一个叫阿如拉(音译)的小镇,然后从那里出发,再花大约一周的时间徒步到达大本营。
早上7点,所有人都挤到了一辆大巴车上,摇摇晃晃地向下一站出发了。汽车开了3个小时,尼泊尔的登山负责人达瓦就吩咐停车,招呼大家下车吃饭,他说再往前走找不到更好的饭店了。说是饭店,实际上就是一户极其简陋的农家,桌子摆在屋檐下,厨房是泥巴灶头,就在屋檐下的空地上。这是我第一次吃尼泊尔当地的手抓饭,几粒肉和少量咸菜,还有一些米饭。米粒没有黏性,像是陈旧的米,一颗一颗,粒粒分明。经过此前几个小时的颠簸,看到这样的饭,也没有几个人有胃口了。
查看原图吃过饭继续上路,后面的山路越来越窄,而且出现了很多大坑,大巴车根本无法行走了,我们所有人和行李被换到了一辆小卡车上。车颠簸得厉害,车身忽上忽下地摇晃,几乎把我们抛出了车外,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在后车厢里的队员葛振芳晕得厉害,中途吐得一塌糊涂。
下午5点,我们终于到达了阿如拉小镇。这一天里,除了上午那顿手抓饭,我们每个人只喝了一瓶水,再没有吃任何食物,所以晚饭虽然很简单,大家却吃得格外香。
第二天一早8点30分,大家整理好了行装准时出发,徒步进山。第一天徒步,大家都觉得很轻松,一边走一边拍村落景色。
沿途遇到的山民很淳朴,看着孩子们纯真好奇的眼神,更是倍感亲切。从孩子们的穿衣打扮能看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差。他们在破旧的房子前面玩耍,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看到我们来,离老远就会冲我们喊“Namaste!”尼泊尔语的意思是“你好!”个个都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很无邪的样子。我们给他们拍照,他们都特别配合,拍完后还迅速围上来,好奇地看相机里自己的照片是什么样子,没有一点点防备之心。大概是很早就接触国外登山者,孩子们大多都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这份亲切让人觉得情感的交流没有国界。查看原图
跟人的交流如此,跟自然界的交流更是如此。到了山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亲切。
第二天到达目的地之后,我正在路边歇息,突然飞来一只小鸟,停落在我身后的木梁上。我轻轻地起身,伸出手把它小心地捧到手掌心里,用手轻抚着它的羽毛。它快速转头看着我,眼里看不到一丝惊恐。这样靠心灵感应的神交让我舍不得放手。抚摸了它好一会儿,才打开手掌把它重新放回了天空。看着它从我的视线中越飞越远,我发了半天呆。人与小鸟能如此亲密相处,这是我从来无法想象的。我第一次感到,原来人与自然可以如此亲密和谐。
从阿如拉小镇开始,我们沿着峡谷往里走。刚开始徒步的前两天,峡谷里没有风,天气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头晕得厉害,感觉像中暑了,每天需要不停地喝水。随着海拔渐渐升高,虽然气温降低了,但因为连续几天徒步,人变得非常疲惫。更闹心的是,脚上打了两个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痛。脚腕也十分酸痛,我行进的速度因此慢了下来,还经常随地坐下来休息,因此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
不过途中发生的情况,让我又不敢随便在路边坐下歇息了。大概是出发后的第三天,中午在路边吃饭的时候,一个队友突然发现他的脚被什么咬了,鲜血直流,仔细一检查,发现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作Bada的东西,也就是旱蚂蟥。等到下午到达营地时,另外一个队员也发现脚被咬了,而且被咬了4处。随队厨师的胳膊也被咬了,衣服、袖子上留下了一片血迹。想到走着走着自己就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蚂蟥咬伤,真是让人抓狂。还有更让人抓狂的事,因为连续几天一直下雨,路面变得十分泥泞,到处都是稀烂恶臭的牛粪汤,一路走过来,都会踩上烂兮兮的牛粪,躲都没法躲。
越往高海拔走,气温越低,身上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要么是被雨水淋湿的,要么是被汗水浸湿的,所以停下来时,穿上厚厚的羽绒服都觉得凉凉的,感觉很不舒服。这段路上有很多碎石,上山的道路因为雨雾变得十分湿滑,不小心踩落一块石头,就听见一阵劈里啪啦的声响,那石头就一路迅速地滚落,跌入脚下水流汹涌的河谷。要是人失足落下,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计划从海拔2600米的地方赶到海拔3390米的Samagaon小镇,然后再往前一站走到海拔4600米的大本营。就在去往小镇的途中,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惊险的一幕:一名背夫不小心扭了脚,连人带行李转眼间坠落,幸亏他反应快,一把扯掉了行李,保住了自己,而行李急速滚下山崖,瞬间就被汹涌的河流冲走了,身边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丢掉行李的背夫一直自责、忐忑不安,始终不敢抬头看大家。达瓦解释说,这是无法控制的意外,像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情况下都是背夫和行李一同滚下崖去,被迅疾的河水卷走,行李与激流中的石头碰撞很快解体,而背夫却被撞击得面目全非,大多数情况下连尸首都无法找到。万幸的是,这次人没有掉进河谷中。
终于到了Samagaon小镇,我们住在一家木屋小店里,这家小店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来自国外的5名登山爱好者。小店里的茶厅很安静,坐在窗户下可以看到对面的雪山,大家都有些疲倦,各自饮着茶,看书或是静静地望着对面的雪山发呆。
一位国外的女队员推门走了进来,可能是门不太好关,她一直关不上。她猛地回身,重重的一脚把门踢上了,宁静中的巨大声响吓了大伙儿一跳。大家齐刷刷地都把目光投向了她,而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众目睽睽之中镇静地走到座位边坐下。
大家都笑了:“这个女人,太生猛了!”
队友里有人接着逗乐取笑我:“你登山久了,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吧?”
我安静地笑了笑,心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就不再是我了。
我可不喜欢把自己搞得像男人那么沧桑、威猛。即便是海拔很高的地方,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尽可能保证足够的清洁。进入大本营之前,我们在Samagaon休整了两天。随着海拔升高,这里的气温已经很低了,白天也很冷。我在厨房要了点热水,凑合着擦洗了一下,同时把衣服和头发也洗了。这儿洗衣服的水冻得手生疼。
8000米山峰也被登山者习惯称为“BigMountain”,在准备登顶之前,都会有一场煨桑仪式,以示对山的敬畏和感激——每个登山者都把自己心爱的冰镐、饰物等拿到祭祀台前,祈求能平安归来。这次的仪式,达瓦队长把尼泊尔国旗、中国国旗和队旗都挂了起来,我也拿出了探路者公司的旗子,把它铺在了台上。这面平日让我感觉十分亲切的旗子,如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神圣感,对我而言,也是力量的象征。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此时都有很多期待,但没有人愿意去多想那些让人忌讳的万一和不幸。可是,随队负责摄像的洪海,偏偏问了我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天下午,我们在大本营一边聊天一边做采访。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次登山,你想给家人说点什么?”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次呢?”
我笑着飞快地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很严肃地看着我,重复了这个问题:“如果这就是你最后一次登山,你不想给你的家人说点什么吗?”
我突然感觉,似乎整个山都没了呼吸。
……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此时,寂静雪山也一定听到了我落泪的声音。
我哭着告诉他:“如果我真的没了,这段视频你不许放给我的家人看……”
猛然间,撕心裂肺地想家……
在此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潜意识里一直都逃避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总是思前想后,那么我也就没有勇气攀登8000多米的雪山了。可是,登山所要直面的生死命题是无法回避的,只不过经由他人的提醒才愿意清醒地面对它。
一整天,我的心都泡在伤心中。
这天晚上,我半夜做梦,哭醒了,非常想家。
但当我们自己做了选择,还没有结果,往往很难说服自己选择回程的路。
这次攀登,我们的训练并不十分紧凑。大家在大本营休整时,王石说他在不远处看到了雪莲,我和张梁随他在营地不远的碎石山脊附近寻找。终于又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石缝中遇见了雪莲,这是我第二次神遇雪莲。它已经过了最早的花期,叶脉还在,花型完整,迎着风,轻轻地摇曳着,在蓝天下呈现出梦幻般的美,仿佛镶嵌在石头间一样。我看得发呆,捧着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王石在旁边笑我:“拍这么久,这花都被你拍‘糊’了。”
其实我自己清楚,我是被它顽强的生命力吸引了,所以才下意识地一直端着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展现它的魅力。这一朵雪莲,仿佛静静地在向我,也向所有为山而来的人提问:
你们究竟为什么登山?你们向山寻求的究竟是什么?
次日是从大本营到C1营地的第一次适应训练,早上7点多钟就出发了,一直走到下午1点多,大约用了6个小时。我们在C1营地停留了1个小时,然后开始下撤。下撤途中下起了雪,周围都是雾蒙蒙的。我想尽量多拍一些素材,所以上山和下山都在忙着拍摄,等回到营地才发现,胳膊累得都快抬不起来了。晚上躺在帐篷里,我还在纠结,下次训练要不要带相机和摄像机呢?
我该如何享受生命的历程,享受攀登带来的灵感与快乐?自己的提问,提醒我接下来的适应性训练,需要更加平和。在攀登的时候,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一边走一边享受拍照的乐趣。我甚至忽略了队长的提醒,他说,在高海拔地区的行进过程中,携带任何与登山无关的器材都会影响到行走的节奏,同时体能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不能带摄像机进行拍摄。查看原图。
但那有什么呢?我悄悄地想,现在是适应性训练,又不是最后的登顶,即使走到最后,体能消耗很大,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不仅背上了自己的厚羽绒服,还背上了大相机、路餐、开水等许多随身必用品。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好极了。
登顶的时间安排定了下来。队伍计划在9月22日开始正式向C1营地进发,一路经过C2和C3营地,在9月25日那天,开始从C3冲顶。
接下来还有两天的休整,这天早饭后,队长达瓦考虑到整个攀登队的安全,开始根据队员的体能适应情况分配协作,每名队员配一名夏尔巴,分配原则是体能弱、经验少的队员分配体能强、经验丰富的协作。综合所有因素之后,我被排在了倒数第三位,我的协作达瓦丹增是名能力比较强的登山协作,他曾经3次登顶珠峰,还登顶过一次玛纳斯鲁。
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一样静了下来,以此减缓内心的激动。这天下午,洪海叫上了我,一起去拍摄新西兰登山家罗塞尔组织的在营地捡垃圾的活动。
罗塞尔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和登山活动指挥者,也是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他本人不仅组织,也亲自参与捡拾垃圾和垃圾分类。他安排把垃圾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可以回收、及时就地处理的,还有一类是需要背下山处理的。
他还会与大家分享高山攀登经验,罗塞尔在大本营会时刻关注着卫星气象。这天晚上,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最新的天气情况:9月25日那天顶峰会有每小时25公里的风速,到9月26日,风速会减弱,根据气象资料,在这个周期里,27日是天气最好的一天,从28日起,天气将开始变坏。所以罗塞尔决定,把原计划登顶的时间推迟两天。9月26日,我们开始从C2向C3营地攀登。
到达7300米C3营地之前不吸氧,对于每个队员都是很大的考验。这次我决定只带一台小照相机,把很沉的5DmarkⅡ(俗称“无敌兔”)留在了C2营地。我的目标是,保持最好的状态攀登到C3营地。所以从C2向C3进发的时候,我没有背任何多余的东西,洪海托付的摄像机也交给了夏尔巴达瓦丹增,可是我依然感觉行走艰难。
一开始,我走在队伍的前面,走到一半路程就感觉缺氧得厉害,攀登的路线也越来越陡,越来越困难。现在的海拔超过了7000米,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了。我一直没有穿连体羽绒服,后来感觉太冷,不加衣服可能再也硬抗不下去了,我决定把连体羽绒服穿上。抬头一看,前面还有很长的攀登路线,而且都很陡峭,初步判断了一下,攀上去至少需要2小时,而且再往上的路线是什么情况,我也一无所知。考虑了一下,我决定在这一个陡峭的结点处停下来,把衣服穿上。达瓦丹增看我在如此陡峭的地方停了下来,很不理解地看着我。很快,他明白了我需要穿上连体羽绒服的意图。他担心我在换衣服时发生滑坠,就站到我的侧下方,一边帮我忙活,一边担心我的举动不安全,有些不理解地摇着头嘟囔着。
我自己也十分小心,因为在这里穿连体羽绒服真的是太危险了——要先把安全带、冰爪脱下来,才能把连体羽绒服穿上。我穿着一双大雪靴,要在不脱鞋的情况下把连体羽绒服的裤脚套进去,需要一只脚着地,难度非常大,如果脱掉雪靴再穿,难度会更大,攀登过8000米级山峰的登山者都清楚,平日在高海拔帐篷里穿雪靴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在这样陡峭的雪崖上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个技术活,缺氧和寒冷已经让我痛苦不堪。我先费力地把脚下的雪踩出一个可以站稳的坑——要知道,在海拔7000米陡峭的冰崖上做这件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然后一点一点地把腿往连体羽绒服里伸,折腾了很久总算套了进去。穿好了连体羽绒服,还要继续把冰爪和安全带重新固定上,这样才能接着攀登。不过让我后怕的是,因为穿连体羽绒服时必须解开所有的安全保护,如果在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滑坠,在这么陡峭而高的雪壁上滑坠下去,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出发的时候,没有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个失误,但决定在这里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明智的,否则,我将很难坚持攀登到7300米的C3营地,如果当天到达不了C3营地,结果必然是我没有机会和队伍一起登顶。查看原图
到达C3营地之前,有一面非常陡峭的大雪坡,这是我感觉攀登最艰难的一段,有好几次我都落在了后面,达瓦丹增在后面示意我,超过一个攀登速度一直非常慢的外国女队员,走到她的前面。我试着超过她,但是不久又落在了她的后面,我努力地跟在她后面,到最后落得越来越远,我谁也跟不上了。这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牙坚持着,走一步,停一步,向C3迈进。我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的队员。
快到C3营地的路上,我看见一位裸露在雪面上的登山者,他仰面朝天与冰雪交融,永远地躺在了冰雪之中。这是我第一次在山上亲眼目睹遇难者,当时自己竟然没有太多的恐惧感,也没有太多的其他反应,难道是自己麻木了?
永远留在冰雪中的登山者,本身已是值得敬畏的雪山的一部分,作为攀登者能留在这儿,也许他的人生不会有过多的遗憾。后来我得知,这位登山者是日本人,3年前在这里遇难,根据遗体所在的位置和他的姿态,我猜测这位登山者很可能是疲劳过度或是突发高山病无法继续下撤而遇难。
到了营地之后,自己撑不住了,头晕头痛得厉害,身体剧烈地发抖。我第一时间爬进帐篷钻进睡袋,捂了很久,还是觉得冷得难受。C3营地的海拔高度已经是7300多米,我想可能是严重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夏尔巴拿来了氧气瓶,我戴上了氧气面罩,大约又过了1个多小时,感觉终于缓过劲来了,可是胃口依然不好,吃不下任何东西。达瓦丹增帮我做了一碗热汤,我勉强喝了下去,喝完汤,我躺下,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就这样一直躺到凌晨两点。
按预计的时间,队伍准备冲顶了。
9月27日接近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在达瓦的引领下出发了。周围黑漆漆的,头灯照射的范围只能看见脚下的队友踩过的雪坑。大家都静悄悄的,很小心地跟着每一个脚印走。达瓦走在最前面,感觉他每一步都非常谨慎,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周围的情况,跟另一个夏尔巴一起确定顶峰的方向是否正确,然后再带着大家继续前行。
天渐渐亮了,天气很好,没有一点儿风。我感觉此时状态特别好,我向夏尔巴要过来摄像机,准备拍摄。为了拍摄到整个队伍的攀登状态,拍摄过程中需要多次超越队伍,有时也需要站在队伍的旁边,这必定会耗费更多的体能,也加大了攀登风险。拍摄过程中王石两次朝我摇手,示意不要再拍,我想他一定担心我的安全。不过,登顶的过程好长一段路都是大缓坡,相对不是太难。
9月27日上午9点,队伍中所有人陆续成功登顶。在登顶后的下撤过程中,当再次回望顶峰的路时,我看见最后收队下撤的杨春风面向山顶,双膝跪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急忙拿出摄像机,迫不及待地想记录下这个场面,他很快站立起来了,我却只拍摄到了一个尾巴。杨春风在中国登山界算是“元老”级人物了,圈内人几乎都知道他,但他也受到过很多质疑。如果以一位组织者的身份看,他在队伍管理方面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这一次他乐于助人和平和的攀登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选队友,我一定会选他这样的攀登者。
登顶后我们安全下撤回到大本营后,乘坐直升机回到加德满都。
进山时,我们徒步了一周;从山里出来,只用了45分钟。
3天前,我们还在海拔8000多米没有人烟空气稀薄的冰天雪地;3天后,我们已回到了海拔1000多米的喧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