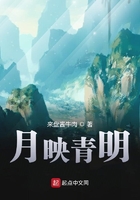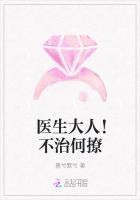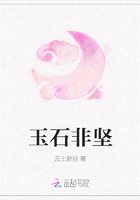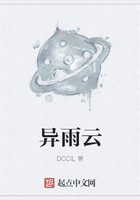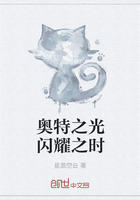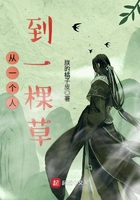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14年,在掠夺东北丰富的工矿农牧业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同时,也在东北进行了若干建设,其中尤以采矿、钢铁、电力、机械等重工业和铁路、公路交通设施为中心。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产业,而且是日本军国主义剥削压榨中国人民所得,日本投降后理应归中国接收。1944年筹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曾为此提出:“鉴于中日战争时间之长久及日本对华经济破坏之深刻,日本当按其实际支付能力,对我支付相当数量之赔偿,以抵补中国战时之一般损失。除金钱支付外,可以实物支付。”[1]
1945年2月,美国与英国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首脑会议上对苏联作出让步,同意苏联在战后东北据有相当的特权,从而使中国在对战后东北问题的处理上自始即处于不利地位。在随后进行的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2]。但据参与谈判的蒋经国告张嘉璈,在谈判中斯大林表示,“特种公司产业应归苏有,‘满洲国’者则苏不染指,即此一谈,此后遂搁置,未加注意”。张嘉璈认为,苏方“今则公然认为战利品。只当大任者不能细心密虑,今铸此大错,可为痛心”[3]。由于中方对一些具体问题未及深思熟虑,如何谓斯大林所称之“特种公司”等等,在中苏条约和有关文件中均未加以明确的界定,从而为未来东北的经济接收留下了变数,也为苏联留下了可乘之机。
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飞抵长春后,在10月17日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称这些产业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马氏说法表明苏方“意欲藉战利品为名,攫取东北工业,继承日本在满洲经济所占有之特殊势力”,并为全面介入东北经济预留伏笔。[4]张嘉璈马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如照马氏说法,东北大多数产业有日本投资,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他向蒋介石建议,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东北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苏联若提出战费问题,则只能由中国政府付给,不宜合办工矿事业。[5]张嘉璈此时不仅主张将东北日伪产业收归国有,而且反对苏联以经济合作为借口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但是当时国民党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虽“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但似乎尚未将此事置于决策的中心位置。[6]苏联则企图以既成事实压中方让步,也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此事最初并未成为中苏双方东北接收交涉的重点。
然而,中苏双方不谈东北经济产业的情况并未能持续多久。在苏联方面,其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事实上也这样做了)[7],二是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或所谓经济权益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东北事务,以确保其在远东地区的国家利益。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根据,国际法对战利品的解释并不支持苏联的说法[8],而苏联也曾同意战争赔偿问题应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再者,中国和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既为同盟国领土上的产业,即便是敌方产业,也不应视为“战利品”;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但苏联自恃强权,在基本运走了有价值的动产并拆卸了能拆的不动产之后,顺势提出其他不能拆卸的不动产问题,企图获得更多更大的权益。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对苏联的强横做法很是不满,不愿涉及所谓“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导致了国民党态度的变化,尤其是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经过在接收过程中与苏方的交涉,认识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而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将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恶感和戒心,不利于国民党接收东北并确立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因此他转而主张就东北经济问题与苏联谈判,并在可能情况下满足苏联的要求,以此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中苏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有关东北经济问题的交涉。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进行了“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的首次接触。斯氏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9]。还在此次商谈之前,10月24日,斯氏已直接要求前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前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将其所属产业移交苏联。在苏军压力下,“满业”和“满电”于当月底与苏方达成移交协议,而中方对此事的全过程毫不知情。11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对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阅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作者注)所左右。”张氏不明底里,“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直到13日,他得到苏方与“满业”和“满电”签署的文件,方才“得其端倪”,“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业,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10]。
就在苏联预谋以经济合作而控制东北经济的同时,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变化。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登陆,并对国民党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然而客观现实却是,军队登陆受阻,接收缺乏强力支撑,熊式辉等在与苏方交涉中屡屡受挫,一筹莫展。与此同时,中共军队迅速进入东北并扩大势力范围,已经构成对国民党恢复东北统治的严重威胁;美国为国民党运兵到东北的举动引起苏联的强烈怀疑,使其对国民党接收东北设置更多的障碍。东北接收本为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问题,但自国民党接收东北之始,除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之外,中共进军东北和美国欲在东北插足这两个因素即如影随形,交织于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全过程之中,并通过与苏联和国民党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成败,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
面对东北接收的不利局面,11月上中旬,蒋介石连续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讨论东北局势,提出撤退东北行营,暂时“搁置”东北接收的计划,得到多数同意,并于11月15日付诸实施。国民党的东北接收计划遭遇重大挫折。但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国民党准备撤退东北行营的前夕,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16日,斯氏复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表示苏方愿将东北日本工业资本以中苏合办形式经营,双方各占一半股份。此时,东北行营正待撤退,奉命留守长春的张嘉璈对东北交涉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只能表示将等候政府的指示。为了对以后的谈判预作铺垫,张还提出,“政治环境可妨碍此种经济合作之发展”,并在斯氏追问时明确表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想法传达给苏方。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的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担任总裁,苏方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特意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东北接收的态度。[11]张嘉璈当即急电重庆,请示方针,并在22日返渝汇报。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早定东北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备尝与苏方交涉的艰辛,张嘉璈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长远意图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与体认。他认识到,“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攫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迁重要机件入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又灼然可见”。他认为“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12]。所谓“精神谅解”就是国民党应以行动表现出对苏友好及对苏联在东北势力范围的默认与容忍,因为东北与苏联接壤,有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苏联目的是“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更不能与苏联作敌对之准备”;“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一方面预绝他国利用东北觊觎苏联之野心,一方面亦预绝中国利用东北作以夷制夷之幻想”[13]。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张嘉璈由起初反对与苏联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改而主张不能不与苏联谈判解决此一问题,以对苏让步得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并在以后的交涉中一直坚持了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对与苏联经济合作本有考虑。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代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其中就包括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14]但在国民党内部,一直有反对向苏联让步的强烈呼声,从而不能不影响蒋的决策。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嘉璈对苏让步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在这种情况下,宋、王虽不主张对苏决裂,但为顾及自身地位和名誉而反对向苏联再做让步实为情理之中。张嘉璈也承认宋、王的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他又自信自己主张的正确,认为“经济解决,虽不敢谓可完全顺利接收,然可望解决问题之大半”[15]。但张嘉璈本为金融专家,非国民党正统出身,在国民党决策层的影响有限,他无力说动国民党决策层的多数人同意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另一方面是苏联有意无意将经济合作与接收相联系,先经济而后谈接收,国民党暂时便无法改变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僵局,只能是暂时“搁置”东北问题,而这又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利。经济、外交与国民党、国共关系和中国国内政治就是这样以其特有的方式纠缠一体并影响着战后东北的历史进程。
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官商谈东北经济合作交涉问题,决定“东北未接收完成以前,决不与其商谈经济问题”。12月1日,蒋介石召见张嘉璈和蒋经国,告以“对俄之经济合作,必须在东北行政接收完毕以后再谈,但亦不能谈全部之工业经济,以此乃将来赔偿会公决之事也”[16]。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璈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11月28日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原则:1.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2.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3.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17]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同意。
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马氏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张嘉璈遂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须俟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18]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嘉璈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张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内容,并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做法,打压与拉拢并施,大棒与胡萝卜并用,一方面表示“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另一方面又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19]。9日,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再度会谈,马氏直截了当地表示,“苏联要求经济合作之目的,仅为获得本身之安全……仍望此事以迅速及简单之方法解决之”。在这几次谈话后,张嘉璈与蒋经国联名致电蒋介石,认为“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实不敢负此重任,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20]。
根据斯拉特科夫斯基12月11日对张嘉璈所言,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81%,水泥37%,电力89%。两天后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9处煤矿,14处电厂,3处钢厂,3处铁矿,19处非金属与轻金属厂,6处机器制造厂,8处化工厂等,共计81个单位;苏方要求组织11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非铁金属、水电、民用航空、煤矿等5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苏联的胃口相当大,所谓经济合作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精华,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的绝大部分均囊括其中。[21]在对苏方方案的分析意见中,张嘉璈认为:化学、机械工业及本溪钢厂设备已为苏军掠去,不妨同意合作;鞍山钢厂设备虽被拆走,但宜保持;煤矿可以部分合作;有色金属多应予保持;电力除丰满电站外均应自办。但此事既须国民党决策层的多数同意,又必须顾及民众和舆论的反应,而且将影响东北以至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此时的张嘉璈,既感在国民党内得不到支持[22],也对同意苏联要求后东北能否顺利接收心怀疑虑(苏方在谈判中只作空洞承诺而不提实际问题),既不能更不愿自作主张,只是等待国民党高层的决策。
蒋介石对东北经济交涉本不以为然。12月13日,他在北平召见熊式辉和蒋经国时,还特别表示“俄谓东北动产为战利品之非,是以东北为其盟国领土,不可以对欧洲敌国领土内之敌产相比拟也”[23],说明他不会在东北经济合作方面对苏联有大的让步,但格于现实环境,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自东北归来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对苏外交问题,决定再作适当让步,以延期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合办事业分为若干单位,不搞成一个大公司,电力不列入合办;先由经济部派人至长春商谈,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24]其时,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赴苏,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因此他同意就经济合作与苏方作初步商谈,不无以此向苏方示好、得其协助接收之意。蒋介石在和王世杰、张嘉璈和蒋经国谈经济合作交涉时,认为“我国对俄方应示以宽和,不宜峻拒,不妨先与试谈”;应将“此时不能固拒不谈之意告之。至于对俄,一来增进中俄同盟之义,并不愿因共党关系而阻碍我中俄邦交”[25]。而苏联也有意通过在东北接收方面向国民党表示“善意”而得到国民党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让步。马林诺夫斯基特意向张嘉璈表示,双方合作“并无困难”,希望国民党空运部队早日到来,苏军当协助国民党逐渐建立政权,甚而对张嘉璈“最好劝八路让出铁路线以外”的要求,“马答极是”,“语气极为肯定坚决”[26]。
1945年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向斯大林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认为“中国方面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蒋经国提出,可以别的名义而不作为“战利品”,将这些企业的半数转给苏联;同时,因为中国缺少重工业,应将部分企业交给中国管理;并希望在苏军撤走后再签有关条约。斯大林表示可以考虑,但认为现在可以谈判,协定晚些时候再签署,不过越快越好。[27]蒋经国此次访苏,在经济合作交涉方面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成果。
就在蒋经国访苏前后,留在长春的张嘉璈继续与苏方进行有关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1945年12月24日,他将中方意见通知苏方。1946年1月16日,经济部特派员孙越崎抵长春,带来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所拟交涉方案及合办大纲草案。由于国民党内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意见不一,且反对声浪很高,经济部的方案比原议方案有所后退,不再提撤兵费一事,缩小合办事业的种类和规模:电力、化学、石油不能合办;矿业应避免合办;可合办者只有本溪钢厂及相关产业(改组为钢铁公司),前“满洲自动车”和“满洲机械”所属工厂(改组为机械公司)。张嘉璈认为“中央指示,与苏方所提,相距太远”,因此致函蒋介石与翁文灏,力陈现“距离苏方撤兵期,只有半月。如此迁延,徒使苏方作种种不利于我方之准备与布置,将更增接收之困难”,主张“请将我方所提,再加放松”[28]。蒋介石的态度则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认为,“俄国对我提出东北经济合作具体方案,其要求范围甚广而苛也”,“忍痛受辱极矣!”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苏军延期撤军的动向,担心因此而影响国民党对东北的军事接收,故其考虑“惟有忍痛牺牲利益,以求达我收复领土之目的。但利益不妨忍让,而主权不能牺牲,故必须不违反我国之公司法为交涉基准,亦以此为交涉范围也”[29]。然蒋既无“忍让”的决心,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内对经济合作交涉退让的强烈反弹,故其指示张嘉璈“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30]。张嘉璈与孙越崎研究并商蒋经国后,提出在煤矿、钢铁、机械等方面再做适当让步。参与研究的孙越崎认为,“苏之目的,非仅在经济上之满足,而在于扶植亲苏政权”[31],对让步成效表示怀疑,更不必说国民党决策层始终坚持苏联不撤军即不签约的态度,中苏经济合作交涉难有大的进展。
事实果如张嘉璈所言。1月25日,他将经济部的方案交给苏方,苏方极为不满。26日至28日,斯拉特科夫斯基与张嘉璈等连续会谈。斯氏声称,中方提案“无法使每一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他还威胁说:“此项讨论,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张说明“我政府方面已尽最大之努力”,“请其将苏方原提案加以修改,作最大之让步。吾方亦再考虑,作最后之让步”。2月1日,张嘉璈会见马林诺夫斯基,马氏直言不讳地告张,中方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张嘉璈认为,“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不能再事迁延不决矣,故决定即返渝一行”[32]。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未及正式开始,便已陷于僵局。
1946年2月1日,蒋介石与王世杰“商谈东北俄军未撤之对策。今后俄军未撤以前,不再与其谈经济问题矣”[33]。4日,张嘉璈回重庆汇报交涉情况,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已届苏军延迟后改定的撤兵之期,国民党东北接收停滞不前,中共在东北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势力范围,形势发展对国民党不利。但在国民党内,多数人仍反对对苏让步。据张嘉璈所记国民党主其事者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的态度,“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蒋介石则“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不愿让步。在4日的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王世杰“仍主消极不予以口实为止,而不取反对形态也”。张嘉璈认为,如此一来,“苏必利用共产党扩充势力于长城内外,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因此建议蒋“重加考虑,决定方针。一则绝对不再与苏方讨论经济合作;一则再提答案,作最大之让步”[34]。7日,蒋再召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决定稍作让步,将鞍钢和鹤岗煤矿列入合办方案,并由张嘉璈回长春与苏方接洽。但宋子文实际并不赞成,他多次对张嘉璈表示,“恐交涉不能有结果。若继续交涉,徒使我方愈陷愈深,不如置之不理”,要张不必再回长春。[35]
就在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不得进展之际,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趋复杂化。美国资本对东北始终抱有经济扩张企图。1945年底,美国特使马歇尔到中国后,在与国民党高层会见时,不止一次提到东北经济问题,“对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特别注重”[36]。马歇尔还明确对王世杰表示,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因为“时间对苏联不利,因为苏军在东北驻扎的时间越久,全世界对苏联蓄意破坏条约就看得越清楚”。这样的意见对主要依赖美国为支持者的国民党而言无疑是有分量的。[37]2月11日,美国大使馆照会王世杰,转达美国政府意见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38]。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华盛顿公开对记者表示,东北日产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讨论解决。[39]美国此举的目的在于其自身利益,即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本处于半明半暗之中的中苏经济合作交涉公开化,导致国内舆论的反对,并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40]。实际上,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与苏联彻底决裂。美国对东北政策的立足点在于: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东北事务。这也是美国对战后中国基本政策的反映。对国民党而言,这无疑有点口惠而实不至。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更是急转直下。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其中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苏联的内容,使国内“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舆论的强烈反应,既不能不为国民党所重视,又为国民党强硬派提供了借口,使国民党决策层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对东北问题更失回旋余地,对苏强硬的主张占了上风。就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认为,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41]。
/和与战的抉择第二章东北的不战不和之局/2月中旬,张嘉璈与王世杰、翁文灏拟出新的经济合作方案。17日,蒋介石令“照兄等所拟办法,作为最后之尝试。但切不再有一字之增加。……必须以此为最后一步之决心”[42]。次日,王世杰约见苏大使,告以中方提出最后方案,将由张嘉璈和蒋经国在长春与苏方谈判。但前此美国提出有关东北经济交涉问题的照会,被蒋介石认为“此固为于我有利之提议”,“或于我不无补益也”,认为“如何因应不失其机会,应慎重处理”,18日急电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令“长春交涉经济合作问题暂中止,缓行静观局势后再定”[43]。20日蒋又致电王世杰转张嘉璈,强调令其“暂留重庆”待议。[44]虽然张嘉璈一直“以为此事早日解决于我方有利,苟拖延,苏方以为我无诚意,必助中共与中央对抗,困难更多”[45]。但他无力改变大局,2月25日致电留在长春的董彦平,告以“最近种种演变,似应先由两国政府间开诚交换意见后,弟等再行返长,因此行期展缓”[46]。随后,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对苏强硬提案,进一步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施加压力,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在被强硬派指为“卖国”的猛烈攻击下,噤口不敢言。[47]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实际交涉难以进行。
2月28日,张嘉璈致电留在长春的秘书张大同,嘱其告斯拉特科夫斯基他迟来的原因,“俾知我虽费一番苦心,而枝节之来,出人意外”。其后,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处长耿匡(济之)告斯氏,张将在二中全会后返长,斯氏表示张嘉璈“离长已多日,因华方无人负责,一切交涉均归停顿。经济谈判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赋予马元帅及彼两人全权负责办理,苏方专家已齐集此间,故报载在他处另行交涉一说,彼毫无所闻。此事总须予以解决,且已届从速解决之时”。不过据耿匡观察,苏方态度对张嘉璈“个人并无偏见,惟对谈判全未露让步之意”[48]。
1946年3月,苏联开始自东北撤军,但仍未放弃在经济合作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努力,并提出了新的方案,作了一些让步。不过,国民党坚持苏联不撤兵、接收未完成则不谈判的立场。3月8日,王世杰告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关于经济合作之商谈,我方原拟派张(嘉璈)、蒋(经国)两位赴长春继续商谈,而近接报告,苏方拆移机械设备甚多,故实无法再谈”[49]。9日,返国述职的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其“因中外舆论均将谓此种谈判系在军队压逼下之谈判,结果好坏均受攻击,于我固不佳,于苏亦不利。现在苏方宜先撤兵后再谈经济合作。……又提及红军搬运机器等事,谓中苏友谊关系两国前途至巨,此种机器于苏联整个建国补益甚少,因此而伤中苏感情,殊不值得。……红军延期不撤,搬运机器种种,均足使怀疑苏联者有所藉口,增加反苏派之力量。苏联真欲与我国永久和好,应对于主张与苏亲善者应不使其为难”[50]。
此时,由于苏军逐步撤退,国民党军队尾随接收,原以苏军隔离而在东北暂时相安无事的国共军队已处于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之中,张嘉璈颇为担忧,因此仍通过其在东北的部下,与苏方保持联系,希望可以促成苏军在撤离时交由国民政府接收,并为未来可能之转圜留下余地。[51]3月10日,张嘉璈致电张大同,告其“中枢方针仍盼圆满解决,保持友好。鄙意目下情形与一月以前迥异,苏方长久友好计,可否即行定期撤兵,将政权交于中央,再谈经济合作。如是,鄙人或可重返长春。若照近日谣传,苏方将撤兵,各地政权将由人民自卫军接收,则无异破裂,即毋须来长”[52]。次日,张大同等将张嘉璈的意见转达斯拉特科夫斯基,斯氏表示:苏方非不愿撤军,“惟如国方军队不能如期接防,则非政府军队不免乘间侵入”。他主张经济谈判仍在长春举行,并盼张速归主持。27日,苏联大使将苏方提案交中方,大体接受中方意见,同意在重庆谈判,唯要求合办企业股份双方各半,总经理由苏方担任。[53]31日,熊式辉告董彦平,“经济合作问题,苏方表示可归中央交涉,今后不在长春商谈,我方亦当视其对我军接防赞助之程度如何而定”[54]。
自3月中旬苏军撤退起始,国共军队在东北发生武装冲突,并随着苏军逐步向北撤离,战事愈演愈烈,冲突地域亦越来越大。张嘉璈“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介石亦以“东北军事紧急”,欲借经济合作“稍灭苏方之阻挠与操纵”,考虑重开经济合作谈判。4月4日,蒋介石约王世杰、张群、张嘉璈等谈东北问题,认为“似应即向苏方表示愿意商谈经济合作问题”。当天王世杰禀命约见苏大使,告以“一俟派定人员,即行开谈,惟望长春、哈尔滨不重演四平街往事,以免中国舆论再行恶化”。但是,王世杰坚持“我决不可因军事上一时之需要”而向苏方让步,对重开谈判并不热心。[55]6日,蒋介石自记:“俄对我东北撤兵亦已发表日程,故余已允其经济交涉开始谈判,而彼则急待此一谈判之决定,或可在长春铁路线使我接防较易。今后无论对俄对共之交涉方针应以不妨碍我长春铁路接防为主旨也。”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吴鼎昌、王世杰等研讨东北对俄经济交涉,决定“如其同意后,应即与其进行交涉,以期长春路全线较易接收。只要长春路全线为我接收,则东北总是解决大半矣。雪艇(王世杰)仍犹豫不决,彼之刚柔太过,即不及也”[56]。蒋介石在会后手令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关于中苏在东北之经济合作问题,由外交、经济两部各指定次长一人,与苏方开始商谈,并指定东北行营张主任委员公权协助该两部规划一切。”[57]
4月16日,外交、经济两部代表与苏方首次正式会谈。此时,正值苏军撤离长春,国共军队展开激烈的长春攻防战,张嘉璈特告已随苏军撤至哈尔滨的董彦平:“若长春为非法武力进占,政府内空气必转恶化,而影响经济商谈。可以此意使苏方知之。”[58]17日,张嘉璈又会晤苏大使,告以“吾政府十分注重长春、哈尔滨两地之接防。若照目下长春情形,势难圆满继续商谈”,结果被苏大使嘲讽为“何必如此斤斤计较”[59]。
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蒋介石下定动武决心,必俟国民党军队攻下长春后再谈其他。当天,王世杰告张嘉璈:“长春情形如是,显示苏方并无协助吾方接防诚意。吾方对于经济合作谈判,候苏方对于吾方所提协助接防长春,勿重演四平故事一点明确答复后再说。”张当即电告董彦平,“长春情形恶化,本人来长无裨益”[60]。5月23日,长春为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得意之余,声称“哈尔滨收复以后,苏方外交可进行,此时尚无外交可谈也”[61]。宋子文亦告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张嘉璈“交涉太懦弱”,因此“最好公权不再前往”,“最好勿使与苏联谈商经济合作,此事可完全由外交部洽商”[62]。
此后,东北成为国共交战的主要战场,经济问题事实无法提上日程,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最终不了了之。[63]
注释:
[1]《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及其他有关问题》,见胡世泽档,Box2。
[2]《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令与苏方切商东北工矿应归我所有电摘要》,1945年8月7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241页。
[3]《张嘉璈日记》,1945年10月17日,见张嘉璈档,Box18。
[4]参见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23~52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5]参见《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报告苏方视东北工业设备为战利品函》,1945年10月20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371~372页。
[6]参见《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5年10月25日,见张嘉璈档,Box10。
[7]有关苏军对东北工业的拆迁和损毁情况,详见下节所述。
[8]据权威的《奥本海国际法》,“在公有不动产所在的领土未经兼并而成为占领国的国家财产之前,没收这些不动产是不合法的”。有外国学者认为,苏联对所谓“战利品”的解释,“超出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实践普遍承认的战利品的概念”(薛衔天:《苏联拆运东北机器设备述评》,见《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86~87页)。
[9]《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32~534页。
[10]同上书,545、551页。
[11]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56~559、563~565页。
[12]同上书,551、554、546页。
[13]《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41~542页。
[14]参见《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46页。
[15]《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70~571、577页。
[16]《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28日,12月1日。
[17]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71、574页。
[18]参见《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158页。
[19]《张嘉璈主任委员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关于东北工矿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12月7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387~394页。
[20]《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87页;《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商谈经济问题电》,1945年12月8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395页。
[21]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588~594页。
[22]1945年12月3日,张嘉璈在路过北平与李宗仁见面时,李宗仁批评“对苏交涉太懦弱”,张嘉璈感叹说,“可见外间不明真相,易于批评”(《张嘉璈日记》,1945年12月3日,见张嘉璈档,Box18)。
[23]《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13日。
[24]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03页。
[25]《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20日、21日。
[26]《张嘉璈致熊式辉》,1945年12月23日,见张嘉璈档,Box26。
[27]参见《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202~205、208页。
[28]《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25~628页。
[29]《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19日、20日、21日。
[30]《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6年1月16日,见张嘉璈档,Box10。
[31]《熊式辉日记》,1946年1月30日。
[32]《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39~646、653、655页;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35页。
[33]《蒋介石日记》,1946年2月1日。
[34]《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30、656页;《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30日。
[35]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60~661页。
[36]《蒋介石日记》,1946年1月29日。
[37]参见《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29日,2月8日;Marshall to Truman,Feb.9,1946,FRUS,1946,Vol.IX,p.426;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见《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215页。
[38]《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1946年2月11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453~454页。
[39]参见《美国注视东北问题》,载《大公报》(天津),19460223,2版。
[40]《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61页。
[41]《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59、666页。
[42]同上书,664页。
[43]《蒋介石日记》,1946年2月12日、16日、18日。
[44]参见《蒋介石致王世杰电》,1946年2月20日,见张嘉璈档,Box26。
[45]《傅秉常日记》,1946年3月4日。
[46]《张嘉璈、蒋经国致董彦平电》,1946年2月25日,见张嘉璈档,Box26。
[47]参见《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19~20页,附件74~75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47;《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78、680、687页。
[48]《耿匡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日,见张嘉璈档,Box26。
[49]《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80页。
[50]《傅秉常日记》,1946年3月9日。
[51]详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的有关记载。
[52]《张嘉璈致张大同转耿匡(济之)电》,1946年3月10日,见张嘉璈档,Box26。
[53]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681、683、698、700页。
[54]董彦平:《苏俄据东北》,172页。
[55]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709、713~718页;《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日。
[56]《蒋介石日记》,1946年4月6日、9日。
[57]《蒋介石致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手谕》,1946年4月9日,见张嘉璈档,Box26。
[58]《张嘉璈致董彦平电》,1946年4月16日,见张嘉璈档,Box26。
[59]《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723、725~726页。
[60]同上书,727~728页。
[61]《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6年6月17日,见张嘉璈档,Box10。
[6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6年5月27日,见宋子文档,Box58。
[63]其后张嘉璈日记中还曾几次提到经济合作问题。6月24日,蒋经国告苏联“曾答复经济合作愿让出抚顺(煤矿)”。11月4日,蒋介石告张嘉璈,苏大使曾与蒋经国谈,应将一切问题提出讨论,如大连、旅顺、中长路及经济问题。1947年2月14日,在东北被中共一度拘留又被释放的张大同,在南京对张嘉璈“谈及经济顾问斯君已回哈尔滨,似将与共方合作矣”(《张嘉璈日记》,1946年6月24日、11月4日,1947年2月14日,见张嘉璈档,Box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