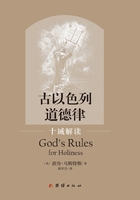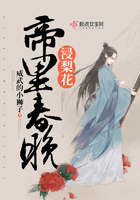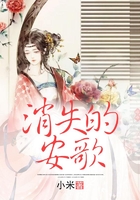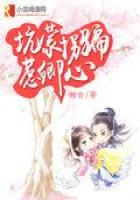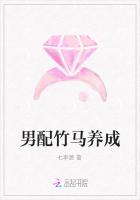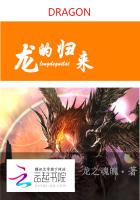写刘歆时,眼前就一直有另外一个人的身影在晃动。
——扬雄。
这不单单因为他与刘歆同龄,他们生活在同时代,同因自己横溢的才华而拔擢为汉成帝黄门郎,又共同以文人身份历经汉成、哀、平帝、王莽新四朝,最后共同以拥护及赞赏的姿态效力于王莽新朝,又彼此将各自生命的句点永恒地打在了天风年间。
更重要的是,当儒学在西汉末年呈现出种种驳杂、混乱景象,固陋贪鄙之徒竞相利用儒学纷纷进行篡改,以达一己升阶登庭目的,儒学被支离、曲解乃至走向歧途之时,他们选择了共同的为儒学矫枉纠偏的使命,挽狂澜于既倒,正视听于喧嚣。
所不同的是,刘歆以倡行古文经为己任,试图在经典文本的回归中正本溯源;而扬雄则是用自己的著述学说,向谶纬笼罩下“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的汉代经学进行挞伐,立己之论,破彼之说。
古文经学领袖刘歆虽以自己形单影只的努力向众博士发难,并最终因政治上的垂荫获得了暂时胜利,但他思想里仍受着阴阳家的深刻影响,其学说之中五行灾异论依然挥之不去。扬雄则援道释儒,为日益走向畸形的儒学重塑精神原貌,并以纯粹的儒者形象孤标粲粲地屹立。
所以,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说“刘歆实纯就古文经学家之见解以立言”,只是提供了一套反阴阳家的古典文本,“不杂所谓可怪之论”,而真正在思想体系上驳斥牵强附会的时学,并为儒家建立正朔之论的,则首推扬雄。
是他,使染垢的儒学重回孔孟之炉提炼,从而上启两汉纠谶纬之偏思潮。
是他,汲取道家自然观入儒,为儒学提供新的支撑力量,就此直接下育魏晋玄学风气。
应该送他一幅四字匾额——承前启后。
一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五十三年,死于公元十八年,历汉宣、元、成、哀、平帝及王莽六朝。一个寿数七十一岁的人能走穿六个朝代,不能说这个人的生命力如何旺盛,只能说那些皇帝们是多么不经活。
在西汉王朝二百一十四年的统治历史中,汉元、成二帝在位仅四十二年,但这却是西汉王朝由盛变衰的重要转折期。自他们开始,正像这些刘姓帝王的短祚之寿所透露出的凋敝气象一样,西汉王朝经“中兴之主”汉宣帝昙花一现般的繁荣之后,全面走向衰败。
不管班固因自家姑姑为汉元帝婕妤的缘故,在《汉书》里如何替这对父子粉饰贴金,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汉元帝刘奭与汉成帝刘骜是一对混蛋透顶的父子皇帝。
刘奭只知宴饮歌舞,荒淫度日,将朝政听任宦官摆布;刘骜则是外制于王氏外戚,内惑于赵飞燕姐妹。清人吴楚材在《廿五史纲鉴》中为前者下的结论是:“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矣。”对后者打的评语是:“帝耽于酒色,委政外家。”
西汉王朝在他们的打理下,政治日益黑暗,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暴乱四起。
很不幸,扬雄就生长在这个时代,而且出生于“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社会最底层贫民家庭。
如此出身,自然决定了他不可能有生于殷实之家的董仲舒那样“三年不窥园”的少年读书生活,更不可能像有刘姓宗室为背景的刘歆那样,少年即受皇帝召见,以早慧之资获得“黄门侍郎”殊荣。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扬雄的天性好学,更不影响他的资质聪颖,还不影响他立志儒道的决心。
《汉书·扬雄传》称:“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简单梳理一下,得出这个口吃少年综合印象者三:
印象一:好学博览,讨厌烦琐章句;印象二:寡言冲穆,喜欢清静湛思;印象三:安贫乐道,贫贱富贵不移。
顺便再拽出几条孔子语录。子曰:“辞达而已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用扬雄的行为比照孔子的教导,只有一个感觉:丝丝入扣。
一粒埋在土中的葵花子,最终不会长成一枚土豆,而是挺出一盘傲人的向日葵,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粒葵花的种子。泰戈尔说,生命在最初那刻即已定型。
由此看来,扬雄之所以在后天成为复归孔孟、重塑原儒的一代宗师,其实,早在他幼年从学时就已经被天性与禀赋所决定了。
二
成都,色泽绮丽,风致曼妙,钟灵毓秀,如诗如画。它似乎天生就与诗赋、与文人骚客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从同谷出发辗转来到成都,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万里桥西一草堂”后,立刻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陶醉,慨然写下:“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初来成都的李白,为其景色赏心悦目,吟出:“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刘禹锡观锦江美景,快意顿生,以一首《浪淘沙》抒发胸臆:“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陆游在成都生活了八年,晚年回到故乡绍兴,仍心怀梦萦,感慨那是自己最好的人生时光:“春夜挑灯话别愁,此心已在锦江头。旧时处处尘昏壁,想复长吟为小留。”
这片土地就是如此神奇,充满诗情画意。那么,它孕育出自己的诗赋大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事实是,早在汉初,汉赋奠基人、赋论大家、文学大师司马相如就出生在这里。
他的赋,势体宏大,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价:“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班固、刘勰称之为“辞宗”。
最为厉害的是,他以一首赋作走上政治舞台。汉武帝刘彻于偶然之间读到《子虚赋》,喜欢至极,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自己不能和作者生于同一个时代。狗监杨得意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见,司马相如又以一首《上林赋》,深得刘彻嘉许,被封为郎。
可以想见,自幼就喜欢辞赋,且生于斯、长于斯的扬雄,对这位前辈乡贤是如何的钦敬有加,佩服不已。在扬雄心目之中,相如“弘丽温雅”的赋作堪称典范,于是,“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历史再次重演,又一位赋作大家在这片土地上站立起来。
真是像极了!只不过在这出戏里,汉武帝换成了汉成帝,杨得意换成了杨庄,司马相如则换成了扬雄。
在《答刘歆书》中扬雄自道:“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御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
公元前十二年,汉成帝元延元年,四十二岁的扬雄接到诏令,离开成都,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走入大汉都城长安。
三
长安,自古以来究竟牵系了多少人的绮丽梦想?
与扬雄隔了七百五十四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同样是四十二岁的李白也接到来自长安的诏令,为此他欣喜若狂,不仅“呼童烹鸡酌白酒”庆贺,而且“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天真地认为就此可以实现“愿为辅弼”的远大志向,能够破柴门,济苍生,安社稷。但最后,现实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只能自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而长安之于扬雄,却既没有梦想,也没有期待,更没有奢望。他甚至上书成帝提出要求,“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由,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不要俸禄,不被杂事缠身,只做一个潜心书斋自由自在的文人。汉成帝笑了,下诏不夺奉,并且“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
来,是承诏而来,没有受宠若惊,甚至连过多的欣喜也没有。留,是顺承上意,没有身居要津的顾盼自雄,更没有放眼未来的雄心勃勃。泰然如素,平静恬淡。那就在待诏承明庭的黄门侍郎位置上,运用自己的才思,踏踏实实地做个粉饰太平、讴歌时代的御用文人吧。
他偏不。
由楚骚衍生出的汉代大赋,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写景,借景抒情。他要用手中的笔,在赋中上讽谏之意,抒针砭之怀。
公元前十一年正月,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扬雄跟随其后,回来后作《甘泉赋》以讽谏。
同年三月,成帝“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祭罢,一行浩浩荡荡游于名山大川,走到殷、周废墟时,成帝“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献上《河东赋》以针砭。
十二月,成帝羽猎,扬雄随从。他认为帝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又写下《羽猎赋》以讽刺。
公元前十年,成帝想在胡人面前显摆,发民捕猎,然后将熊罴、豪猪、虎豹、狐菟、麋鹿,载以槛车,送到长杨射熊馆。让胡人手搏,自取其获。扬雄为此写出《长杨赋》,借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刺。
然而,无论《甘泉》、《河东》,还是《羽猎》、《长杨》,均写得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如同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美轮美奂,赢得包括汉成帝在内的所有欣赏者为之掌声如潮,赞不绝口。
但,唯独作者闷闷不乐。
扬雄开始进行自我反思:“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汉书·;扬雄传》)
他认为讽谏是赋的重要写作使命,在华丽的辞藻、盛大的铺排中,借景抒怀,推类明意,现在呢,看赋的人只见到浮华的文字表面,而无视意欲表达的讽谏主题,这就失去了作赋的本意,岂不悲哉?
进而他联想到往时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向汉武帝上《大人赋》,本来想讽谏他好仙追神的虚无,汉武帝看后却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
扬雄为此得出结论:“赋劝而不止,明矣。”既然不能劝谏,那么赋就不光是“雕虫小技”,而且“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作为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大赋泰斗,自此,他再也没写过一篇赋作。
这是天性使然。
四
这种天性的养成,却和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自言:“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
两位老师,一个是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的远亲林间翁孺,这对他后来写成《方言》著作影响巨大。另一位就是严遵。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原名庄遵,后为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名严遵。清虚自守,自甘淡泊,德高学深,而且不屈身事人,是一位隐于市井的高人。他自甘贫贱,卖卜于市,数十年不改其业。这位老先生还有个怪癖,每天只为数人卜筮,“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
这样的人的确让所有人钦敬,何况是亲闻咳唾的学生。扬雄在《法言·;问明》中称赞乃师:“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
以隋侯珠、和氏璧形容乃师,且“吾珍庄也”的扬雄,可见对老师学问及人品的深切服膺,严遵的“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自然影响到他的为文与为人。
于是,扬雄“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天性,也就找到了答案。
然而,这样的人永远不合时宜。
汉哀帝登基之后,先前不可一世的王氏外戚集团大厦立倾,代之的是新外戚丁、傅两姓的权倾朝野,哀帝的同性恋友董贤也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所有跟随这三家跑的人都得到了升迁重用,表现奇佳者如朱博,火线提拔,官至臣相。
罢黜或升迁,那是他们的事情,这一切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不为外界吵吵嚷嚷所动的扬雄,更像个得道的高僧。
他关起门来,将喧嚣避之门外,为自己的书案保存一份雅静。
赋,是坚决不写了,那就追《老子》、《易经》之意,发自己之怀,写写《太玄》吧。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在这纷乱扰攘的世界守住自己这颗泊如的心。
电影《全民公敌》主人公迪恩有句著名的道白:“当你周围全是妓女,而你还守护着处女的贞操,那么你就会成为公敌,遭到所有人的耻笑与挖苦。”
扬雄就处在被嘲笑的位置。
他没有为此愤怒,或者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而是写下一篇《解嘲》,用对话的方式为自己解嘲,同时讥笑那些嘲笑者。
《解嘲》中,客问:“……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回答:“……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
从这问答中可以看出,扬雄的人生取向不是无所进取,躲于书斋不理世事,而是有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鲜明儒家情怀。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澈,天下大乱,朝廷颠簸,大臣们相互倾轧,“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此为他所不屑,所以“默然独守吾《太玄》”。
这种人生取向,同样可以追溯到他求学时面对屈原的态度。
扬雄早年深以屈原之文远远超过司马相如为奇,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哀惋。长发,宽袍,玉珮,香草;一片浩渺的大泽,一缕枯瘦的诗魂,一声回响天宇的叹息,一弯跃向汨罗的弧度,这种种意象在深喜辞赋、同为文人的扬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波澜。“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但扬雄并不以屈原怀石自沉的做法为然,他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怎么能以自戕的方式来结束自己?于是,作《反离骚》一篇,然后诗人气质十足地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
仔细看,扬雄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来自三个古人的嘴中。
老子曾对问礼洛阳的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以行。”孔子告诫弟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荀子在《宥坐》中说:“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这一点显然与董仲舒之后的那些经学家有着本质的差异。以儒为本、援道入儒的思想学术根基,使得扬雄始终能甘坐在冷板凳上,博学深谋,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
在扬雄看来,被时儒改造过的经学化的儒学,或谶纬化的经学彻底歪曲了经典儒家的真面目,他期望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纠正儒学发展中的偏向,从而纯净儒学,重振儒家精神。
这就是《汉书·;扬雄传》中所说的:“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能站在客观的学术角度对太史公说三道四,在中国,扬雄是第一人。
五。
李白的一首《侠客行》千古风传,脍炙人口:“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全诗通过赳赳侠客之口,道出了与皓首穷经于书斋的学人不同的另一番人生样态。
诗中所言之阁是天禄阁,所指之人正是扬雄。
汉哀帝之时,扬雄已经完全意识到“赋劝而不止”,于是“辍不复为”,然后他迁心于别处,“大潭思浑天”。执意不再用自己的赋来为皇家歌功颂德捧臭脚的扬雄,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将自己在政治上自我边缘化。
从此,深坐书斋,探研学理,这当然不是为避世而养心静气,做此无为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而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姿态,通过自己的述作,重新确立经典,再树儒家精神。
《太玄》、《法言》于是面世了。
扬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结构上却与《周易》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玄》和《周易》虽然都认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认为天道并非不可认识与把握。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和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所生成,阴阳二气产生于玄,玄是世界生成与发展的根源。
这个貌似无甚意义的理论确立,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它吸收了老子朴素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进而援道释儒,推翻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而对因“天人感应说”而产生的谶纬神秘学说进行了根源上的颠覆,直接对后世中国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汉张衡的“浑天说”宇宙论,就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思想,宋代的“图书”学统的理论根源,也与扬雄的《太玄》直接关联。
由于《太玄》文辞坚深,旨远义幽,不被时人所接受。正所谓“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行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
就连刘歆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无揶揄地对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利禄,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他担心好友的心血之作被后人用来盖酱缸。
扬雄的朋友张伯松曾盛赞扬雄介绍各地异代方言的专著《方言》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而对《太玄》也极尽鄙薄,“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与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抵粪,弃之于道矣”。
但一些卓有远见的人却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评价。
同时代的大学问家桓谭,就认为扬雄卓尔蹈孔子之迹,是鸿茂参二圣之才,“子云所造《法言》、《太玄》也。《玄经》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东汉张衡更是以一个科学家的立场评价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与《太玄》的遭遇不同,《法言》甫一面世就获得广泛好评。
在《法言》中,扬雄确立孔子为宗,指出“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虽山川、丘陵、草木、鸟兽,裕如也”,因之强调“孔氏者,户也”,表达了愿以孔子作为自己学习门户的自觉,和以孔门儒家作为思想宗旨的立场。他认为,孟子道继孔子,由他传承的学说才是大道,其余诸子之论皆为离经叛道之说。
最为可贵的是,他将老子援引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精神补给。“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进而指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
在他看来,儒学所宣扬的至真精神至简至易,它虽然是治国安邦、修身论学的最高原则,但却是一门人生实践之学,是孔孟从个人生命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故而不应该存在难解或不可理喻的成分。《法言·;孝至篇》写道:“或曰:圣人事异乎?曰:圣人德之为事,异业之。故常修道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扬雄认为,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最好从常识入手,不能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这就对西汉当时盛行的神秘“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思想,以及种种荒诞怪异之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篇》)“或曰:甚矣,传书之不果也。曰:不果则不果矣,又以巫鼓。”(《法言·;君子篇》)扬雄认为,流传的纬书不但不实,而且滥用巫术鼓吹,实为荒诞不经之论。
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写道:“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可见,他不仅自比为孟子,以孔孟之道的直接传承者自居,而且给自己定下了责无旁贷的大任,要以一己之力,廓清儒学发展道路上的塞路者,尽己之能恢复业已被篡改的经典儒学的真面目,展示儒家的精神原貌。
其实,以思想建树而言,扬雄的造诣还远逊于孟子,但他在儒学被谶纬神秘思潮包围的西汉末年,能重新廓清传统儒学,辟阴阳家之言,使儒学与之截然分离,实乃功勋卓著。
“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只有一扬雄。”这是千年之后王安石对他的感叹,司马光更是推尊他为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六
寂寥和落寞,永远是文人的宿命。
一部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人蹭蹬失意史,里面飘荡着太多的穷困、潦倒、抑郁、悲号。
大多数文人因科举失意,或人生狭窄逼仄,种种生活的艰难境况常常是自怨自艾,悲戚愁苦,精神萎靡,登高绝望,途穷哭返,笔下呈现出的多是叹老喈悲的人生灰暗呻吟。
这中间不乏人生志趣高迈者,如遭驱逐的屈原、被流放的苏轼、被贬谪的柳宗元……他们在远离庙堂、播迁漂寓的天涯亡旅中,较之于前面那个人群,表现出了更多文人的刚性与韧性,或仰天长问,或掀须朗笑,或将困苦的羁旅当做一场豁达的潇洒游玩。
但仔细看,他们从政治中心的出走都属被迫,他们的超脱与不在乎面庞下隐隐有几许故作轻松的成分。
扬雄完全异于他们,他是一个孤标。
从公元前十二年,四十二岁的扬雄因文名而被汉成帝诏见入京始,他就表现出一种“万物不可加于我”的人生恬淡之态。他上书成帝,“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由,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只想躲进书斋里,做个纯粹的文人。
继之的两年中,他以四篇赋作名动京华,同时更深得最高统帅的赏识,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何等求之不得的荣誉,但他此时却认定自己的文章只是“壮夫不为”的“篆刻雕虫”,果断停止了这种在自己看来非常无聊的写作。
汉哀帝时,外戚丁、傅和哀帝的同性恋朋友董贤大红大紫,“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但扬雄却没想去攀附这些人,走走曾一同共事的董贤的后门,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致志地写起他的《太玄》。
扬雄初为黄门侍郎时,与王莽、刘歆同僚。朝夕相处的工作岗位,彼此共同的对儒家文化的倾心爱好,自然使得他们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但王莽后来很快被封为新都侯,并出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三职。刘歆也在哀帝时任侍中太中大夫,再升为奉车都尉,领校秘书府图书,而比他们年龄更老的扬雄却三世不徙官,“位不过侍郎”,在给事黄门的板凳上一动不动。
淡泊名利、冲穆自守的扬雄,班固称他“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如果仅指“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确实做到了。
扬雄死后,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问桓谭:“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桓谭回答:必传。只是你与我见不到了。“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桓谭的眼力真是厉害!扬雄死后四十年,《法言》果然大行于世。
一个在他所处时代腾达亨通的文人,必在他身后的时代里湮灭。而真正的文人,虽在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淹蹇,也一定在他身后的时代被人尊崇。
七
在东汉崇拜扬雄的庞大文人群体中,班固就属于一个。
他对扬雄的仰慕显而易见。《汉书》中为一个人单独作传,且不惜笔墨分为上下两章,享有此殊荣的只有两位:一是王莽,一是扬雄。
详述王莽,是为了尽情批判与挞伐;细说扬雄,则纯系发自衷心对扬雄的景仰与爱慕。
因了这份爱戴,他不仅将扬雄的所有赋作原文照录到传中,甚至还长篇摘录扬雄的《法言》与《太玄》等作品,但奇怪的是,他对于扬雄另外两篇重要作品《剧秦美新》和《元后诔》却只字未提。
这中间有着班固内心的巨大隐情。
奉诏修史的班固站在东汉统治者的正朔立场上,认为王莽新朝属于大逆不道,是篡汉行径。扬雄的《剧秦美新》,却写于公元九年王莽代汉的新始建国元年。在这篇文章中,扬雄写下了“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之类指斥秦朝、讴歌新朝的文字,为王莽歌功颂德之作。
公元十三年,元后王政君死后,王莽诏扬雄作诔,是为《元后诔》,诔文中说“新都宰衡,明圣作佐。与图国艰,以度厄运”,同样是在赞美新朝,扬颂王莽。
这么一个潜心书斋、与世无争、“恬于势利乃如是”的君子,怎么能写出逆附汉贼王莽的阿谀之文呢?爱惜偶像羽毛的班固,于是悄悄隐去了这两篇文章,他不允许偶像有此污行。
不独如此,班固在《扬雄传》中还刻意说:“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言下之意,貌似扬雄是新朝的不合作者,这句“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也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其实,扬雄并非因为“耆老久次”的老资格而获得的大夫之职。
新始建国元年,王莽擢拔扬雄为中散大夫,比二千石秩,这说明王莽对扬雄非常器重,而扬雄也在此年写下《剧秦美新》,真心表达自己的拥戴之情:“数蒙渥恩,拔擢伦比,与群贤并,愧无以称职。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
两年后的公元十一年,发生了扬雄的投阁事件。原因是刘歆之子案发,案件牵连到曾教刘歆儿子生僻奇字的老师扬雄。天禄阁上正认真读书的扬雄,听到狱吏要来捉拿他,从阁上纵身跃下,几乎摔死。
此事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扬雄受王莽迫害的铁证。
其实,班固自己都在《汉书》中说:“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这说明王莽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后来,还是王莽亲自下诏不要追问扬雄,这也才有了公元十三年元后死后,“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扬雄欣然命笔的《元后诔》。
那么,这位从成帝、哀帝、平帝时一直“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素不与事者,怎么到了王莽的新朝忽然一改禀性,阿谀起来,攀附起来?
只有一个解释:在扬雄的心目中,王莽是以有德之新朝代无德之汉朝,符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的思想,是正统之禅。所谓篡汉,只是到了东汉班固这里才有的概念。
事实上,看王莽登基前的民心所向即可见一斑。钱穆先生说:“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我在《刘歆:雄踞两汉的一座学术重镇》一文中写过,若非王莽获得众人真心拥戴,就无法理解以刘歆、扬雄、桓谭为代表的一大帮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都属于重量级的文化精英,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信仰着王莽。
至于后来日益迷信化、刻板化、教条化的王莽如何让人厌烦,那是题外话了。但在新朝初创的此时,扬雄真心拥戴王莽,王莽真心器重扬雄,均为事实,无可隐讳。
所以,无论班固对扬雄的美化,还是明人用“士一失身难自雪,千秋史载莽大夫”对他讥刺,抑或郭沫若先生义愤填膺地指责他失节,都属以己之意,度古人之腹,是同样的不明就里。
八。
但扬雄很快看出了面前这个王朝的一片虚假性繁荣了。
他再次退回到自己书籍遍布的阁楼里,从此再不见有任何歌功颂德的文赋。
时局的黯淡让他心灰。人至暮年,又连丧二子,更增添了他无尽的悲哀。桓谭在《新论》中写道:“扬子云为郎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
贫困潦倒中的他已无意面前这个神话、谎话、鬼话满天飞的王朝,而这个摇摇欲坠的王莽新朝,似乎也已忘记了他。
那就孜孜于书阁,旁搜远绍,著书立说,为心中的一份神圣使命——为圣人立言,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燃尽自己最后一滴蜡油吧。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这是陶渊明的叹贫伤世之作。
一样喜欢饮酒、同样贫困不堪的扬雄,却没有这份凄苦的心情,《汉书·;扬雄传》说他,“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此时,他的眼前是否晃动着卖卜市中,得十钱就卷帘回屋读老子的老师严遵的身影?“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中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悲哀的吗?”
扬雄当然不可能听到这话,但他以老死贫困之中的枯瘦之躯,告诉人们,什么是瓢食箪饮居陋巷,晏如也。
公元十八年,扬雄别世。寒风中,为他起坟送葬的,只是那个叫侯芭的学生。